
在一个社交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在高频度地展示自己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这种展示成为一种“做自己”与“热爱”的代名词。自媒体博主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副业乃至正式职业,与令人疲惫的职场文化相比,它如此诱人:为自己喜爱的餐馆录制一次探店,精心修饰自己与行业名人的合影,一块屏幕背后,“兴趣变现”似乎变得触手可及。
然而,在《热爱的代价》中,康奈尔大学社交媒体研究学者布鲁克·埃琳·达菲(Brooke Erin Duffy)通过大量调研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对自媒体博主来说,所谓靠热爱谋生的背后,是无数人面临长时间的无偿劳动和自我营销。在一个算法流量为王的时代,他们必须不断地披露自己、取悦观众,这种热爱驱动的“愿景劳动”推动博主们进行自我剥削,也在逐渐异化他们的热爱本身。
作为一名批判取向的媒介学者,作者将自身也作为了研究对象。在达菲看来,当代学术体制与社交媒体环境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有着有趣的联系。为何学者们也在进行和自媒体博主一样的“愿景劳动”?当代学术体制又如何将这种意识内化并进行再生产?本文试图对这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展开探讨。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热爱的代价》,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原作者 | [美] 布鲁克·埃琳·达菲
学者们不可或缺的“愿景劳动”
作为一名学者,我特别坚持自己作为“批判媒介学者”的自我认同,部分原因是为了将自己与那些采取行政方法进行传播研究的研究者区分开来。然而,我希望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表明,这本书并不是对那些构成了不断增长的愿景劳动阶层的个体内容创作者的批判。相反,在这个项目中,我对那些慷慨与我分享见解和经历的女性(以及少数男性)怀着极大的尊重。我将他们的创业活动解释为试图应对建立在相当不稳定基础上的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而不是虚假自我意识的表达。诚然,还有一个更为私人的原因促使我强调自己批判的对象是结构而不是其居民:我自己也是一个愿景劳工。也就是说,我发现影响社交媒体领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与当代学术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虽然学术界有着稳重、象牙塔般的外表,看起来与创意产业相距甚远,后者是一种以波希米亚的酷感为标志的职业,但将知识的创造和传播理解为一种文化工作形式在概念上的跳跃并不大。许多同样被推崇的理想,即自主性、灵活性、对“做自己热爱之事”的永恒追求,似乎同时激励着两个领域的工作者。事实上,艺术史学家/作家宫德光认为,学术界在“将工人的个人身份与工作产出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职业中独树一帜,这也适用于创意产业。
创意劳动甚至越来越多的学术劳动——有许多不那么理想化的特征,包括长时间工作、高度不稳定性和对临时员工(自由职业者、无薪实习生和临时工,抑或兼职教师)的过度依赖。在这种背景下,文化理论家罗莎琳德·吉尔敦促同行学者“将学术劳动视为一种文化工作,面临着许多与文化创意产业工作相同的挑战和经历”。

《热爱的代价:社交媒体、理想职业与愿景劳动》
作者: [美]布鲁克·埃琳·达菲(Brooke Erin Duffy)
译者:李泽坤
版本: 东方出版中心
2025年11月
然而,对我来说,发现这些职业的相似性是一个偶然,我是在访谈时看到这一点的。当受访者——一位时尚博客领域的新手但已积累了大批粉丝——反思她的个人品牌提升策略时,我发现自己也在思考是否该利用这些社交媒体自我品牌的推广实践。毕竟,作为一名初级学者,我非常熟悉这种推广自己的研究的要求。但这种特别的冲动——对我Twitter帖子的发布时间进行精心计算——让我感到不安。正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创意生产和学术生产的世界多么相似——也正因此,我的大部分劳动相当具有愿景性。
让我明确一点:我并没有想成为互联网创业者,也不期望企业品牌会因为我推销产品而对我大加关注。但其他巧合似乎无可辩驳,最显著的是这些职业领域的个体化性质。学者——特别是在定性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是卓越的独立工作者:尽管我们隶属于部门、学院和/或大学,但我们的学术项目是由自己制定的。当然,限制是存在的:学科的、意识形态的,以及日益增加的基于市场的限制。但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个体化的职业。品牌推广的话语在这里似乎特别贴切:我们的研究专长是我们的利基,我们精心打磨的“学术演讲调性”是我们的口号。这种演讲塑造了我们在学术会议、讲座后的招待会和非正式聚会中的介绍性互动。这些活动就像创意产业的聚会和其他形式的“强制性社交”,是劳动和休闲的奇特混合体。这些活动被合理化为对未来的自我的投资,但它们可能“有回报”,也可能没有。而且它们可能也没有报酬,因为预算的减少迫使一些大学暂停了对教师的差旅资助。

纪录片《受审视的生活》剧照。
像本书中记录的愿景劳工一样,学者被赋予了一些自由来设定自己的日程,即便这显然因机构和组织文化而异。一年中的某些阶段,如暑假和寒假,也给了学者行动上的灵活性(即远程工作)。就我个人而言,我在家完成了大部分的休假写作,许多大学校园在夏季异常安静。然而,这些表面上的自由是有代价的:就像网络创业者一样,学者被迫随时保持在线:对学生、教师同事、合作者等。工作侵入一天中的每个时刻,截止日期以疯狂的节奏到来。正如一个笑话所说:“学术界的工作灵活性很大:你可以任意安排每周80小时的工作!”此话所言非虚。事实上,当我的受访者详细描述收件箱爆满、假期引发的焦虑和笔记本电脑一直放在床头时,我发现自己也在热切地点头。
女性学者愿景劳动的复杂性
虽然有些想法是我个人的,但它们也是饱和的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症状,这个劳动力市场挤满了高度专业化的工人。高度竞争的系统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求职者和那些幸运地找到全职工作的人内化了“不发表就出局”的心态。此外,为了巩固他们的终身教职,学者必须以完全可量化的方式展示自己的生产力。“学术影响力的证据”包括学者的被引次数、h指数和期刊录用率,这些指标与社交媒体生产者的“影响力”评价标准并没太大不同。虽然这些指数长期以来帮助人们评估学者的职业成功,但研究人员越来越有责任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活动“有机地”提升这些数字。我感到有必要持续更新我的网站,在Academia.edu等网站上发布我的研究,最重要的是,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与同事分享我的出版物。
正是最后一项活动让我感到极为紧张。就像我的受访者表达了对“展示自己”的焦虑一样,每次在Twitter或Facebook上分享一项职业成就时,我都会感到一种不安。但我周围充斥着关于“自我品牌推广”重要性的建议,或者,正如《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所描述的,“如何策划你的学术数字身份”。因此,我发现自己正在战略性地思考我的线上形象。当同事、前教授、学生、朋友和家人占据相同的社会媒介空间时,对“语境崩溃”的担忧就会被推到前台。我曾责备自己最亲近的人上传和我的学术角色相去甚远的照片,并且我完全能意识到我的朋友和家人对我定期分享的论文征稿信息毫无兴趣。
这些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人品牌推广,当然与社会规范深深交织在一起:研究证实,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夸耀自己的成就,而边缘化群体的成员则不太可能进行自我推销。这些差异对劳动者产生巨大的文化和经济影响。在学术界,我们在引用实践中看到了这些影响:自引率中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31%的男性和21%的女性会引用自己研究),这对他人如何看待研究者产生了实际影响。根据研究性别和引用实践的社会学家的说法, “虽然自我推广增强了能力评估,但它也降低了女性的受欢迎程度。这些自我推销的性别化观念可能会影响对自引的看法”。

美剧《黑镜》(第三季)剧照。
对女性主义学者来说,这些反应增加了一层复杂性。反思自己作为女性主义活动家的工作,亚历山德拉·尤哈斯(Alexandra Juhasz)解释了她如何将自己的博客理解为“公开思考、磨炼声音、自我命名、社区建设和利益相关”。然而,新一代女性主义学者将同样的社会实践——学术博客——理解为个人“自我推广”的形式,而不是集体政治。我同意,差距确实存在:资深学者从未敦促我“推广我的工作”,但我现在发现自己会建议博士生一定要创建和维护网站,撰写关于他们研究的博客文章,甚至有策略地确定他们的文章标题:“短标题更容易被引用,”我建议说。
这种愿景劳动的制度背景是日益公司化的大学系统。面对公共支持的减少,它已接受了市场理念。高等教育的这种转变表现为多种形式:“摇钱树”硕士项目、对问责制和指标的不断要求、明星教授的崛起,以及文化产业研究员凯西·布里恩扎(Casey Brienza)描述的“新自由主义言论……将学生重新定义为顾客,将导师重新定义为服务提供者”。
媒体学者杰夫·普利探讨了这种市场逻辑的另一种表现,即社交媒体学术出版网站(Academia.edu和ResearchGate是最受欢迎的两个)的增加,这些网站代表了从事数字声誉建设实践的“学术微名人平行宇宙”。因此,普利认为, “学术声誉的社会学——传统上专注于引用和大众媒体曝光度——应该更新,以解释学术生活中的‘平民化转向’”。他的呼吁促使我们仔细思考由公司化和名人化相互作用塑造的知识生产系统的利害。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以呼吁在数字媒体研究中进行另一项、平行的更新作为结尾:由于市场结构的持续存在,我们应该继续将文化劳动者的经验置于中心的学术研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从他们那里学习,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还因为他们能让我们看到自己。不论是作为逐愿者,学者,还是作为文化创造者。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原作者:[美]布鲁克·埃琳·达菲;摘编:刘亚光;编辑:刘亚光;校对:张彦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不错过每一篇精彩文章~

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
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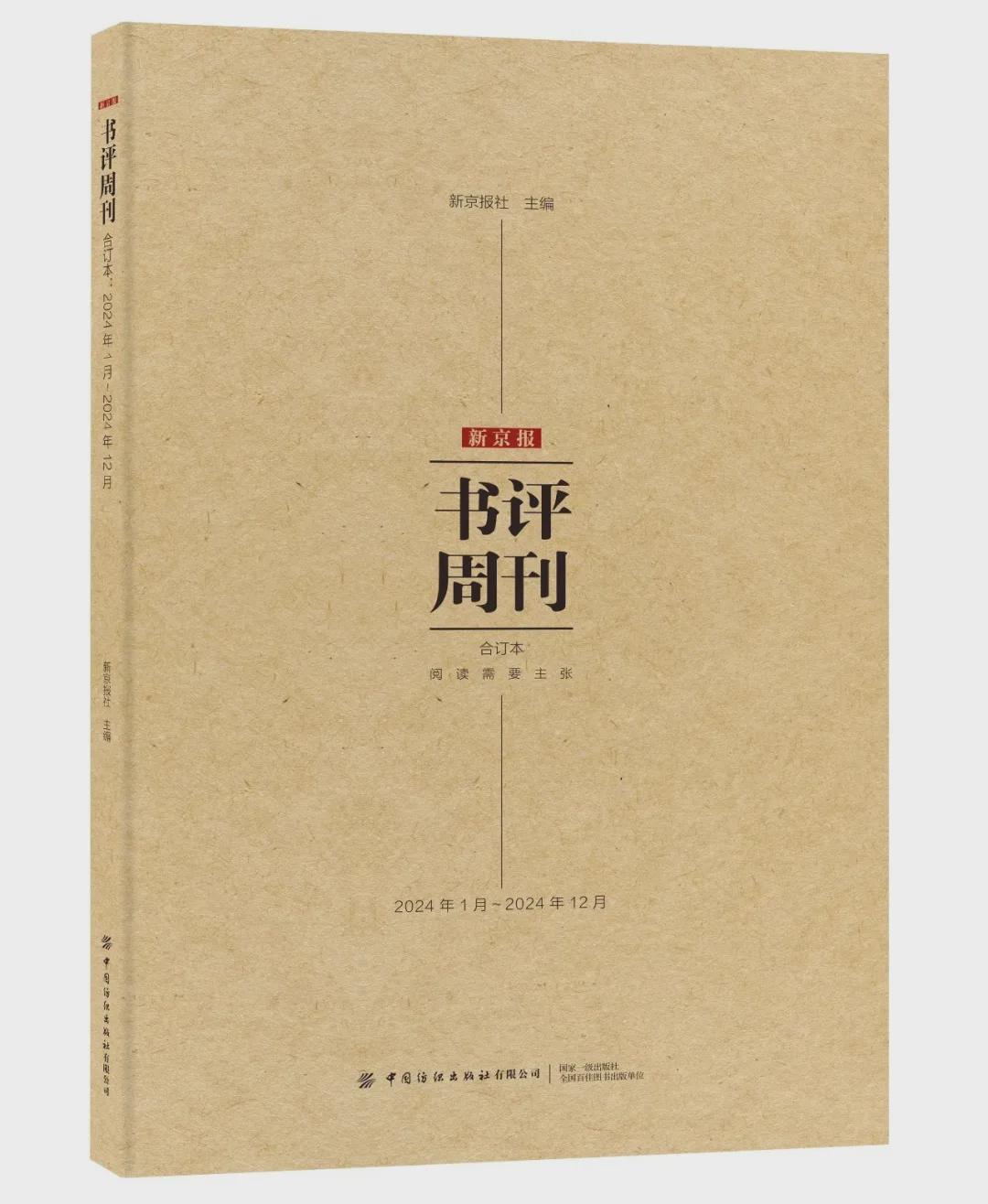
了解《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合订本详情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