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黎紫书是Miu Miu文学俱乐部上海站活动的嘉宾之一


今年大概有五个月时间,黎紫书在忙怡保老家的新房装修。她请了两位师傅,一个管硬装,一个管软装,年纪都在五十岁上下。那段时间她人还在美国,日常靠着WhatsApp遥控指挥。起初对话全是正事,师傅每天发来照片和视频,汇报进度。渐渐地,聊天内容松了下来,也穿插些家长里短。等黎紫书回到怡保,特地请两位师傅吃了顿饭。饭桌上,黎紫书当记者那会儿的劲头又上来了,问东问西眉飞色舞。当装修大功告成,她多了一间新房,也多了两个朋友。
直到最近,两位师傅偶然发现,那位常与他们闲聊的客户竟是马来西亚国宝级作家。他们又惊又喜,发来语音:“我们是第一次给作家装修呢!”然后邀请黎紫书当周去吃火锅,还让她带上一本亲签的书。她一口答应:这周在上海,回去就约。

Miu Miu文学俱乐部当天的第三场对谈,主题为“张爱玲:成长与逃离”
飞抵上海,是为参加“Miu Miu文学俱乐部”上海站活动 —— 受欧洲文学沙龙与艺术家社群的悠久传统所启发,Miu Miu文学俱乐部于2024年于米兰启动,通过文字映照今昔女性的生命图景,上海站活动同样延续这种推进当代思想进步与文化教育的立意 —— 然而当黎紫书坐下,对谈开始,她随即切换至另一种状态:一种近乎冒犯的、令人屏息的诚实。当天对谈的主题是“张爱玲:成长与逃离”,黎紫书与张爱玲研究专家张曦以及当代小说家笛安共同解读作品《雷峰塔》。一开口,她便语惊四座:“今天在这样一个场合,其实我很希望能说我对张爱玲认识很深,可是我偏偏已经答应了自己要诚实,所以我必须告诉大家,我过去都没读过张爱玲。我是为了今天活动才读了她的《雷峰塔》。”
这番赤裸而诚实的讲述随即卷起舆论狂潮,但对熟悉黎紫书的人而言,她早已多次显露过毫不含糊、拒绝扮演“正确”角色的姿态。宝珀文学奖的颁奖礼上,担任评审的黎紫书也曾直言:“我希望青年人表现出更大胆更狂放更有独创性的东西,值得我为TA不择手段地去争第一名……但这一届,没有这样的作品。”
“我现在越来越敢说了。“黎紫书在播客《岩中花述》中聊到,”我并不觉得自己年轻时候对世界的看法和今天的有太大差别,今天说着同样一番话的时候,身份不一样了,底气不一样了,效果也就不同了。”

Miu Miu文学俱乐部上海站活动现场
这份近乎执拗的耿直,或许可以在她早年的生命经历中找到回响。黎紫书原名林宝玲,1971年生于一个贫困凄苦的家庭。父亲有三个家庭,十多个小孩,几乎不太出现;母亲是第二房太太,只上过三年小学,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四个女儿。在她的成长记忆里,“匮乏”是关键词。买不起书,是她最早需要靠自己的智慧去解决的难题:妈妈床底下的旧电影杂志、舅舅家的金庸小说、书报亭里能借来看的日本漫画……有什么,就看什么。在这些驳杂的书中浸泡大的黎紫书,形容自己从小“孤僻”,独行惯了,不太受他人意见的影响。
三十五岁的时候,黎紫书决定“出走”。当时她在《星洲日报》深受器重,婚姻生活也安稳平淡。但她难以抗拒内心写作的召唤,最终决定离婚离职,纵身跃入前路未卜的、毫无保障的生活。为了避开亲友们劝阻,她躲起来不接触任何人。“我已经决定了,就这样子。”
同样是这份对自我的极度忠实,让黎紫书对文学本身发起了挑战。当外界赞叹她横扫马华文坛的各大文学奖项时,她却毫不讳言,为了尽早“出头”,曾对获奖作品做过大量研究,揣摩技巧,迎合评委喜好。直到拿奖拿够了,她对这场游戏感到厌倦,决定退出所有评奖,只书写符合自己文学标准的作品,于是,有了《流俗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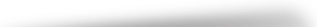

《流俗地》
长久以来,马华文学像一座孤独而湿热的岛屿,既不属于中国的“中心叙事”,也难以完全融入马来西亚的“国家论述”,这使华文写作者们常常怀有一种文化焦虑,在作品中埋入极具辨识度的“标识”:橡胶林与大象、五一三事件的历史创伤、华人在多民族国家中的身份焦虑。这些主题,既是坐标,有时也成为一种创作惯性。但在《流俗地》中,黎紫书几乎是主动丢掉了最趁手的武器,将笔触沉入故乡怡保,专注于描摹其中市井小民的俗务俗事。她用那双对万物进行补帧的眼睛,让人们看到怡保老茶馆里的慢生活,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凡俗并无不同;一个叫银霞的盲眼女人在命运中浮沉,也足以引发跨越文化的共鸣。
“我喜欢写这些人,是因为他们通常‘不被看见’。比如开理发店的印度人,对马来西亚读者来说,是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面孔,却从未在我们的文学中真正登场。难道他们就没有被书写的价值吗?“黎紫书的语速偏快,节奏很密,”我把自己看作是他们当中一员。尊重他们,就是尊重我自己。”在《流俗地》的构思中,人物大辉失踪多年的去向,本是一个必须交代清楚的悬念。给读者一个说法,这几乎是所有作者的肌肉记忆。但在写作过程中,黎紫书敏锐地意识到:小说里的其他人物,根本没有人在意大辉去了哪里,他们早已被各自的生活裹挟而去。此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摆在了面前:究竟是该遵循自己作为“创作者”的需要,还是该遵循“小说”自行生发出的内在逻辑?她选择了后者。“我创造出了一个有生命力的东西,”黎紫书说,“那么我就必须尊重这个生命,让它以最自然的方式去成长。”
这种尊重同样体现在她对汉语的坚守上。黎紫书没有接受过规范化的中文教育,从小在混杂着华语、粤语、英语、马来语的“语言熔炉”中长大。但她对纯正汉语的锤炼近乎一种洁癖。在她看来,马来西亚日常语言的芜杂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像一片“毫无美感可言的野地”。因此,她在小说中坚持“每一个字都必须承载它的功能”,不留任何闲笔和灌水。

Miu Miu文学俱乐部上海站活动现场
她毫不讳言,自己的每一次写作,都是为了写出能够传世的作品。“像《流俗地》这样的小说,”她说,“我真的相信除了我没几个人能写出来。我认识的、见过的这些人,我跟他们倾谈的那些时间,都不是白费的。”从文学奖的“优等生“,摇身一变成为了游戏规则的”叛逆者“,黎紫书再一次获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成功。《流俗地》成了现象级的”出圈之作“,它几乎拿遍了华语文学界最重要的奖项,并牢牢呆在各大书店的热销榜单上。黎紫书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力,甚至丧失了百分之四十的右耳听力,至今病因不明。她原本计划一生至少写三部长篇,如今却必须直面一个残酷的问题:下一部,是否会让她再失去剩下的听力?“如果要写。” 一向快人快语的她罕见地陷入了犹豫,“需要勇气。”
当写作这条路以一种近乎掠夺的方式消耗她的身体时,黎紫书至少在故乡怡保,那个她想要养老的地方,一砖一瓦地建造了自己的新家。她对这个安放写作的房间,只有一个要求:“必须要有一扇窗。”窗外不一定有绿荫,但要有人,让她在写不下去的时候,可以隔着一点距离静静地观察。“这扇窗在某种意义上比那个房间还重要。”这或许就是黎紫书最终为自己营造的安身之所:一间房,一扇窗。房间里,她是那个孤独的造物主,向着文学边界坚定地掘进;窗户外,她是那个孤僻的潜行者,在凡俗人间找到了最丰饶的养分。

有评论认为,您的《流俗地》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传统马华文学的南洋意象和研究框架,回归到了一个更普世、更纯粹的关于“人”的故事。这种“脱离”是您一次有意识的“越狱”,还是一次自然而然的“远行”?
“远行”这个词更贴切。“越狱”预设了一座监狱,一种对抗的姿态。我没有。我从未觉得“马华文学”是牢笼。书写故乡更像是一个我欠了自己很多年的承诺。那是我最了解的一片土地和一群人,动笔去写他们,本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之所以迟迟不动笔,是因为我深知,写自己最熟悉的地方,责任最重。必须等到自己足够成熟,心智足够强大,才能不辜负它。所以,当我动笔写《流俗地》时,那种自信已经在了。我清楚地知道,这部小说的样貌会跟我过去所认知的马华文学图景非常不同。我甚至能清晰地预判到评论界可能会有的声音,好的,坏的。但在那个当下,这些外部声音已经无法干扰我了。小说有它自己想要长成的样子,我的任务是忠于它的内在逻辑,不受干预地将它呈现出来。我知道,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在挑战一些既有的书写范式。但这难道是坏事吗?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能够诚实地、勇敢地拓宽边界,这本身就是一种荣誉。

Miu Miu文学俱乐部上海站活动现场
您曾说过“所有写作到最后都是个人生命史的写作。”我想问的是,在您的“生命史”里,是否也藏着一两个不肯离去的“鬼”?也许是某个您需要反复重写的场景,某个您始终无法真正理解的人?
是有的。我后来自己也发现,在我的小说里,父亲的形象总是以相似的面貌出现 —— 负面的、缺席的、不负责任的。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一种刻意的发泄,更不是控诉。它更像一种无法回避的、诚实的映照。当故事需要一个父亲的角色时,那个不负责任的形象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因为那是我最熟悉、最真实的父亲的样貌。我意识到了这种重复的倾向。但我也清楚,我不能为了对抗这种重复,而去刻意塑造一个美好的、虚假的父亲形象。那将是一种背叛,是对写作、也是对自己的不诚实。
您在很多城市生活过,也掌握了很多门语言。非常期待您那本以“异乡人”为主题的短篇集。您笔下的“异乡感”,会更倾向于一种存在的痛楚,一种旁观的视角,还是别的什么?
这个短篇集,我想处理的是一种更普世的“异乡”体验。我会写我自己作为异乡人,在别处生活的状态;但同时,我也会写那些我在马来西亚所接触过的、来自别处的异乡人。我还想探讨一种更微妙的异乡感——当你离开故土多年后重返,却发现自己在家乡也成了一个异乡人。因为你的故乡变了,而故乡的人也开始用看外来者的眼光看你。所以,这个集子会包含各种各样的“异乡”状态:地理上的、心理上的、时间造成的……所有与这个主题相关的观察和体验,我都想将它们收纳进来。

Miu Miu文学俱乐部上海站活动现场
想了解下您平时的写作习惯?
我只有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才称得上是自律的。我平时的生活其实相当随性,写作时间也不固定,经常晚睡。但长篇不一样,我知道如果不设定一套严格的纪律,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会给自己安排“双休”,一个礼拜只写五天。在工作日里,我每天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完成一两千字。通常,我会在四到五个小时内写完,一旦达到字数要求,当天的工作就结束了。在真正动笔去写之前,那个画面已经非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了:光线是从哪个角度射进来的,打在什么物体上,形成了什么样的阴影,人物的位置关系又是如何……我几乎是先“看见”了这一切。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尝试着用语言去“还原“这个已经存在的画面。我的写作方式是“一次成稿”。当天写下的一千多字,就是最终要用的版本,不会隔日删改。写完,就是完成了。
你喜欢的作家来到你的城市,你有机会当面问他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
我不会问TA任何问题。很多年前,我听说莫言和王安忆要来吉隆坡演讲,那是我知道的、第一批来马来西亚的中国大陆作家。我特地从怡保搭乘长途巴士,在还没有高速公路的年代,一路颠簸,顶着中午的烈日赶到现场。当我满身大汗地挤进去时,已经迟到,没有座位了。我就站在最后一个角落里听。结果,我一句也没听懂。王安忆的语速很快,他们两人都有着我们当时完全陌生的口音。我站了整场,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就默默地离开了。那一刻我或许就明白了,作家和作品是两回事。
就像金庸,就算再喜欢他的武侠小说,我也知道金庸是金庸,不是他小说里的大侠。我遇到过他的一些旧日下属,他们说我的上司不是金庸,是查良镛,他是商人。他没有具体讲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马上可以猜到了。所以,不管我有多么欣赏一部作品,我都不会再将它与作者本人划上等号。我不想问他们任何问题,他们最好的回答,已经全部写在了书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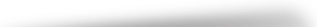

《流俗地》改编的影视作品有望明年上线
您的作品,尤其是《流俗地》,被广泛认为是当代女性写作的杰出代表。但同时,您的笔触又异常坚硬,充满了某种“去性别化”的力量感。在您的个人成长和创作中,您如何看待和处理自己的“女性”身份?它是一种束缚,一种赋能,还是一种您更愿意超越的标签?
说实话,我过去很少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身份和角色。我认为我是中性的。这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家里几乎没有男性,父亲常年缺席,姐姐也很早就外出打工。某种意义上,我扮演了家中“男性”的角色。水电工是我,扛重物的也是我。但这并非委屈,因为家里总得有人去做,我恰好就是那个去做的人。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感恩有过这样的经历。正是因为从小就没有产生过那种“这件事应该由男人来做”的依赖性,才让我成长为一个特别勇敢、特别有担当的人。这也导致我在做人生很多重大选择时,比如离开故乡,我并不是站在“女性本位”去思考,而是站在“人的本位” —— 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我该如何解决问题,如何扛起责任。所以,当这些年很多人都在谈论女性主义,甚至有些读者会非常执着地、只用一种女性主义的眼光来阅读文学时,我会有一些疑虑。女性能够更自觉地去阅读和创作,这当然是好事。但我怀疑的是,他们所理解的,是一种全面而深入的女性主义,还是一种偏狭浅薄的视角?如果创作者都去迎合那种单一的、所谓“大女主”的创作方向,我认为那只会让文学走向一种不健康的同质化。
我们知道根据《流俗地》改编的影视作品有望在明年跟观众见面,你对它有什么期待吗?
我把这部小说托付给了两位非常有诚意的、尚未成名的年轻新导演,因为我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故事是真心喜欢。《流俗地》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我,我也真心希望,这部小说能够成为一个起点,去成就另外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导演有个很有意思的想法,让我客串一名记者。戏里的情节是,银霞因为“人肉地图”的事迹走红,引来了大批记者采访。其中一个上前采访她的记者,就是我。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奇妙的时空错位。因为小说里描写的那个年代,正好就是我在怡保当记者的时期。所以,某种意义上,我将扮演“当年的我自己”,去采访一个“由我虚构出来的人物”。这其中的互文关系,想想就觉得好玩。
采访/撰文Sandra
编辑Leandra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