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的冬天,那是真的冷,四川宜宾火车站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
有个穿红毛衣的女人蜷缩在角落里,那毛衣早就磨得不成样子,但在灰蒙蒙的雪地里还是扎眼得很。
路过的人都捂着鼻子走快两步,没人愿意多看这个浑身恶臭的乞丐一眼。
直到她身子彻底硬了,咽下最后一口气,被人用破草席随便一裹扔到了荒郊野外,这狼狈的一幕才算完事。
谁能想的到,这具连个墓碑都不配有的尸骨,三十年前那是整个川南地区最风光的女人?

但要是翻开那些发黄的老档案,把“恶霸地主”这些标签先撕下来,你会发现凌君如这事儿吧,复杂得多。
要说清楚凌君如的命,得先扒一扒她那个糟心的家。
在民国时候的四川,“袍哥”这词儿你绕不开,黑白通吃,跟现在的社会关系网似的,渗到了地缝里。
凌君如亲爹死的早,老妈带着她改嫁给了一个叫凌友臣的富农。

这继父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是当时“叙荣乐”社团里的老油条,吃喝嫖赌那是样样精通。
在这么个家里长大,还在宜宾女子中学读书的凌君如,虽然是公认的校花,但脑子里装的可不是什么“知识改变命运”。
她太清楚了,读书太苦太慢,哪有像继父那样在江湖上混吃混喝来得痛快?
这种价值观一旦歪了,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
中学一毕业,这继父就把她推给了曹荣光做干女儿。
说是干女儿,其实大家都懂,这就是去“拜码头”,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岗前培训”。

曹荣光专门请人教她唱戏、跳舞、应酬,这哪是培养大家闺秀啊,分明就是在这个乱世里,要把她打造成一件待价而沽的高级玩物。
一九二九年,那场戏院的相遇根本就不是偶然。
这事儿说白了,就是一场精准的围猎。
嫁进刘家那几年,凌君如过的确实是神仙日子。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到那个年代能奢靡成什么样。
据当地老人的回忆,光是她的衣服就装满了五十个大樟木箱子。
啥概念?
就是现在的女明星也不一定有这排场。
她脚上的绣花鞋有四百多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能做到天天不重样。
那时候四川还穷得叮当响,她就已经是用法国进口香水的时髦女郎了。

每次坐着那辆挂满铜铃的人力车出门,车还没到,香味儿先飘出两条街。
这种巨大的物质满足感,给她造成了一种致命的幻觉。
她以为只要依附在权势这棵大树上,这种好日子就会像长江水一样,永远流淌下去,永不枯竭。
可是啊,历史这玩意儿,最喜欢在人得意忘形的时候给你下绊子。

这一招看似是姐妹联手,其实是蠢到家了。
这两姐妹仗着受宠,开始插手刘家的财政大权,疯狂敛财。
虽然最后她们带着私房钱跑回了老家,生活依然比普通人强百倍,但这其实是命运给她的最后一次逃生机会。
可惜啊,她没抓住,也没想过要换种活法。

真正让凌君如万劫不复的,是时代的彻底翻篇。
这可不仅仅是换个朝廷那么简单,这是对旧有一切依附关系的彻底清算。
凌君如还想着回刘家公馆分一杯羹,结果被二姨太杨仲华直接关在大门外,理都没理她。
她又想回头依靠那个继父,结果继父因为参与土匪活动,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家产全部充公。
一夜之间,昨天还是云端上的贵妇,今天就跌进了泥潭里。

在这个新社会里,劳动才是光荣的,只有干活才有饭吃。
可她呢?
除了唱戏、打牌、花钱、抹香水,她连个扣子都不会缝。
她后半辈子的悲剧,说到底不是谁在惩罚她,而是她彻底丧失了生存能力。
她带着弟弟流落到宜宾西郊的贫民窟,为了活下去,她把那枚当年价值五千大洋的钻戒卖了,把那些法国香水和漂亮衣服都卖了。
等到这些东西都卖光了,她不得不去做小买卖,甚至沿街乞讨。

那个曾经在宜宾最繁华地段招摇过市的女人,变成了一个人人嫌弃的疯婆子。
这种心理上的落差,比肚子饿更折磨人。
在那样的乱世里,她以为美貌是免死金牌,殊不知所有的馈赠,命运早已在暗中标好了昂贵的价格,而且是利滚利的那种。
短短几年时间,那个曾经风华绝代的女人就迅速衰老,看着跟六十岁的老太婆没两样。
一九六一年的那个冬天,估计是她这辈子最冷的一天。
病得快不行的她,想去成都投奔亲戚,这大概是她求生的最后一点本能了。

但死神没给她这个面子。
她在宜宾火车站停止了呼吸,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哭声,甚至连张像样的纸钱都没有。
她的一生,就像是一场绚丽又荒诞的烟火,在旧时代的夜空中炸了一下,然后在新时代的晨曦里成了灰,风一吹,啥都没剩下。
参考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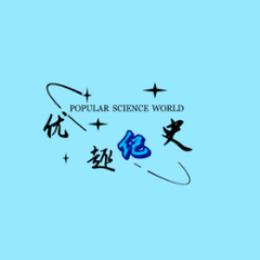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