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世界里,有一群至关重要却常常隐于幕后的人——剪辑师。他们鲜少在红毯亮相,却能让演员的表演更动人;他们鲜少面对媒体,却可能比导演更清楚每个镜头的前世今生;他们不编写最初的台词,却可能决定了一句对白在何时落地,能激起千层浪。
当我们谈论一部电影时,总会提到导演的构思、演员的表演、摄影的画面。但你是否想过,那些让我们屏息凝神的情节转折、恰到好处的情绪爆发、行云流水的时空转换,究竟是如何实现的?这一切都离不开剪辑师。面对堆积如山的原始素材,用近乎外科手术般的精确与诗人般的直觉,重新裁切、拼接时间,最终赋予故事以呼吸和心跳。
“剪辑,无疑是电影制作流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始终是结构电影最基本的语法”。它远非简单的镜头拼接,能让平淡化为神奇,在方寸之间重塑影片,甚至脱胎换骨。
作者: 周新霞 主编 丨姜富海、林鸿飞、王姜永 编著
出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丨后浪
出版年: 2025-12
丛书: 后浪电影学院
ISBN: 9787221186553
《一剪光影:华语电影金牌剪辑师访谈录》——一部系统梳理剪辑师群体创作经验、深入揭示华语电影核心创作环节的著作,由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历时7年精心策划编纂,正式出版。本书由一级剪辑师、中国电影剪辑学会会长周新霞担任主编,她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代表作包括《潜伏》《大阅兵》《横空出世》《荆轲刺秦王》《红粉》等)为本书奠定了坚实的实践与学术根基。这并非一本单纯的技术手册,而是一部以人为鉴、以史为脉的华语电影剪辑艺术深度记录。
《一剪光影》全面聚焦两岸三地25位金牌剪辑师,首度公开重量级华语电影制作内幕。受访者们是张艺谋、陈凯歌、王家卫、徐克、侯孝贤等大导演的得力伙伴,参与书写了《霸王别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悲情城市》《阳光灿烂的日子》《站台》的影史传奇,见证从手工匠艺到工业体系的技术演进与代际传承;从《三毛流浪记》的胶片剪接台,到《流浪地球》的数字工作站,他们始终是银幕时空的“隐形建筑师”。
这些幕后英雄带领我们直击名场面的诞生现场,畅谈力挽狂澜的神奇时刻与“熬夜再改N版”的艰难取舍,无私分享数十年积累的宝贵实战经验。其中,既有独门技术干货,也有集体合作秘诀和行业生存智慧。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著名剪辑师廖庆松是如何分享他的剪辑之道:

Part 4 “ 影片才是最后的真相”
我接到一个片子会先看剧本,这是一定的。然后再去看实际拍成什么样子。像现在, 我接的片子基本都会是final cutting(◎终剪)。我一定要看最初的顺剪版本和最终的剪辑版本,这是因为顺剪版可以让我知道他拍了什么,而最终版可以告诉我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比较两个版本,你会发现最终版一定会有取舍。可这样的取舍是不是对?那就会有不同观点。这时就需要对照原始剧本和影像去判断。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影像,还是要看导演拍了什么。这时的剧本已经变成影片,而影片也已经融入了导演的思考。所以我们最终要面对现实,要判断影片中哪些传达得好,以及最重要的是什么。毕竟,影片才是最后的真相。
比如我剪过一部电影叫《爱你爱我》,导演是林正盛。影片真正的原始构想,是要拍槟榔西施后面的黑社会,讲卖槟榔的女孩子后面有控制她的势力。可问题在于导演本身不像侯导有过相似的生活经历,所以你看他拍摄的黑社会部分,会感觉很多都不对劲。那我就要决定是按照导演的想法去剪,还是做出改变。大概因为我剪习惯了很多侯导关于黑社会的片子,由于他本人对这样的环境比较了解,黑社会的场景就很真实。我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受到他的影响,所以最后我就把《爱你爱我》里面不真实的黑道部分全部拿掉了。这样做虽然违背了导演原本想要表达的事情,但从剪辑上来说,却把影片的优点剪了出来,把缺点抹除掉。当时我也曾跟监制沟通过,我说剪辑师去改一个影片纯粹是他的个人意见,是否采纳其实应该是监制同导演去讨论的,我不会去强行坚持,尤其现在是用数码剪辑,每个人剪的其实只是一个方案,完全没必要争执,谁有意见就去剪一个版本,大家去看哪一个更适合。不过那部影片确实就是林正盛去柏林拿到最佳导演的影片。

我常拿《悲情城市》举例子,当年这部影片全片应该是200 多场。剧本很厚,可是侯导只拍了一半,这就导致在剪辑时会时不时出一个窟窿,因为有些段落完全没拍。我跑去问他为什么这么多场不拍,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他觉得很啰唆。没办法,我只好去研究他的画面,因为他都是长镜头拍摄的,我想也许我可以把每一场戏都当牌来打,也就是说我可以重新排列。于是我做一个处理,我叫它“诗化”,就是把影片处理成诗的感觉。这样一来,画面语言上就可以跳跃。另外,由于他都是长镜头拍整场,所以我怎样跳故事都不会讲错。坏处是人家可能会看不懂,好处是这样处理整个片子味道会很立体。
像影片中“台湾光复”的段落,剧本里面大概有几十场,可他只拍了一半。我就用这一半来拼出这个感觉,首先不用在意情节走向,其次让影片像诗一样。就像每一句诗都是一个单独的场景,这反而会让观众觉得很有味道。没有所谓情节,那观众就没有必要去接情节,他就只能一场场去感受。而且场跟场之间会有跳动,倒装得非常厉害。
这种感觉很像元代诗人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的“枯藤老树昏鸦”。你如果说“在黄昏,一棵缠满枯藤的老树上落着一只乌鸦”,这就是情节。可是只用三个名词,它就变成了一首诗。
用这样的方法,我就可以省略很多东西。比如辛树芬被用轿子带上山,实际上里面还有很多情节的,像是她报到、当护士啊,等等。但侯导都没有拍,那我就从她上山直接跳到宿舍跟梁朝伟见面的部分。这样一来,场次就被我抽掉很多,但接起来却更有力量。这中间的断接要靠观众用想象力去补充。虽然每一场断掉后你又看到一个新的情境,不过从整体看,它们却共同讲述了一个大时代的转换。这就变得像诗一样有味道。当你省略掉之后,焦点就会变得集中,不是集中在梁朝伟或是辛树芬身上,而是集中到那个时代上。而对于影片来说,那个时代才是最重要的。
后来侯导也说,事实上导演有能力拍下所有细节,但你要选择想要表达的部分,就像诗人或是作家,只用几个字去传达。如果讲他起床、刷牙、走路、搭公交车,那就变成了流水账。反倒是概括一下、拼凑一下,就会很有味道。
Part 5 “ 找到限制才会找到自由”
实际上拿到一部影片,通过对影像的基本了解,你就可以在心里形成一个“picture”。而且这个“picture”是会变的,它有时是海报,有时是角色,有时是状态,有时也会是一种形象。
比如《蓝色大门》,对我而言它就像一个小水晶球。我还曾跟焦雄屏讲,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可爱的小水晶球,就是拿起来透过阳光看会闪闪发亮的小水晶球。焦老师当时听不懂什么小水晶球,结果她带着片子去国外走了一圈回来,我问焦老师它是什么,她说对了,它就是小水晶球!实际上这个概念是我在剪辑时感受到的。大家现在看影片,陈柏霖的角色是一个阳光男孩,但实际上导演拍的不完全是这样。这个小男孩还会跟其他同学坐在学校宿舍顶楼的水塔上,去聊女孩子。聊的似乎是那个年龄男生对女生的喜好,可是讲出的话却让我觉得对女生有一点不敬,更像三姑六婆在讨论女生一样,所以这些就被我全部剪光,我要保留小水晶球的气质。这是因为我最初看完影片,看到桂纶镁对一个女孩子有了性启蒙的感觉,我就觉得它像一个水晶球般可爱。可是那些男生凑过来,就会让小水晶球里有杂质。我不想让小水晶球有瑕疵,于是陈柏霖的角色就被我做了一个限制性的动作,把他的一些戏剪掉了。但更少的表达反而更完整,这个角色反而让观众定位得更清楚。

电影《悲情城市》(1989),侯孝贤导演,廖庆松剪辑
我对《悲情城市》里陈松勇的角色也做了这样的处理。原本他演了很多戏,但最后我只留下了大概1/3 到一半的样子。因为少,反而好,反而让人物更立体,也更接近我心中影片的调性。所以《悲情城市》在我看来会是一首诗的形象,《蓝色大门》则会是一颗小水晶球。
这个“picture”其实很复杂,有时是实物,有时是一句话。不同的影片会给我不同的感觉,而这个感觉就是我定剪时想要呈现的感觉。
原则上来说,表达得越少,观众越会有想象空间。表达得少,不代表表达得不完整。十分里你只讲三分,剩下的部分,观众就会透过情节、张力或是情感,把很多东西自己补充起来。
《海上花》里很多转场的空白,就可以留给观众去做更多的补充。事实上,《海上花》原计划是在上海石库门拍摄的,结果剧本没通过,最后只能在台北拍。我们做了一个场景,把里面全部改成《海上花》的内饰。这个场景是实做的,不是影棚,真的是花了很多钱。但遗憾的是没有外景,在台北又不可能拍到《海上花》的外景。这么一来,在剪辑时面对场景之间的转换, 我就没有办法了。当时我用Sony 的剪辑机来剪Betacam 磁带。于是我就在剪辑机上找了一条最长的“fade-in”(◎淡入)和“fade-out”(◎淡出),大概有十几秒。我说这个就像是幕起、幕落,最后影片就变成了一幕幕的样子。其实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故事和情绪的段落起止,否则观众一定会混乱,因为这中间都没有外景隔开。索性就用了一个类似舞台剧的感觉,让它很悠长地慢慢fade。事后我也反思过这件事,我发现没有外景便没有干扰观众去捕捉人物状态,这反而会让大家更集中在一个空间里去看人物的生活状态。包括我自己后来看片子也是这样的感受。后来我也跟侯导聊过,我觉得找到限制才会找到自由。像《海上花》,其实是因为受限制,才有这样的“long fade-in”和“long fade-out”。此前没人会用这么长,没想到这样一来反而会让人觉得这个味道很好玩。

电影《海上花》(1998),侯孝贤导演,廖庆松剪辑
我经常跟学生讲,看完一部影片,绝对不要把看到的一场戏仅仅当作它本来的样子。你去看一个镜头,不能看它在分场中的位置。你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元素,你需要考虑的是你从这个元素中能看到什么。比如你用颜色角度看,它是红色,灰色,还是其他?你再用情感角度看,它又是什么?你最不应该用情节角度看,因为那样最简单。你应该更多地看到这个镜头的元素特性,这样才能判断出你剪到哪里时可以用到这个元素。如果这样做,你就不会被情节限制,不会把一个镜头归纳到第几场第几镜,就不会在剪辑上把自己锁死。
我认为剪辑师要有这个修为,不然就没办法看到新的关系的形成。而一旦你把镜头当作元素,那就可以做太多处理。你可以修辞,可以排列,可以变化。你会发现它可以是句子里的一个字,也可以是单独一个字就完成了完整的表达。
对剪辑来说,其实只有到剪辑台上才能知道哪个镜头是最好的。我记得剪《悲情城市》时,发现少了一个镜头。我去问候导,他说没有了,只剩下一些NG 镜头。然后我就去把那些放在角落里大概一两万尺的NG 镜头拿出来看。结果我从里面找到大概二三十尺接了进去,而且这二三十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镜头。另外,在剪《踏血寻梅》时,改完后,我跟导演翁子光说,我觉得最后少了一个女主角春夏的镜头。他想了好久说,只拍了一个春夏在楼上一边晒衣服一边唱广东歌的镜头。我说你给我看一下,结果真的很神奇,那刚好就是我要的镜头。
采访手记(出自作者团队)
廖老师从业 47 年,剪辑了太多经典作品。而且除了剪辑,也曾担任编剧、导演、制片。用他的话讲,感觉职业生涯像是一个拉镜头。自己从剪辑这个点出发,慢慢拉出,从而看到电影的全貌。
廖老师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爱称“廖桑”,这是源于当年常去日本做后期,日本同行对他的敬称。据说后来侯孝贤导演也曾调侃他,说他已经老了,不再是小廖了,可以喊他廖桑了!
那天在我们访谈的最后,谈及此事的廖桑还会心有不甘。他说现在特别喜欢别人叫自己小廖,因为听起来就很年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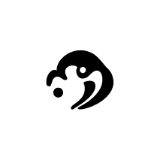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