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100道古代美食》“彩蛋”,再次迎来曹雨老师——这位既是大学教授,又是写吃的一把好手的人类学家,要带我们开启一场以臭为美的“双鲜重叠之旅”。
《浮生六记》里看似娇嗔的闺房“对抗路”对话,背后竟藏着中国发酵文化的关键转折点线索?曹雨老师从爱情讲起——看沈复新婚的一则饮食故事,如何串起中国人食臭的历史脉络。
温馨提示: 本篇文章可能会有嗅觉风味冲击

《浮生六记·闺房记乐》中,沈复回忆新婚生活,有一段极生动的饮食场景:
其每日饭必用茶泡,喜食芥卤乳腐,吴俗呼为臭乳腐,又喜食虾卤瓜。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恶者,因戏之曰:“狗无胃而食粪,以其不知臭秽;蜣螂团粪而化蝉,以其欲修高举也。卿其狗耶?蝉耶?”…… 以卤瓜捣烂拌卤腐,名之曰“双鲜酱”,有异味。余曰:“始恶而终好之,理之不可解也。”
芸曰:“情之所钟,虽丑不嫌。”
芸娘“喜食芥卤乳腐”“又喜食虾卤瓜”,在沈复眼里,是“生平所最恶者”,甚至要拿狗、蜣螂来打趣。可在短短数句拉扯之中,他们从“你是狗耶?蝉耶?”、“我家系狗窦耶?”这种带着讥讽的玩笑,一路走到“以箸强塞余口”,再到“从此亦喜食”,最后落在那句极见性情的话:“情之所钟,虽丑不嫌。”
这段小小的“饮食攻防战”,一方面展现了闺房里的情趣与默契:沈复自诩“调其言,如蟋蟀之用纤草”,以为自己是拨弄芸娘情绪的那一方;可等到吃臭乳腐、虾卤瓜时,真正被一点点“调教”的,却是他自己。另一方面,也是在极日常的饭桌上,把“臭”与“美”的关系摆给读者看:那些在旁人看来“丑恶”的滋味,在习惯者、爱好者心中,却自有其“异味之美”。
“双鲜酱”,正是在这样的情感互动里诞生的:一边是来自芥卤乳腐的“异香”,一边是虾卤瓜中鱼露、虾油的鲜腥,两种“丑味”叠加在一起,被芸娘轻描淡写地命名为“双鲜”,既是口味判断,也是某种温柔的价值翻转。


要理解“双鲜酱”,得先看清两样“底味”:
所谓“芥卤乳腐”,就是浸泡芥菜卤的臭豆腐,与今天流行的臭豆腐做法并无二致,只是现代的臭豆腐一般用苋菜卤泡,而这里是芥菜卤,想来味道应无大差别。
芥菜卤从明代至今都非常流行,也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其名首见于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称“此卤嘉兴府城中大家多藏之”,后又有倪朱谟《本草汇言》记载,《随息居饮食谱》中亦有:“腌芥卤煮食物,味甚鲜美。若坛盛埋土中,久则清澈如水,为肺痈、喉证神药”。据我的考证,芥菜卤的主要原材料是雪里蕻,因其长期腌制后可能产生青霉素,所以对肺炎有疗效,原产地在嘉兴天宁寺。

“虾卤瓜”则是虾油卤瓜。这种做法今天也很常见,环渤海地区的虾油,通常的用法就是腌各类小菜。江南地区如今用来腌鸡、鸭肉比较多,但腌瓜也非罕见。以虾油、鱼露这种高鲜度发酵调味料,去浸渍脆口瓜类,本身就有“一物引一物”的加乘效果——腌得久了,瓜吸入海味,虾油也得了瓜香。
在芸娘那里,这两样“穷人家的下饭菜”—— 一件来自陆地雪里蕻的芥卤,一件来自水里虾油的卤瓜,一“臭”一“腥”,对她的味蕾与记忆构成了很深的安慰。“腐取其价廉而可粥可饭,幼时食惯”是童年的日常,是贫家也能端得上的一碟小菜。
沈复初见,只觉“狗食”“蜣螂之物”,与其说厌恶味道,不如说厌恶的是那种与自家阶层气质不相配的“下里巴人”的气味。
直到被芸娘一筷子“强塞余口”,在“掩鼻咀嚼”“开鼻再嚼”的两重体验之后,他才开始意识到,这些带着“臭气”的东西之中,藏着另一种“脆美”“异味”。这才有了后文更精细的搭配:“以麻油加白糖少许拌卤腐,亦鲜美”。
也就是说,芸娘并不是“凑合吃”的那一方,而是极懂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把发酵出来的臭、腌渍出来的鲜,调和成一碗有结构、有层次的“贫家酱料”。


在这基础之上,才有了“双鲜酱”的诞生:“以卤瓜捣烂拌卤腐,名之曰‘双鲜酱’。”
技法上看,“双鲜酱”和绍兴一带的“蒸双臭”、广东人以虾酱蒸鱼、碎肉蒸蟹,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以鲜叠鲜的做法。浙江人用虾酱蒸臭苋菜梗,或是以臭冬瓜蘸鱼露,大概也是这样的味道,也是鲜味加乘的效果。
不同的是,“蒸双臭”用的是同一谱系的异香:臭豆腐、臭苋菜梗、霉千张、臭冬瓜、臭芋艿蕻,这几种臭食的臭味都是一类,就是绍兴人经常说的“异香”,闻起来吃起来味道倒也和谐不悖。

“双鲜酱”则是把两种不同谱系的臭味叠在一起:一个是臭卤发酵出来的“异香”,一个是鱼露虾油带来的鱼腥鲜,用芥卤乳腐打底,再把虾卤瓜捣烂拌入,既有豆类发酵的乳香与氨味,又有海产发酵的腥鲜与咸香。两种臭路数交缠在一起,才会让沈复觉得“有异味”,既非单纯的“难以忍受”,也不是习见的“家常好味”,而是“始恶而终好之”的那种复杂。
在这意义上,“双鲜酱”并不是一碗“将就”的穷酸料,而是极用心、极有创造力的家常发明。在厨房极有限的库存里——一坛芥卤、一缸虾油、几块乳腐、几只腌瓜——芸娘通过“捣烂”“拌和”“起名”,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味觉体验。
她给这碗酱取名为“双鲜”,其实也是给自己的一番饮食哲学命了名:一切在旁人看来“丑”的东西,只要被情感所“钟”,就都可以是鲜的。

芸娘与沈复是表亲关系,但家境不如沈复,有吃茶泡饭和臭豆腐的习惯,可见在那时臭豆腐也是中小层民众的饮食。
廉价、耐放、能“可粥可饭”的臭乳腐与卤瓜,放在十八世纪的江南消费结构中,属于极典型的“底层调味”:一碗稀粥、半碗冷饭,有了这一小碟,便能“添味”,也能添一点尊严——不是单纯为饱腹,而是可以在味道上争一口气。
从更大的发酵谱系来看,“双鲜酱”站在豆类与鱼虾发酵的交界处:
一边连着芥卤乳腐、臭豆腐、蒸双臭这些臭卤系豆制品;
一边连着虾油卤瓜、虾酱蒸肉、鱼露蘸菜这些鱼虾酱类。

臭卤的流传路径,大致从绍甬一线往太湖流域,再随商业流动逐渐扩展到长江中游;芥菜卤则以嘉兴天宁寺为原产地,在明清文人笔记与医家本草中频繁登场;虾油、鱼露则在沿海、沿河的渔村市镇普遍存在。
芸娘的一碗“双鲜酱”,把这两条技术–地理谱系,在一个普通人家的饭桌上对接了起来。
味觉记忆层面,“双鲜酱”里的鲜,则是“幼时食惯”的鲜:那是贫家女孩从小吃到大的臭乳腐,是嫁入夫家后才尝到的虾卤瓜,是从娘家到夫家的味觉迁移,也是她用来“循循善诱”丈夫的工具:先是“妾亦强啖”蒜以迁就他,继而“箸强塞余口”,让他在掩鼻与开鼻之间,学会品鉴这类“臭食中的鲜味”。

当沈复感叹“始恶而终好之,理之不可解也”的时候,他说的是味觉经验的自我颠覆;芸娘回以“情之所钟,虽丑不嫌”,说的则是情感如何改变审美阈值。
“双鲜酱”的意义,恰在这“理”与“情”的交错处:在理智层面,它承载着豆发酵与鱼虾发酵两条工艺线索的叠加;在情感层面,它则是夫妻二人从阶层差异、口味隔阂,到共享一碗“异味”的过程见证。

如果把视野再拉远一点,会发现“双鲜酱”正好卡在中国发酵文化的一个关键时间点上:
芥菜卤最早文献记载出现在1622年,而《浮生六记》中提及吃芥卤乳腐之事时间当在1784年前后。芥卤出现的时间大致可以推定在17世纪,而以芥卤浸泡得到臭豆腐,当在18世纪。

也就是说,芸娘这一代人的厨房,正是在这些新近发明、快速扩散的发酵食品的包围中长大的。
腐乳从毛豆腐雏形发展而出,时间大致在17世纪;臭豆腐大概在18世纪以后从绍甬一带流行起来;臭卤、雪里蕻的腌制技术在江南广泛普及。在这样的技术–时间背景下,“以卤瓜捣烂拌卤腐”就完全不是偶然一试,而更像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叠加操作”。
农家本就习惯把各种腌菜汁拿来煮食、入药;把豆类发酵品与鱼虾发酵品叠在同一碗小菜之中,是极自然的味觉实验。换句话说,“双鲜酱”不是一时兴起的“怪味创意”,而是十八世纪江南普通人家在发酵世界里做小小排列组合的成果。它既不走御膳房那套“山珍海味”的路,也无意成为“名菜”;它更多只是闺房之私、夫妻之间的默契:
一人从“恶”走向“好”,
一人把“丑”转成“鲜”,
一碗酱,成了他们共同的“口味记忆”。

我们今天再回头去读这一段,或许可以把视线暂时从“臭豆腐是谁发明的”“虾油传到哪里去”的宏大叙事上移开一点,多看一眼芸娘的那只小碗:她把童年的味道、娘家的贫寒、江南发酵术的精巧,以及对爱情的笃定,都搅进了这碗“双鲜酱”里。
于是,一切“丑味”,都变成了“情之所钟”的异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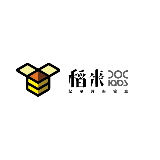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