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重返狼群》的故事再次回到大众视野,格林与李微漪伟大的跨物种情谊令我们的动容。但这种故事或许在迎合或者说强化某种关于狼的迷思——狼只属于旷野,狼的“天性”让它不适合也不应该生活在人类社会中。
这个稍显打破常规的观点来自另一位与狼相伴者罗兰兹,他养大了一头叫布雷宁的小狼,布雷宁的一生都在人类社会里度过,他们一起打球、上课、泡吧、在各个国家旅居。狼是否一定属于狼群?对于这个问题,《哲学家与狼》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来自另一种视角的思考。

有的人认为训练狗,甚至说训练狼是残忍的,就好像打破了它们的灵魂,或者使它们被永远地恐吓住一样。但与此相反,当一条狗或狼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信心会大大增长,随之而来的,也会更为镇定。就像弗里德里希·尼采说出的不太悦耳的真相,那些不能够约束自己的人,很快就会被他人约束。而对于布雷宁来说,我的责任就是做那个“他人”。不过约束与自由之间的联系是深刻而重要的:约束并非与自由相对立,自由的最有价值的形态在约束中成为可能。没有约束,就谈不上真正的自由,留下的只能是放纵。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我们总能在散步时遇见有些狗主人牵着他们的狗——通常是哈士奇或者爱斯基摩犬这样类似狼的犬种,并解释说如果不这样,狗就会冲到远处,很难再把它们牵回来,甚至可能就此再也看不到它们了。这很有可能是真的,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如此。那之后,在我们住在爱尔兰期间,每天都会从田间的羊群中走过,这时布雷宁也是没被牵着的。我承认,第一次这样尝试的时候,自己还是有点紧张的,尽管也许羊儿们比我更紧张。而在我们相处的整个过程中,我从未对布雷宁大喊过,也从未打过他。我十分确信,如果一匹狼可以被训练得完全无视命定的猎物,那么狗也可以被训练得呼之即来。
布雷宁将继续着这样一种对于狼来说前所未有的生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能够将他带到任何地方,而我也确是这样做的。诚然,这样做是因为考虑到在我因讲课而不能照顾他的早晨里,他有足够的精力让我的房子变成瓦砾。不过,我们之所以能一同过着如此有意义的生活——而非把他圈在后花园中并将他遗忘——全都得益于他学会了一种语言。若不是这种语言,他绝不会拥有这样一种生活结构,也因此绝不会得到满满的可能性。布雷宁学会了这种语言。而既然他已经要在这样一个充满奇迹,而非机械性的人类世界中生活,这种语言让他获得了自由。

当然,前所未有的生活并不一定就是好的。经常有人这样问我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怎么能把一只动物从自然环境中带离,强迫它过一种完全非自然的生活呢?问这种问题的往往是这样一类人 :自由派中产阶级学者,以生态主义者自诩,却从没有养狗的经历或相关知识。不过抛开对问这些问题的人的中伤,只看问题本身,也就是避免在哲学中所谓“诉诸人身”(adhominem)的谬误。这个问题本是一个很好的、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我觉得我得指出,布雷宁并非出生在野外,他生下来就带着束缚。如果没有父母的训练而将他放生到荒野,他一定会很快死去。不过这并没有很好地为我开脱。从付钱买下布雷宁起,我就在维系着这样一个在束缚中哺育狼的系统,如此一来,便剥夺了他依本性生存的机会。所以现在,问题变成:我怎样证明这样做的合理性?
我认为,这个问题预设的是:狼只有在做自然需要它做的事时(进行捕猎或与狼群的其他成员互动等自然行为),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或满足。这样的主张也许看起来明显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很难解释清楚。首先,“自然的需要”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自然需要狼来做什么呢?或者说,自然需要人来做什么呢?确实,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说自然在需要什么呢?根据进化论,我们有时候会用比喻的方式来说自然需要什么,但这种讨论从根本上来说归于这一点 :自然要求生物传递它们的基因。我们所能为“自然的意图”赋予的实在的意义,也只仰赖于基因成功的概念。像狼这样的动物之所以会选择捕猎与群居生活的策略,也是为了满足这种基本的生物需要。然而,即使是狼,也可以采取各种不一样的策略。在历史发展的某一个节点上,由于尚不明了的原因,狼融入了人类群体,变成了狗。就“自然的意图”而言,这就是其意图的一部分,同狼继续为狼没有什么不同。

我从哲学中学到了这样一个有用的技巧 :当某人下一个断言的时候,要试图去发掘这个断言的预设前提。因此,如果有人说,狼只有在参与符合自然本能的活动时,例如捕猎、群居,才能够过得快活的话,那么这种断言的预设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我们看到的也许是——至少就大部分而言——对人类的傲慢的表达。
不过我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存在的灵活性”(existential flexibility)这样一个整体的概念。为什么是人,且只有人,有能力过形形色色不同的生活,而其他生物却生来注定成为遗传法则的奴隶、自然历史的仆人呢?除了一种残存的人类傲慢,还有什么可以作为这种想法的基础呢?几年前,在预备一大早飞往雅典的前一个晚上,当我坐在位于盖特威克机场的一个旅馆的露天啤酒馆里时,一只狐狸走近我,像一条狗一样坐在离我不过几英尺远的地方,耐心地等着我扔些什么食物给它——我当然这么做了。服务员告诉我,它是这个旅馆里的常客——显然也经常光顾其他旅馆。那么,请你试图告诉这只狐狸它的天性要求它捕捉老鼠,或者告诉它,与我们不同,它的本质先于存在,也并不会为存在而存在。
当我们认为狐狸的自然本性只限于捉老鼠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贬低它。当我们对它们的存在怀有这样一个局限性的想法时,实际上低估了其机智与随机应变的能力。狐狸的天性是随着历史与命运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因此,其存在,也就是狐狸的本质,也在随之改变。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排除自然历史的限制。倘若把一只狐狸日复一日地关在笼子里,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到快活或满意的。狼也不能。换作我也一样。我们都有某些历史赋予自己的基本需求。但若因此说狼与狐狸只不过是披着动物皮毛的提线木偶,任凭历史来操纵系在它们身上的线,这种推论是没有道理的。它们的本质也许限制了存在,但并没有决定后者。就这一点来说,狐狸、狼与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像是在打发到自己手中的牌。有时这一手牌太差劲,我们对之束手无策。有时则并非如此——然后要看个人的发挥。如今发到狐狸手中的牌便是,急速的城市扩张占据了它原有的自然栖息地——尽管这个术语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了。我想,我的这位狐狸朋友,就将这手牌玩得相当出色,这一点仅从它在桌间穿梭的方式就可以判断——它只在有食物的桌旁停留,然后耐心地坐着,直到获得需要的东西。
布雷宁同样玩着命运发给他的那一手牌,而且我觉得他玩得相当好,至少那牌并不糟糕。他本可能会像其他狼或者狼狗那样,因难以驯服而最终被关在笼子或后院。但与此相反,他过着多样而丰满的生活。我保证他一天至少有一次长时间散步,而且由于训练过,我完全不需要牵着他。如果环境允许,我会让他参与一些符合自己天性的活动,比如捕猎,或者与其他犬类交流。我竭尽所能不让他感觉无聊——不过不包括听我的课这种恼人的日常工作。那种认为“布雷宁会因没有做野生狼该做的事情而不开心”的观点,只不过是人类傲慢心理的一种陈腐的表现形式,它完全轻视了布雷宁的聪明与灵活性。当然,布雷宁是追随着他一万五千年前的祖先的脚步,响应着文明的召唤,与猿类中最强大也最堕落的一支缔结了共生的,甚至是牢不可破的关系。站在遗传的角度来看,你只需要对比一下目前狼与狗的数量——粗略来看是四十万比四亿,就能知道这个策略是多么惊人的成功。认为狼依附人是一种非自然的选择者,这种观点只能暴露出他们对“自然”的浅薄无知。考虑一下野生狼那短暂的寿命——七年已经相当长了——以及通常而言的,它们悲惨的死法,文明的召唤真的并非全然的灾难。
以上节选自《哲学家与狼》
图片为纪录片《重返·狼群》剧照及截图

哲学家与狼
作者:[英]马克·罗兰兹
译者:路雅
出版时间:2025年10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作者简介:
马克·罗兰兹(Mark Rowlands),英国人,牛津大学哲学博士,美国迈阿密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多部哲学畅销书,如《动物权利》《宇宙尽头的哲学家》《跑着思考》《像狗一样快乐》等。
内容简介:
小狼布雷宁与哲学家马克·罗兰兹11年来朝夕相处,他与罗兰兹一起生活,一起玩耍,甚至在罗兰兹的大学课堂里打盹。他作为狼的生命不断刺激罗兰兹反观作为猿猴的自己,将生命的真实瞬间从人类的傲慢、计算和贪婪中打捞出来。
“他便是那抹光亮,让我得以在阴影中看到自己”。
- End -

成为更好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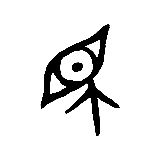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