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达利 #

。。。
“当我每天早晨醒来,”这位绘制了软化的时钟和燃烧的长颈鹿的画家写道,“最极致的喜悦就是我是萨尔瓦多·达利……”达利,一个痴迷名利的加泰罗尼亚人,画得不少,说得也多。他最爱的话题就是“如何成为天才”。他炮制天才的菜谱如下:“噢,萨尔瓦多,你现在该明白真相了;只要你扮演天才,就会成为天才!”

自画像
Self-Portrait
约1920年,布面油彩,52 cm×45 cm
私人收藏
“大胡子先生”(达利的绰号来自他醒目的鬓角)被画在印象派风格的卡达克斯海岸前,这片岩石海岸在达利艺术生涯的各种作品中反复出现。
6岁时,他想要成为一个“厨娘”,并坚持要用这一名词的阴性形式;到了7岁,他又想成为拿破仑。“自那时开始,”达利后来回顾道,“我的野心就稳定地增长,我的自大狂妄也随之增加。现在我只想成为萨尔瓦多·达利,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愿望了。”在这段早年生活中,他还画了人生中的第一幅画。此后,在10岁时,他发现了印象派;14岁时,则邂逅了“消防员派”,即19世纪的学院派艺术。在 1927 年,时年 24 岁的他已经成为著名的达利,他童年的好友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为他题献了一首“教诲颂”。多年之后,达利声称洛尔迦为他神魂颠倒,说洛尔迦曾试图与他发展同性恋情,却不太成功。达利身上总有丑闻的气息!他的父母为他命名为萨尔瓦多(西班牙语意思为救世主),因为——以这位艺术家本人的话说——他注定要成为绘画的救世主,而此时的绘画“正承受着抽象艺术、学院派超现实主义、大部分的达达主义及各种无政府‘主义’的致命威胁”。

大提琴家里卡德·皮乔特的肖像
Portrait of the Cellist Ricard Pichot
1920年,布面油画,61.5 cm×50 cm
菲格拉斯,加拉—萨尔瓦多·达利基金会
达利采用画家波纳尔描绘亲密关系的风格,为他正在拉大提琴的邻居兼好友绘制肖像,年轻的他已经显示出对多种绘画风格的掌握。
如果达利生于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天才可能会更易被接纳,甚至被归为正常。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一个被达利称为“患了白痴病”的时代,他永远是个挑衅者。尽管现在达利被认为是现代艺术中一位真正的伟大人物,地位比肩毕加索、马蒂斯和杜尚,尽管达利成功地魅惑了普罗大众,赢得了人们的欢心,但是他的作品仍然使人震惊。面对达利,许多人仍想大喊“疯狂”,但达利本人却坚持道:“我和疯子的唯一区别在于我没疯!”还有一件真事,如达利反复强调的那样,“我和超现实主义者的唯一区别就在于,我是个超现实主义者”。正如莫奈是唯一贯彻始终的印象主义者一样(莫奈的伙伴后期分化成了立体派、点彩派或野兽派),达利始终是最忠实的、唯一真正的超现实主义者。虽然他也这样描述自己:“他思维的石磨转动不休,像文艺复兴之人一样拥有对万事万物的普遍好奇。”
米歇尔·德翁在达利的《天才日记》前言中写道:“人们自以为了解达利,是因为他凭着极大的勇气决定要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记者们贪婪地吞食着他所提供的一切,但最终,达利最让人惊讶的却是他那朴实明智的感知,正如那个场景一样:一个年轻人想要知道成功的秘诀,却被建议吃鱼子酱、喝香槟,以免像个按日计薪的零工一样埋头苦干,死于饥饿。而达利最棒的莫过于他的‘根’和‘天线’。他的‘根’深扎于地下,寻找40个世纪以来人类在绘画、建筑和雕塑领域中所能创造的所有‘多汁美味’的养分(用达利最爱的三个词汇之一来说)。他的‘天线’则直指未来,以闪电般的速度捕捉各种振动、预判和解读。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达利拥有无法被满足的好奇心。他的所有发现、发明都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只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简而言之,达利,正如公众已充分认可的那样,完全能代表他的时代,哪怕只是在把自己打造成“明星”这一点上。
但达利同时也是一个加泰罗尼亚人。他自视如此,坚守身为加泰罗尼亚人的特权。他于1904年5月11日出生在赫罗纳省的小镇菲格拉斯。后来,他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庆祝了这件喜事:“让所有的钟鸣起来!让辛勤劳作的无名小农直起他僵硬的后背,他的背总像橄榄树干一样躬向泥土,因特拉蒙塔那风而扭曲弯折;让他沟壑纵横、沾满泥土的脸颊能以高贵的姿态躺在他长满老茧的手里,短暂地陷入沉思歇息,看啊!萨尔瓦多·达利刚刚来到了人世!……希腊人和腓尼基人一定就是在这样的早晨登上了罗塞斯和安普里亚斯的海湾,为我的出生准备文明之床和干净白洁、充满戏剧性的床单,一切都安顿在这片恩波达平原的正中央——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具体、最客观的一片风景。”
达利作品里贯穿始终的一些迷人要素直接来源于他加泰罗尼亚的“根”。据说,加泰罗尼亚人只相信他们能吃、能听、能碰、能闻或能看到的东西。达利毫不掩饰自己唯物主义者的特征和这种传统的加泰罗尼亚口味:“我知道我在吃什么,但我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达利经常引用的一位同胞、哲学家弗朗西斯科·普赫斯将天主教会的扩张比作是一头正在养膘待宰的猪。

记忆的永恒
The Persistence of Momery
1931年,布面油彩,24.1cm×33cm
纽约,纽约艺术博物馆,匿名人士赠予,1934年
著名的“软时钟”,灵感由融化的卡门贝尔奶酪而来。
达利继而也对圣奥古斯丁做了一番达利式的注解:“基督就像奶酪,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堆积如山的奶酪。”在达利的作品中,这种饮食谵反复出现:著名的“软时钟”源于梦中出现的卡门贝尔软奶酪,表现着时间自我吞噬和吞噬万物的形而上的景象;还有无数的《(没放在)盘子里的煎蛋》、《拟人化的面包》、《龙虾电话》,以及《煮熟的豆子的软结构(内战的预感)》。

达利在里加特港,约1950年
德夏尼拍摄
但是,达利身上的加泰罗尼亚传统不仅表现在对食物的热爱上,还可见于出现在他作品中的用心呈现的恩波达平原。对达利来说,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景色,也是他早期作品的主题。达利最著名的一些画作就取景于加泰罗尼亚绵延的海岸线,从克雷乌斯角到埃斯塔蒂特,中间是卡达克斯,都沐浴在地中海独有的阳光里。达利最爱的赘生物,即化石、骨化物、拟人化物以及它们在《性吸引的幽灵》里其他奇怪的“表亲”,都源自被这些元素雕饰过的海岸岩石。这些元素以不同的形式徘徊在达利作品中,不管是以《欲望之谜》中的形式,还是作为隐形的竖琴或冥想用的物品。

站在窗边的人
Figure at a Window
1925年,纸板油彩,105 cm×74.5 cm
马德里,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
在通过学校的结业考试后(这很是费了一番工夫),达利试着劝说自己的公证人父亲让他到马德里艺术学院学习。达利的坚持、他第一位老师努涅斯和朋友皮乔特一家的鼓励,或许还有1921年达利母亲逝于巴塞罗那,种种相加,最终打消了达利父亲的疑虑。失去这个世界上对他意义最为重大的人让达利悲恸欲绝。后来,他写道:“我必须功成名就,抹平痛失挚爱母亲给我带来的羞辱。”

有着拉斐尔式脖子的自画像
Self-Portrait with Raphaelesque Neck
约1921年,布面油彩,40.5 cm×53 cm
菲格拉斯,加拉—萨尔瓦多·达利基金会
但他的导师们让他大失所望。他们仍在探索那些达利早已抛在身后的“最新潮流”。他们着迷于现代艺术,没有向达利传授他所追求的古典主义。尽管如此,达利还是加入了马德里的先锋派,并很快成了这个拥有着佩平·贝洛、加西亚·洛尔迦、路易斯·布努埃尔、佩德罗·加菲亚斯、欧亨尼奥·蒙特斯和拉斐尔·巴拉达斯的圈子里的头号人物。达利在朋友的陪伴下度过了波澜壮阔的两年,其后因煽动同学示威,反对学校任命一位平庸的艺术家为教授而被马德里艺术学院开除——这实在是因祸得福。他回到了卡达克斯,在当地,他一天最多能画到5幅画,因引人注目的鬓角被称为“大胡子先生”,他腰间用一条细绳系住的几支画笔让人从在远处就能把他认出来。《有着拉斐尔式脖子的自画像》就是这个时期的一件作品。从风格和标题来看,这幅作品旨在表达对这位他十分崇拜的著名前辈的致敬。达利的父亲此时对他心有责备,可见于达利的一张铅笔画(《艺术家的父亲和妹妹的肖像》)中父亲的面部表情。达利被学院开除的消息摧毁了这位公证人对儿子取得公职的所有希望。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学院现在对他的儿子来说毫无意义:萨尔瓦多就要成为达利了!
确实,在达利面前,几乎所有时髦的现代艺术潮流都显得如同儿戏。他已然探索过印象主义、点彩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新立体主义和野兽派,这厢才向毕加索致敬,那厢又能向马蒂斯致敬,表现出对各种风格惊人的精通。达利毫不掩饰各个流派给他带来的影响,对各种风格的探索不过意味着他离自己所追求的形象又迈进了一步。它们只会吸引他几周的注意力,之后就会被抛在身后,未曾留下丝毫痕迹,仅余下持续增长的自信。这在《我父亲的肖像》或《站在窗边的人》中都有所体现。

我父亲的肖像
Portrait of My Father
1920年,布面油彩,91 cm×66.5 cm
菲格拉斯,加拉—萨尔瓦多·达利基金会
这位在菲格拉斯赫赫有名的公证人被画在达利最爱的风景之前,显得气度非凡。
说服父亲让自己到巴黎继续学习大概并没有花费萨尔瓦多很多工夫。“一旦到了巴黎,”达利预言道,“我就会攫取权力!”他似乎在巴黎待了一周,大约是 1927 年初,为以防万一,他的姨妈和妹妹陪同前往。据达利自己所言,他在此期间做了三件大事:参观凡尔赛宫和格雷万蜡像馆、拜访毕加索。“曼努埃尔·安吉利斯·奥尔蒂斯是格拉纳达的一位立体派画家,对毕加索的作品保持着紧密的关注,他将我引荐给毕加索。奥尔蒂斯是洛尔迦的朋友,因而我恰好认识他。来到波艾蒂路上的毕加索宅,我就被深深地震撼了,心中充满了崇敬之情,仿佛正在拜见教皇。‘在参观卢浮宫前,’我说,‘我先来拜访您了。’‘你做得很对。’毕加索回答说。”就在同一时期,达利的好友路易斯·布努埃尔向他提出了要拍一部电影的想法,并打算用他母亲提供的资金来拍摄这部名为《一条安达鲁狗》的电影。

装置与手
Apparatus and Hand
1927年,木板油彩,62.2 cm×47.6 cm
圣彼得斯堡,佛罗里达,萨尔瓦多·达利博物馆
这两位艺术家从自己的幻想中截取交错并置的画面,以超现实主义“自动写作”的手法创作出这部电影。布努埃尔曾见过一片碎云飘过月亮和一只被剃刀割破的眼睛;达利则曾梦见过一只爬满蚂蚁的手和一头腐烂的驴子,如他当时的一幅画一样(即《臭屁股(腐烂的驴子)》。他们都同意要将唯一一条简单原则(在往后余生中,达利一直忠于这一原则)作为他们作品的基础:

臭屁股(腐烂的驴子)
The Stinking Ass
1928年,油彩、沙、瓦绘于木板,61 cm×50 cm
巴黎,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蓬皮杜中心
这幅作品预示着达利与布努埃尔共同创作的电影《一条安达鲁狗》中的一组场景。
他们绝不会使用任何易受理性、心理学或文化影响的想法与画面。为非理性敞开大门!他们只接受能给人带来巨大冲击的图像,而不会去探寻根由。达利一边等着要将《一条安达鲁狗》“像一把匕首一样直直地插入风趣、优雅而文明开化的巴黎的心脏”,以打开通向超现实主义圈的大门,一边在巴黎到处寻找“优雅或不优雅的、对我的情爱幻想感兴趣的女人”。在《我的秘密生活:达利自传》中,他写道:“到达巴黎时,我引用一本在西班牙读过的书的书名对自己说:‘要么成为恺撒,要么一文不名!’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在车上问司机:‘你知道有什么好的妓院吗?’……当然,我并没能逐一拜访,但我看了许多,其中有几家给我带来了数不尽的欢愉……现在我要闭眼深思片刻,以挑出三个最为丰富独特,又给我留下了最神秘印象的地点。于我而言,夏巴奈里的楼梯是最神秘而丑陋的‘情色’地点,维琴察的帕拉第奥剧院是最神秘而神圣的‘美学’地点,而埃斯科里亚尔帝王陵墓的入口则是世界上最神秘而美丽的停尸房。是的,对我来说,情色总是丑陋的,美学总是神圣的,死亡总是美丽的。”

《达利》
基础艺术08
[法]吉勒·内雷 著
刘心懿 译
后浪|湖南美术出版社
202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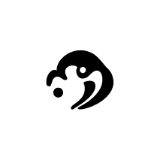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