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晨两点半,急诊科的走廊终于安静了点。我盯着电脑屏幕上那个被退回的申报文件夹,右下角的时间跳动了一下,像是在嘲笑我还没合眼的双眼。
这已经是我申报副高的第三年了。
刚才带教的学生发来微信,问我那个SCI的回修意见怎么改。我回了个“先放着”,关了对话框。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改,那些所谓的数据模型和临床统计,在无数个通宵值班后的脑子里,乱得像一团拆不开的缝合线。

从主治到副高,这层窗户纸到底有多厚?
如果你问一个刚入行的小医生,他可能会说:“不就是论文、课题、学分加上年资吗?”但只有真正卡在这个节骨眼上的我们才知道,这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们究竟在经历一种怎样的“无效努力”。
最让人崩溃的往往不是做手术。手术台上,切开、分离、缝合,每一针都有反馈。可职称评审不是。
为了凑齐那些SCI点数,我曾在下班后钻进实验室,对着那些细胞观察到后半夜,第二天还要强撑着上手术台。手在抖,心在慌,但我不敢停。因为在这个体系里,你救活多少个病人,可能还抵不过一篇发在三区杂志上的实验报告。这种错位感,像极了在旱地里拼命划船。
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继续教育学分。为了凑够分,咱们多少次在开会时偷偷把手机支在角落,挂着视频,人却在处置室里忙得满头大汗?那种“必须完成”却又“毫无所获”的消耗,最是消磨人的心气。
我们都在努力,甚至是在拼命。可这种努力,有多少是真正为了提升医术,又有多少是为了填满那张考核表的空格?
有时候我也会反思,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这种内卷的泥潭?
大概是因为,当我们把“副高”看作唯一的上岸标志时,我们就已经把自己异化成了数据的奴隶。评审体系就像一个巨大的模具,不管你是善于拿手术刀,还是长于问诊,最后都得把自己削成能塞进那个模具的形状。大家都在跑,你不敢慢,哪怕前面是一片迷雾,你也只能跟着人流,透支着发际线和睡眠。

但今晚,看着桌上那叠厚厚的病例,我突然在想,那种“无效”的挫败感,是不是因为我们弄丢了重点?
其实,那些真正在这行里走得远、走得稳的前辈,并不是最会写论文的那个,而是最先从这种焦虑中“松绑”的人。
他们也评职称,但他们更明白,职称只是职业生涯的一个副产品。真正的“有效努力”,是那些在临床中复盘的每一例疑难杂症,是在手术台上对每一个细节的死磕,是那些哪怕没发成文章、却实实在在长在自己脑子里的临床思维。这些东西,评审表不一定看得到,但病人的身体知道,你的同行知道。
副高这道坎,确实难跨。它隔着的,不仅仅是不眠之夜,更是一个医生从“被标准衡量”到“自我定义”的蜕变。
窗外天快亮了。隔壁床那个术后观察的病人翻了个身,监护仪发出平稳的滴答声。
我揉了揉酸痛的肩膀,把那份被退回的文件重新存了个档。生活还得继续,论文还得改,但或许从明天起,我该试着把那份紧绷的焦虑收一收。
毕竟,在成为“副主任医师”之前,我得先保住那个最初想当“好医生”的自己。

走廊里传来了交班护士细碎的脚步声。又是一个新的清晨,希望今天,我们的努力能更贴近一点治病救人的本心,哪怕只是一点点。
你说呢,老伙计?
如果你也正卡在评审的关口,或者正在某个不眠之夜里挣扎,欢迎在后台留言。也许我们可以聊聊,那些表格之外的、真正的医生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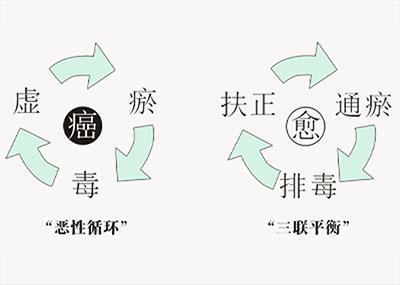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