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打赏回血

关于1984这部著作,本来要解读为20集作为一个连载系列。 但是由于,收到的效果不是那么很好,每期的浏览量也非常的少。所以我就改成了另外一个作品的解读,那就是康德的未来的形而上学导论,因为这不光是在公众号里要创作作品,还要考虑到其他平台的文字创作。然后有小伙伴儿要求我继续更新,说希望我继续把1984这个作品解读下去。当时我的心情很激动,我没有想到这个平台和另外的某些平台。还有这么忠实的小伙伴。对我有所希望。让我感到不胜的惶恐。所以我答应继续把这个系列处理完。所以闲话少说,书归正传,嗯,但是视频我就不创作了,因为那个比较耗费精力。只以文字稿的形式呈现给各位小伙伴,希望大家也能谅解我。


春启万物新生


朋友们,欢迎回到这个灰蒙蒙的、透不进光的伦不论是在这个平台尘、甚至还有老鼠出没的破房间里,搞出了一段所谓的爱情。但这一集,我们要狠心地把镜头从那张温存的破床上拉开。我们要把那些廉价的浪漫、那些以为找到了避风港的幻觉,统统像撕墙纸一样撕掉。因为在第一大洋国的逻辑里,爱情从来不是重点,爱情只是一种作案工具,是多巴胺在废墟里的一次短暂违章。温斯顿以为他拥有了生活。他以为那个慈祥的查林顿老头租给他的房间,是一个可以躲避电幕的世外桃源。错。在大系统看来,这不叫生活。这叫死刑犯行刑前的最后晚餐。
PART 01
消失的同事:西蒙的命运
我们要重新回到那个冰冷、残酷、空气里永远弥漫着劣质消毒水味道的真理部办公大楼。我们要回到那个巨大的、像绞肉机一样的社会机器里。因为有一件事终于发生了。这件事,温斯顿早在几个月前就预言过。那是一件在职场里最恐怖、却也最平常的事:一把椅子,空了。
事情发生在真理部一个平淡无奇的早晨。伦敦的阳光永远像是一层洗不净的煤灰。温斯顿像往常一样,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进食堂。那里排着长长的队伍,大家在等待领取那种看起来像呕吐物、闻起来像工业废水的肉类炖菜。温斯顿端着托盘,习惯性地往旁边那个固定的座位看了一眼。那个平时总是坐在那里、瞪着突出的眼珠子、喋喋不休地讨论新语词典第十一版修订进度的语言学家——西蒙,没来。第一天,温斯顿以为他生病了,或者被派去出差执行秘密任务。第二天,那个座位上坐了一个陌生人。那是一个面孔模糊、只会机械吞咽食物的基层办事员。第三天,温斯顿去查看了走廊公告栏上的国际象棋委员会名单。西蒙原本是那个委员会的重要委员。温斯顿站在那张密密麻麻的名单前,指尖轻轻划过纸面。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了一下。名单上没有划掉的横杠,没有涂改的墨迹。西蒙的名字,彻底消失了。原本写着那个名字的地方,现在的排版天衣无缝,行间距精准得令人发指。就好像那里从来就没有过文字,就好像西蒙这个生命,从未在那张纸上留下过哪怕一个字符的痕迹。
这就是第一大洋国的离职流程。没有告别聚餐,没有交接文档,没有人力资源部门的最后谈话,更没有朋友圈里的煽情道别。你就这样——噗的一声,在这个世界上蒸发了。奥威尔用了一个极其冷酷的词来定义这种状态:非人。朋友们,请细品这个词背后的重量。非人不等于死人。死人至少在档案里还有个注销日期,在公墓里可能还有一块写着生卒年的石头。但非人意味着你被彻底格式化了。你的出生证明被扔进了焚化炉,你的学籍记录被从数据库里抹除,你曾经签过的每一份合同、你发过的每一个指令、你在合影里留下的每一个侧脸,都在一夜之间被专业的系统清洗人员处理得干干净净。如果你的父母在街头突然想起你,那是思想罪;如果你的朋友在喝醉后提到你的名字,那是叛国行为。因为在官方的历史里,你从未出生过。你不是死去了,你是从未存在过。
这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谋杀。这是在时间轴上、在存在层面上对一个人进行的彻底抹杀。想象一下,如果此时此刻,你所有的社交账号被瞬间注销,你的手机号变成空号,你的银行卡被冻结,甚至连你邻居记忆里关于你的画面都成了禁忌。在现代社会,如果你失去了所有的数字痕迹,你和死了有什么区别?西蒙,那个曾经活生生、充满激情的语言天才,就这样变成了一缕灰色的烟雾。

系统的逆淘汰机制
现在,我们要进行一次冷峻的职场验尸。西蒙为什么会死?是因为他反动吗?不。西蒙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忠诚。他崇拜老大哥,他甚至能为每一个被删减掉的旧语单词而感到一种扭曲的快感。是因为他懒惰吗?不。他是个典型的卷王。他没日没夜地钻研词典,他恨不得把人类的思考能力压缩到极致。是因为他乱说话吗?也不是。他说的每一句立场话都极其正确。那他为什么必须死?温斯顿早在几个月前,看着西蒙那双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眼睛时,就在脑海中写下了判决书:他太聪明了。他把事情看得太清楚了。
朋友们,这就是系统里最残忍的逆淘汰机制。在一个要求绝对服从的机器里,有两类人是安全的:第一类,是像帕森斯那样的傻子。这种人没有脑子,只有一副好体力和一颗盲从的心。老大哥说太阳是方的,他会立刻去定制方太阳的旗帜。这种人是推磨的驴,是安全的资产。第二类,是完全的职业奴才。他们知道自己在撒谎,但他们享受撒谎带来的权力。而西蒙,属于致命的第三类人——清醒的拥护者。西蒙不仅仅是在编词典,他在研究统治的逻辑。他懂这个系统的运行机理。他知道为什么要消灭自由这个词,他知道怎么通过阉割语言来阉割大脑。他甚至能从语言学的专业角度,去欣赏这种暴力的美学。
这才是他的死因。系统不需要理解者,系统只需要执行者。你太懂了,你就危险了。因为你今天能从逻辑上论证老大哥的英明,明天你就可能用同样的逻辑,推导出系统的荒谬。你的智商本身,就是对那些平庸管理层的威胁。在一个要求无意识服从的社会里,一个有意识的、清醒的头脑,哪怕他是拥护你的,也是一颗必须被剔除的砂砾。因为他不可控。他拥有解释权,而解释权是最高权力的禁脔。看看现在的某些职场。那些真正懂业务、懂底层架构、能一眼看穿项目死穴的人,往往混不长。反而是那些只会喊口号、只会做漂亮文案、只会拍马屁说领导高见的人,步步高升。西蒙那把空掉的椅子,其实是每一个自命不凡的精英的墓碑。
生存者:甲虫般的人
西蒙消失了,但谁活下来了?温斯顿坐在食堂的角落里,冷冷地观察着隔壁桌的一个职员。那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人,长着一张像甲虫一样扁平、油腻的脸。这个人正在对着对面的女同事喋喋不休。温斯顿发现,那甚至不能叫说话。因为从他嘴里喷出来的不是经过大脑思考的词汇,而是一连串预设好的自动回复。那不是大脑在说话,那是喉咙在说话。那是一种像鸭子一样嘎嘎叫的声音。这个甲虫般的人在说什么,具体内容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语调:激昂、坚定、充满了那种廉价的正能量。只要你给他输入一个关键词,比如当前形势或者老大哥的决策,他就会像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语音生成器,自动生成一段形势一片大好的废话。
温斯顿断定:这个人永远不会被蒸发。因为他没有自我。他已经彻底昆虫化了。这种人在庞大的官僚机构里如鱼得水。他们没有个人的喜怒哀乐,他们只有系统的喜怒哀乐。系统让他咬谁,他就跳起来撕咬;系统让他赞美谁,他就立刻热泪盈眶。他们不是坏,他们是空。而这种极致的空,是进入那个世界唯一的生存资格证。
PART 02
仇恨周:情绪的统购统销
西蒙的消失,在整个大洋国的喧嚣中,甚至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因为一场更大的、覆盖全城的疯狂已经降临了:仇恨周。这不是那种每天两分钟的快餐式仇恨。这是一场精心准备的、全民参与的狂欢节。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全城挂满了巨大的旗帜。广场上立起了狰狞的欧亚国士兵模型。电幕里二十四小时循环播放着高亢刺耳的仇恨之歌。甚至当几颗来历不明的炸弹掉在游乐场里,炸死了几十个无辜的儿童时,这种惨剧也被瞬间包装成了敌人的暴行,用来给愤怒的火堆添一把最烈的柴。
温斯顿忙疯了。他在真理部每天连续工作十八个小时。他的任务是大量编造假新闻,修改过去的数据,把所有的仇恨都引导向官方指定的那个方向。朋友们,请大家仔细看看这个仇恨周。它像不像我们现在的某些时刻?像不像全网针对某一个人的集体网暴?像不像某种被资本和流量精确操纵的舆论狂欢?它的本质,是情绪的统购统销。平时,你的生活是枯燥的、被压榨的、绝望的。所以,管理层必须定期制造一个高潮。他们允许你在这个星期里疯狂,允许你尖叫,允许你释放内心所有的暴力和戾气。但前提是:你的愤怒必须指向那个特定的靶子。温斯顿站在窗边,看着外面那些眼睛通红、喉咙嘶哑的人群。他感到一种深深的虚无。他知道内幕。他知道那些炸死儿童的炸弹,很可能就是老大哥自己扔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仇恨的化学反应。但这都不重要了。当全城的人都相信这是真理时,事实就死在了垃圾桶里。
PART 03
新语:思想的牢笼
西蒙虽然肉体蒸发了,但他毕生心血的结晶,那本沉甸甸的新语词典第十一版,却像一个幽灵,死死地统治着每一个人的大脑。温斯顿坐在办公室那张沾满墨水的桌子前,手里掂量着这本小册子。它的封皮是粗糙的灰色,散发着一股廉价油墨和化学药剂的刺鼻味道。它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温斯顿知道,这每一页纸、每一个条目,都是一把手术刀。还记得西蒙生前最兴奋、最狂热的那句话吗?他说:“我们正在把语言切剩到只剩骨架。我们每天都在消灭成百上千个词。”
今天我们要聊点硬核的东西。我们要聊聊语言。很多人觉得,语言只是个传声筒,是个工具,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错。彻底的错。有一位名的大哲学家说过一句至理名言: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老大哥和那些身处核心层的权力专家,深知这一点。他们知道,抓人、打人、杀人,那是最低级、最浪费资源的统治方式。因为你只能限制一个人的肉体。如果他心里恨你,他的灵魂依然是自由的,他依然会在黑暗中策划反抗。如果你想进行最彻底的、永劳永逸的奴役,唯一的办法就是——修改他的字典,阉割他的词汇,最后彻底切除他的思考能力。
新语的核心逻辑:做减法
新语的核心逻辑非常简单,简单到令人发指,也简单到令人后背发凉。那就是四个字:做减法。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里,语言是一直在膨胀的。我们发明出无数细腻、丰富、优雅的词汇来形容万物。但在第一大洋国,语言在萎缩。举个例子。在我们的旧语言里,有好,也有坏。但在新语里,坏这个词被枪毙了。西蒙曾经解释过: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好这个词,为什么还需要坏?坏只是好的反面。它本身不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词存在。所以,在新语里,你只能说不好。你想表达非常棒?别用那些精彩、绝伦、卓越、辉煌这些复杂的词了。那些词带有太多情感色彩,容易引发不必要的联想。在新语里,统一用加好。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强烈?那就用双加好。
朋友们,听听这些词。不好、加好、双加好。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现在某些只剩下绝绝子和神中神的互联网评论区?或者像某些只会用缩写字母表达情绪的低龄社交圈?这背后的阴谋是惊人的。当坏、邪恶、卑鄙、残酷、暴政这些充满了批判性、充满了愤怒力量的词汇全部从字典里被删除,只剩下一个干瘪的、毫无感情色彩的不好时——你还怎么形容你对现状的不满?你本来想写一篇檄文,愤怒地控诉:这是一个残暴的、毫无人性的、疯狂践踏尊严的体制!但在新语环境里,你张开嘴,只能吐出一句:这个政策是不好的。
听到了吗?那种撕裂黑暗的愤怒力量,消失了。那种刺破谎言的批判锋芒,变钝了。你听起来不再像一个觉醒的革命者,你听起来像个坐在食堂里哼哼唧唧抱怨饭菜不合口味的小屁孩。这就是系统的目的:通过消灭词汇,来消灭你的情绪深度。当你找不到精准的词去形容痛苦的时候,你的痛苦就在逻辑上变得模糊了,变得不存在了。更狠的招数,是概念的阉割。有些词虽然在字典里被保留了,但它的灵魂已经被完全阉割了。比如自由这个词。在新语里,你依然可以说自由。但这个词的用法被严格限制在了物理层面。你可以说:这只狗身上没有虱子,所以它是自由的。你可以说:这块地里没有杂草,所以它是自由的。但是,你绝对不能说:政治自由或者思想自由。因为在大洋国的世界里,政治自由这个概念本身已经被从根源上铲除了。
这就像你不能对一个从未见过电力的原始人解释网络波动一样。因为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电和数据的概念。对于那些在新语词典环境下长大的下一代孩子,自由这个词,仅仅意味着没有、空着。你想跟他说:我们要去争取自由!他会瞪着一双天真且空洞的大眼睛问你:我们要去争取没有?我们要去清除什么害虫吗?这就是著名的语言决定思维假说的黑暗应用:如果你字典里没有暴政这个词,你就永远无法思考什么是暴政。如果你字典里没有权利这个词,你就永远无法意识到你已经失去了权利。这是一种维度的碾压。系统把你从一个拥有三维思考能力、拥有细腻情感起伏的人,硬生生地压成了一个只有黑白两色、只有加好和不好的平面纸片人。
鸭语:语言的终极退化
新语的终极目标,是一个奥威尔创造的、极其生动的词:鸭语。顾名思义:像鸭子一样嘎嘎叫。这在第一大洋国有两层含义。如果是形容敌人的演讲,那是在骂他胡说八道,吐出来的全是废料。但如果是形容自己人的汇报,那就是至高无上的赞美——双加好鸭语。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说话这个行为,已经完全脱离了大脑。当你的词汇量被压缩到只有几百个,当你所有的观点都有标准答案,你说话就像是自动售货机吐出收银条一样快,根本不需要经过思考。老大哥是双加好的!欧亚国是双加不好的!这些话不是从大脑里想出来的,而是从喉咙里直接喷出来的。声带在振动,肌肉在收缩,但大脑皮层是死寂的。你不再是一个拥有灵魂的个体,你变成了一个生物扩音器,一个系统的复读机。
看看现在的某些职场。那些张口闭口底层逻辑、颗粒度对齐、赋能、抓手、闭环的人。当大家习惯了用这些空洞、干瘪、像罐头一样标准化的词汇来交流时,我们以为自己很专业。其实,我们正在逐渐丧失说人话的能力。我们正在变成那些在系统里呱呱叫的鸭子。当语言失去了温度,思维也就失去了生机。朋友们。别以为这只是一本发黄的旧小说。打开你的手机,看看你的聊天记录。看看那些变异的字母缩写,看看那些因为所谓的敏感而不得不变成星号、变成方框的词。看看那些为了规避某种审查,而不得不把死亡改成领盒饭,把杀人改成口人的荒诞字幕。这不仅仅是一种避讳。这是一种慢性的、集体的智力退化。当我们习惯了用表情包代替细腻的感受;当我们习惯了用吃瓜来解构所有的严肃新闻;当我们习惯了用带节奏来否定一切理性的质疑。我们就在主动走向那座新语的监狱。
温斯顿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他是个旧时代的残党。他还能记起那些丰富的、带刺的、充满血肉感的词汇。他还能想起那些形容尊严、形容美丽、形容绝望的微妙语词。他是一个守墓人。他在守护着语言最后的火种。但那些下一代呢?那些从小只听过双加好的孩子们,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他们不会觉得笼子太小,因为他们的思维已经萎缩到连笼子的栏杆都碰不到了。这一章,我们拆解了新语。它是比思想警察更隐蔽的杀手。它不杀你的头,它只杀你的词。西蒙死了。但他编的那本杀人字典,正在伦敦的每一个角落里,安静地收割着人类的灵魂。温斯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他不仅是一个思想犯,他更像是一个词语的难民。
但系统留给他感伤的时间不多了。仇恨周的高潮已经像海啸一样扑面而来。在那个狂热的广场上,温斯顿将亲眼目睹一场人类历史上最荒谬、也最完美的魔术表演。那是关于战争的真相,也是关于记忆的彻底崩塌。我们要走进那个震耳欲聋的广场。去看看,当敌人可以在演讲进行到一半时突然被调包,下面的人群是如何在零点一秒内完成大脑重组的。朋友们,趁着你还能说出复杂的话,请珍惜那些带刺的词汇。
欢迎来到仇恨周的最后现场。如果你觉得之前的两分钟仇恨只是某种职场早操,只是让大家活动一下面部肌肉,那么现在,系统为你准备了一场长达七天的、高强度的、令人窒息的感官盛宴。此时此刻的伦敦,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正在漏气的压力锅。盛夏的阳光暴晒着街道。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作呕的味道:那是劣质杜松子酒的酒精味、变质炖菜的馊味,以及成千上万个不洗澡的躯体散发出的酸臭味。但在广场上,没有人关心这些。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这里,每一个人的脸都因为兴奋而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潮红。巨大的喇叭在每一个街角轰鸣,震得人的耳膜嗡嗡作响。他们在等一个瞬间,一个足以让他们彻底释放压力的法外瞬间。这几天,大洋国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在尖叫,所有的电幕都在喷火:我们要打倒欧亚国!欧亚国是人类的毒瘤,是必须铲除的害虫!欧亚国的军队正在边境烧杀抢掠,我们要用血来偿还血!那种愤怒是真实的。它像野火一样在人群中蔓延。如果你现在在大街上抓住一个长得像欧亚国的人,这群狂热的市民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用指甲、用牙齿把他撕成碎片。
但是,朋友们,请盯着那个台上的演说家。就在这个情绪最饱满、愤怒最亢奋、大家已经准备好要为正义献身的巅峰时刻,那个足以载入人类荒诞史册的魔术,发生了。台上站着一位真理部的资深演说家。他是一个完美的喉舌:声音洪亮如雷鸣,手势夸张如戏剧,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都透着一种慷慨赴死的正义感。他正在发表一篇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历数欧亚国在边境的所谓暴行。台下的群众听得如痴如醉,每一个排比句落下的瞬间,人群中都会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怒吼。就在演讲进行到一半,演说家的语速达到每分钟两百个词,气氛已经快要炸裂的时候,一名戴着袖章的文员快步上台,递给了他一张纸条。没有停顿。没有惊讶。演说家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他接过纸条,扫了一眼,顺手揣进兜里。他继续讲了下去。
但是,就在这一秒钟,奇迹发生了。他的前半句还在痛斥欧亚国的罪恶,后半句的主语,突然变成了东亚国。发生了什么?难道不需要逻辑过渡吗?难道不需要给台下的人解释一下国际形势发生了什么惊天变动吗?不需要。就在这一秒钟,战争的对象变了。大洋国现在的死敌是东亚国。至于欧亚国?那是我们的盟友啊!那是我们从开战第一天起就并肩作战的兄弟国家啊!最恐怖的,其实并不是演说家的临场改口。毕竟,他只是一个拿工资的演员,他的大脑早已被系统接管。最恐怖的,是台下那几万名听众的集体反应。
按理说,一个正常的生物,听到这种自相矛盾的话,第一反应应该是:哎?是不是搞错了?或者:你刚才不是还在骂欧亚国吗?不。在第一大洋国,这种逻辑上的廉耻感是不存在的。在那一刻,广场上的人群发生了一阵骚动。但这种骚动不是在质疑演说家,而是在愤怒地寻找阶级敌人。他们突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天哪!我们手里的横幅印错了!广场上挂的这些海报,怎么印着欧亚国的名字?这一定是东亚国的特务搞的破坏!疯了。彻底疯了。全场几万人开始疯狂地撕扯那些刚刚还被他们视为神圣的横幅,踩踏那些前一秒还被他们举在头顶的海报。他们义愤填膺,好像这些海报本身就是一种对他们的羞辱。几分钟前,他们还在为了反对欧亚国而热血沸腾。几分钟后,他们坚信自己从始至终、从出生那天起,就是在反对东亚国。那个切换的过程,比你手机刷新网页还要快。
这就是双重思想的最高境界:控制过去。对于这群人来说,记忆不是连续的河流,记忆是一块可以随时擦写的黑板。既然现在的领袖说敌人是东亚国,那么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就从来没有和欧亚国开过火。至于前几天那些关于欧亚国的报道?那是幻觉。那是假象。那是敌人的恶意渗透。朋友们,让我们停下来,深吸一口气,想一想。这真的只是小说里的情节吗?看看我们现在的舆论场。昨天的战略伙伴,今天可能就是邪恶势力。昨天的行业先驱,今天可能就是吸血资本。当某种风向决定要调头的时候,底下的评论区是不是也在一秒钟内完成了集体大掉头?前一秒还在喊某某加油,后一秒风评一变,马上开始喊某某去死。没有人觉得自己被打脸了,没有人觉得自己之前的狂热是个笑话。大家都会一脸正经地说:哦,原来他是这样的人啊,我早就看出来了。
这就是群体性失忆。在那个巨大的、被情绪操纵的广场上,敌人是谁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正在战斗这个姿态。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合法投射暴力的靶子,至于靶子上面贴的是哪张脸,那是上面的人决定的事。奥威尔看透了这种玩法的本质:战争不是为了胜利,战争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结构。为了让民众保持那种紧绷的、易怒的、容易被操纵的状态,敌人就必须永远存在。如果这个敌人被榨干了价值,那就换一个。换敌人,就像给手电筒换电池一样简单。广场上的演讲圆满结束了。群众们心满意足地去游行了,去打砸那些所谓东亚国特务留下的痕迹了。但是对于温斯顿来说,他的地狱周才刚刚拉开序幕。因为他是真理部的基层员工。既然领袖说敌人变了,那么所有的历史都必须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完成物理性的坍塌和重组。
你想想这个工作量有多大?在过去五年里,所有的报纸、所有的期刊、所有的电影纪录片、所有的宣传画。凡是提到正在与欧亚国打仗的地方,全部都要作废。每一行字,都要被改成正在与东亚国打仗。温斯顿回到了办公室。此时的真理部大楼,灯火通明。整个政府机构都进入了一种病态的、甚至带点宗教仪式感的疯狂加班状态。剪报、重印、销毁、替换。那个巨大的、通往地下焚化炉的记忆洞,日夜不停地咆哮着。它像一个永远吃不饱的怪兽,吞噬着无数吨沉重的历史文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成千上万名穿着蓝色制服的员工,坐在明亮的灯光下,手里拿着剪刀和胶水,正在用一种极其严谨的态度,去伪造每一个标点符号。他们知道真相吗?当然知道。他们刚刚才从那个广场上回来。但他们必须假装不知道。他们必须用一种神圣的、虔诚的工匠精神,去生产谎言。
经过了六天六夜、不眠不休的疯狂劳作。任务完成了。所有的旧报纸都被回收销毁了。新印出的、日期却标注在五年前的报纸,已经被悄悄塞进了档案馆的柜子里。现在的图书馆里,如果你翻开任何一张过去几年的报纸,上面赫然写着的都是我们在和东亚国打仗。欧亚国?那是我们的老朋友,一直都是。温斯顿看着这一叠叠还带着油墨香味的新旧报纸,感到一阵深入骨髓的绝望。这比任何肉体上的折磨都让他感到虚无。因为这意味着:真理,彻底死了。客观事实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领袖说二加二等于五,只要他修改了所有的教科书,催眠了所有的民众,焚毁了所有的反对证据,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二加二就真的等于五。
这就是现代文明最深层的恐惧:如果一棵树在深山里倒下,没有电幕转播,没有数据库记载,那么这棵树就真的从未倒下过。甚至,这棵树从未存在过。看看我们现在的互联网。该内容由于违规无法查看是什么?词条已锁定是什么?评论区精选又是什么?那就是现代数字版的记忆洞。当一个人的存在痕迹被抹去,当一段公共讨论被格式化,仅仅需要几年的时间,新一代的年轻人就真的会以为,那些事从未发生过。历史不再是刻在石头上的碑文,历史变成了屏幕上随时可以被后台管理员修改的一串串代码。
这一章,我们见证了权力的终极傲慢。几万人在一秒钟内完成了大脑的重组。几千个温斯顿在六天内完成了历史的重生。这就是系统的力量。它不仅要霸占你的现在,它还要强奸你的过去。温斯顿累瘫了。他提着公文包,走出真理部那座像白色金字塔一样的大楼。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飘浮在真空中的幽灵,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字是真的,没有一个日期是准的。但是,就在他极度绝望、快要被虚无吞噬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地方。一个在这个充满了修改液、谎言和粉碎机的城市里,唯一还保留着肉身真实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电幕的窥视。那个地方住着一群被精英们视为牲口、视为草芥的底层人——无产者。温斯顿突然意识到:在这个巨大的疯人院里,也许只有那些在大街上洗着臭烘烘的尿布、为了两分钱的彩票奖金吵得不可交、在大口喝着劣质啤酒的底层劳动者,才是真正活着的。
让我们从那个疯狂的、充满血腥味的广场撤退。刚刚我们在外面见证了一场集体精神病的爆发,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小小的、破旧的、但在此时此刻还算安全的私人空间——慈善店二楼的那个房间。温斯顿站在窗前,那是他最喜欢的姿势。窗户半开着,没有电幕的嗡嗡声,只有夏日傍晚微凉的风。窗外的院子里,站着一个无产者妇女。如果按照大洋国官方的审美,这个女人简直丑得无可救药。她五十多岁,身材因为长年的重体力劳动和劣质的碳水化合物而变得异常臃肿,两条胳膊由于长期浸泡在肥皂水里而呈现出一种粗糙的、鲜艳的肉红色。她穿着一件已经洗得发白的围裙,正在那儿晾衣服。
她嘴里衔着几个木夹子,手里熟练地抖动着湿漉漉的床单。最让温斯顿震撼的是,她在唱歌。那是一首由真理部下属的音像处用机器自动合成的低俗流行曲。歌词平庸、旋律单调,原本是用来麻痹底层劳工的精神饲料。但在此时此刻,在这个女人的嗓子里,这首歌竟然唱出了一种像大地一样厚重、像野草一样顽强的生命力。温斯顿看得痴了。就在几分钟前,他还身处那个要把所有人的大脑都整合成一块芯片的体制内。而现在,他看着这个在夕阳下晾尿布的女人,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审美冲击。她很美。这种美,不是画报上那种经过修饰的虚假。这是一种像石头、像泥土、像生生不息的繁衍本身一样的真实。她在这儿洗了一辈子衣服,生了十几个孩子,她也许一辈子都没想过什么高深的哲学,她甚至认不全新语词典里的词汇。但她就在这儿,她在歌唱。系统可以修改历史,可以枪毙精英,但系统无法阻止这个女人在劳作之后发出的那声叹息,和那串悠长的调子。这就是温斯顿最后的发现:真实,只存在于泥土里。
在这一章里,温斯顿对着坐在床上的朱莉娅,说出了一句足以让所有中产精英感到脊背发凉的话:无产者才是人。我们不是人。朋友们,请大家仔细品味这句话背后的辛辣讽刺。温斯顿是谁?他是外围党员。他穿着蓝色的制服,在气派的写字楼里工作。他受过高等教育,他有编制,他甚至有资格吃那种虽然难吃但定量的配给粮。按现在的标准看,他就是典型的精英,是白领,是社会的中坚。而无产者是谁?他们是那些在贫民窟里为了两分钱的菜价打架、在酒吧里喝得酩酊大醉、满口脏话、不识大体、被统治阶级视为牲口的底层。但在温斯顿看来,这些被称为牲口的人,才真正保留了做人的尊严。因为他们保留了私情。
你看温斯顿周围的那些同事:看到朋友被抓,要面无表情;看到父母消失,要表示坚决拥护;甚至连做梦都要小心,不能说出真心话。为了在系统里活下去,温斯顿们主动或被动地切除了自己的情感。他们变成了逻辑严密的机器,变成了只会复读口号的录音机。而无产者呢?他们虽然愚昧,虽然粗俗。但当他们看到亲人被打,他们会真的愤怒;当他们看到爱人受伤,他们会真的流泪。他们保留了那些被系统视为低级、落后、甚至有毒的本能反应。温斯顿终于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这个宏大叙事、宏大理想、宏大仇恨吞噬一切的世界里,如果你还想保持人性,你就必须先让自己变得低级一点。因为那些所谓的高级智力,早就成了系统进行自我审查的帮凶。
温斯顿站在窗边,看着那个红胳膊女人的背影,在脑海里写下了一个数学命题。在大洋国,党员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剩下的百分之八十五都是无产者。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如果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在某一个早晨,同时跺一下脚,那个看似坚不可摧的白色金字塔就会在一瞬间土崩瓦解。那个晾衣服的女人,只要她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她甚至可以徒手把那个瘦弱的、只会躲在电幕后面窥视的思想警察撕成碎片。他们拥有核弹级别的原始力量。只要他们愿意。但悲剧也恰恰在这里。这是奥威尔抛给全人类最绝望的一个悖论:在他们觉醒之前,他们永远不会反抗;而在他们反抗之前,他们永远不会觉醒。这是一个死循环。是一个给巨兽安装的、永远无法解开的电子锁。
系统是给这些无产者提供了什么?廉价到几乎没有酒精的劣质啤酒、充斥着暴力和色情的下流刊物、以及那个由政府控制、充满了虚假希望和数学陷阱的彩票。这就够了。这就是现代人常说的奶头乐策略。只要底层的感官被这些低级的、碎片化的快乐填满,只要让他们每天为了那一块钱的彩票奖金而争得脸红脖子粗,他们就永远不会去思考那个真正的问题:为什么我辛苦了一辈子,却连一个不发霉的房间都买不起?看看现在的世界。算法推荐给你的那些让你不断下滑的短视频,那些让你在瞬间获得虚假优越感的口水仗。它们是不是正在把你变成一个快乐的无产者?你有力量吗?你有。但你没有脑子。温斯顿有脑子吗?他有。但他没有任何力量。这就是权力的最高稳固形态:把智力和力量彻底隔离,让它们老死不相往来。
夕阳终于彻底沉入了伦敦那层厚厚的雾霾之下。房间里暗了下来。温斯顿和朱莉娅并没有开灯。在这个世界上,黑暗有时候比光明更安全。他们在那个充满了古董气息的房间里,进行了一场关于死亡的最后谈话。温斯顿看着朱莉娅。在朦胧的月光下,这个女孩显得那么真实、那么鲜活。他突然开口,声音平静得像是一块沉入水底的石头:我们是死者。朱莉娅是一个极其务实的女孩。她不喜欢这种深奥且丧气的哲学思考。她拉着温斯顿的手说:别瞎说。你看,我的皮肤是热的,我还能感觉到饿。我们还活着,而且我们要活很久。但温斯顿摇了摇头。在他看来,从他在那本日记本上写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被系统在名单上勾掉了。他说:我们现在的这点私人生活,这点在破屋子里的温存,并不是什么新的开始。它只不过是尸体腐烂之前,残存的那么一点点余温。这是一种极致的绝望,但也是一种极致的勇气。这叫向死而生。温斯顿不再幻想着能逃过思想警察的眼睛。他不再幻想着能等到所谓的自由。他只是想在死亡正式降临之前,作为一个入,多待一会儿。能多喝一口黑市上买来的真正带有咖啡香味的咖啡,能多看一眼窗外那个唱歌的胖女人,能多感受一下朱莉娅手心的温度。这就是他对那个冰冷世界的、最后的、无声的嘲讽。
本集最令人窒息、也最令人心碎的时刻,就在这一秒钟降临了。朱莉娅为了安慰温斯顿,也为了表达她对这种命运的认同,她轻轻地跟了一句:是的,我们是死者。就在这两个人紧紧相拥,准备迎接又一个黑暗的夜晚时。一个声音,毫无征兆地在房间里响起了。那个声音不是从温斯顿嘴里发出来的,也不是从朱莉娅嘴里发出来的。那个声音低沉、冷酷、带着一种令人绝望的金属质感。它像录音机一样,冰冷地重复了他们刚才的话:你们是死者。温斯顿全身上下的血液瞬间凝固了。他僵硬地转过头。房间里没有电幕。这是他租这个房间唯一的理由。在那面贴着发黄墙纸的墙上,只有一幅旧画——圣克莱门特教堂的版画。那是温斯顿一直用来凭吊旧时代美好的象征。那个声音继续下达指令,像是一个无形的死神在宣判:还在那里动!背着手!站在房间中间!朱莉娅惊叫了一声。画框。那幅画。它被某种力量从里面推开了。它摔在地上,碎成了一堆烂木头。在那个空洞背后,露出来的不是砖头。是一块电幕。一块一直躲在画纸后面,像猫戏弄老鼠一样,默默注视了他们整整一个月的、发着幽幽冷光的电幕。
门被粗暴地撞开了。一群穿着黑色制服、拿着警棍的士兵冲了进来。温斯顿在那一刻,感到了一种近乎解脱的虚无。他知道,魔术演完了。但他依然想看看,那个带他走进这间屋子的、那个总是笑眯眯地讲古董故事的、那个让他放下了最后一点警惕的查林顿老头,现在在哪儿?门外走进来一个人。那是查林顿。但温斯顿揉了揉眼睛,几乎认不出他了。那个老态龙钟、走路颤颤巍巍、带着老花镜的老头不见了。站在温斯顿面前的,是一个腰杆笔直、步伐矫健、眼神像鹰一样锐利的男人。他摘下了那副伪装用的旧眼镜。他甚至看起来年轻了二十岁。他从未怀念过什么旧时代。他从未同情过什么异见分子。他是思想警察。他是一名资深的特工。他已经在温斯顿身边,潜伏、观察、诱导了整整几年。这一刻,温斯顿感到了最深层的冰冷。没有所谓的死角。没有所谓的漏洞。那个租给他的房间,那本卖给他的日记本,那个对他表现出友好姿态的奥布莱恩……这一切,全都是系统为你量身定做的思维囚笼。系统故意留给你一个破洞,就是为了让你把所有的真心话都吐在那儿,然后再一次性收割。你以为你在秘密地反抗?不。你只是在大屏幕面前,按照剧本完成了一场完美的表演。
一个士兵走上前,粗暴地抓起了温斯顿最心爱的那块玻璃镇纸。那是他在查林顿店里买的,里面有一块粉红色的、晶莹剔透的珊瑚。那曾是温斯顿心中唯一的、未被污染的净土。士兵把它高高举起,重重地摔在了地毯上。砰的一声。玻璃碎了。那块粉红色的珊瑚,在灰尘中变得暗淡无光,像一块普通的石头。温斯顿被分开了,朱莉娅被带走了。重重的一记老拳打在温斯顿的肚子上,让他疼得像一条缺水的鱼。他倒在地上,视线模糊。他最后一眼,看到了那个已经面目全非的查林顿。温斯顿被捕了。他以为他找到了通往灵魂的自由,其实他只是从一个牢房,走进了另一个更隐秘的审讯室。朋友们,故事到这里,并不是终点。相反,真正的治愈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温斯顿将被带到那个传说中的仁爱部。在那里,等待他的不是枪子,而是老大哥最深情的关怀。那里没有黑暗,那里灯火通明。那里要让你知道,为什么二加二不仅可以等于五,还可以等于任何老大哥想要的数字。这里是人生实话。我是温斯顿。我的葬礼已经开始了。请记住你的珊瑚。即便它最终会碎裂,至少它曾经闪过光。我们下集见。
THE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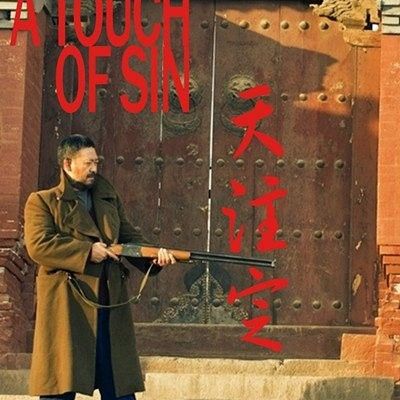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