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编过《北方文学》,未料到退休后重操旧业,又干起老本行来,被黑龙江省招生办《学子》杂志聘为副总编。
那年,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召开主席团会议,我的座位在迟子建右侧,约她为《学子》写篇卷首语。她大略翻了翻我带去的刊物,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可以给你们写一篇关于朗诵与逆向思维的文字,对高中生如何写作文会有些帮助。身为省作协主席和著名作家,能欣然为一本面向中学生的杂志写稿,毋庸置疑,作家的责任感使然。
几天之后,读到了她转给我的这篇文章,写得实在是好,不能不为她的美文击节赞赏。我迫不及待地拿给编辑们传看,大家一致认为,卷首语只能发一千字左右,太可惜了,开设个作文指导专栏,全文刊发多好!
作为这家杂志的副总编,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先于《学子》的读者,一字一句地看了这篇文章。从文章中可以看出,迟子建喜欢朗诵,对朗诵情有独钟。她在文中这样写道,“好的文章给人一种欣赏音乐的感觉。能够读出声来,读出气象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说得好,我向来以为,音符是可以朗诵的文字,不是吗?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的一首《江河水》,令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伏案大哭,文章、诗词莫不如此。我每每听到大型历史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朗诵的“怎能忘记,毛主席率领我们走过的万水千山”时,禁不住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就是在日常生活的酒桌上,我们常常即兴朗诵郭小川的《祝酒歌》,三伏天下雨哟,雷对雷,朱仙镇交战哟,锤对锤,今晚哟,咱们来个杯对杯……大家频频举杯,把聚会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可见,朗诵的魔力所在。
此刻,我想起被国家环境部聘为环境大使的著名诗人徐刚。上大学时,我俩住在一个宿舍,晚上熄灯入寝后,此人常常从床上爬起,打开电灯朗诵,旁若无人。一次夜半时分,他居然站在地中间,大声朗诵他的诗歌新作,同寝的人却无人非议,虽戏谑他疯了,倒成了他的听众。尽管后来他不大写诗,全身心投入环境文学写作,著述等身,依然坚持朗诵的习惯。在北京团结湖的家中,给我朗诵过他在黄山写就的那首《悬崖上的红杜鹃》:“你,悬崖上的红杜鹃,向着我莞尔一笑,我却心惊胆战!我唯恐你掉下,在峡谷里粉身碎骨——美,从来都是面临着灾难……”顿觉黄山的天空,天更蓝,云更白,阳光更明亮,花朵更芬芳。
二十世纪80年代初,《新观察》刊出他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伐木者,醒来》,亦曾给我朗诵过部分章节,尽管他操着浓重的上海口音,四声混同,“黄”“王”不分,但那磅礴的气势,鲜明的节奏,优美的文字,一下子让我回到大森林中,给了我创作的灵感和一试身手的激情。
在家里,我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一本伴我几十年的朗诵诗选。每当写作不顺利心烦意乱之时,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就会拿起这本书,选一首诗歌朗诵起来,先是尽情去体味美的旋律和美的语言,随之激发起我的创作冲动,一次次屡试不爽。
朗诵是一种奇妙的文学表达。热爱文学、追随文学、走在文学之路的朋友们,让我们面对青山绿水、冰天雪地,放声朗诵名家的作品,或许获得灵感,或许打开思路,或许点燃不可抑制的创作激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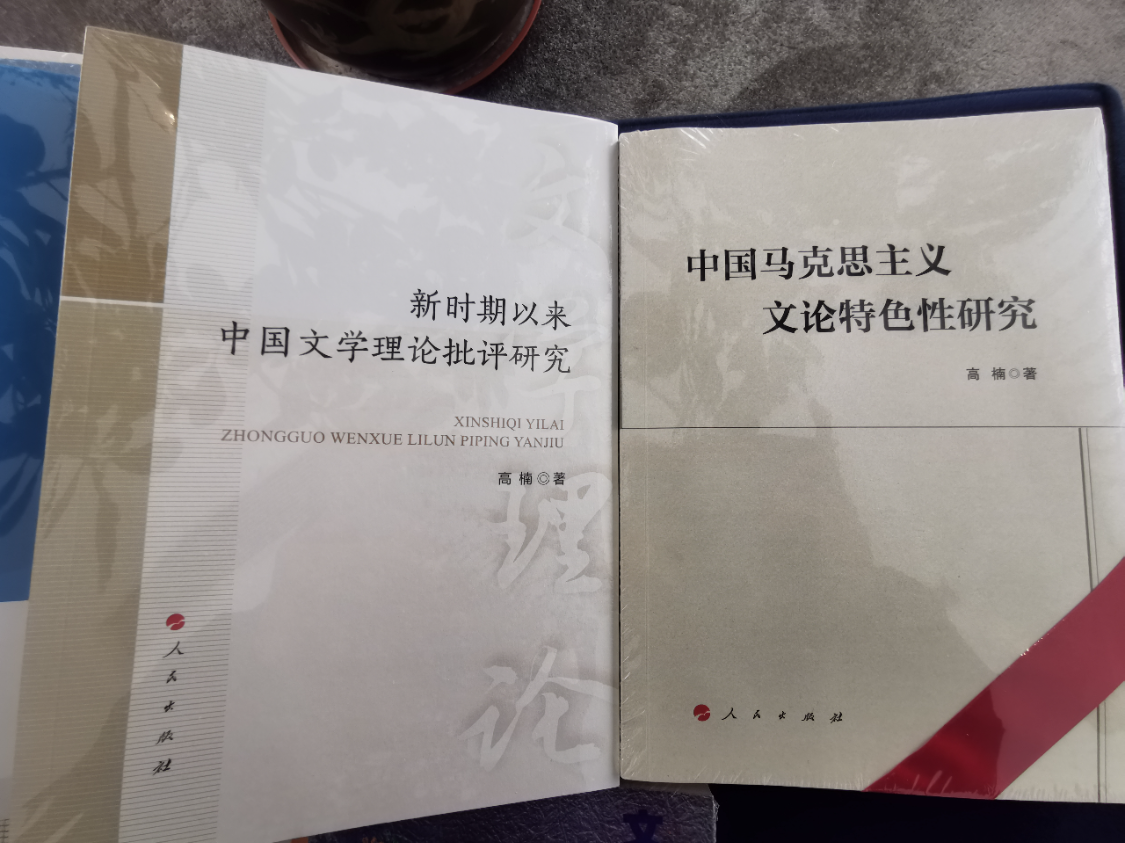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