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历史B面的“沉默巨匠”
2026年,岁次丙午,中国迎来了又一个充满活力的“马年”。
在东方的文化语境里,马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图腾;在西方的史诗中,它是骑士精神的载体。几千年来,人类习惯了马蹄声回荡在古战场的硝烟里,或是繁忙驿站的尘土中。我们赞美它是交通工具,是战争机器,是忠诚的朋友。
然而,如果我们翻开人类文明的另一本账簿——那本关于生死、病痛与疗愈的医学史——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马的名字同样赫然在列。甚至可以说,现代医学这座宏伟的大厦,有相当一部分基石是建立在马的脊背之上的。
从终结儿童传染病的梦魇,到揭示血液循环的物理奥秘;从开启激素替代疗法的先河,到如今对抗致死蛇毒的最后一道防线。马,不仅仅是人类历史上的“运载者”,更是医学史上最伟大的“生物合伙人”。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拨开历史的迷雾,讲述这段跨越三个世纪、鲜为人知却波澜壮阔的“马与医学”的纠葛。

2016年9月15日:医疗主任Barbara Dallap Schaer医生(右)和放射科医生Kathryn Wulster博士抱着一匹马,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肯尼特广场新博尔顿大型动物中心医院进行计算机断层扫描。
一、那一管红色的喷泉——生理学的物理觉醒
人类对自身身体的探索,往往是从动物身上开始的。而对心血管系统最关键的一次物理性认知,源于一匹倒霉却名垂青史的母马。
时光回溯到1733年,那是“放血疗法”还在欧洲盛行的蒙昧时代。当时的医生虽然知道心脏在跳动,血液在流动,但他们将心脏视为产生热量的“炉子”,而非泵送液体的“水泵”。
英国牧师兼科学家斯蒂芬·哈尔斯(Stephen Hales)决定挑战这个认知。在一个寒冷的下午,他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他在一匹母马的颈动脉中插入了一根铜管,并连接着一根长达2.7米(9英尺)的垂直玻璃管。
为了科学,这匹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止血夹松开的那一刻,鲜血瞬间冲入玻璃管,并在8英尺3英寸的高度上下剧烈波动。哈尔斯惊奇地记录道:血液的高度并非静止,而是随着马匹每一次沉重的心跳而节奏性地起伏。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直观地看到了“血压”。
这匹马的牺牲,彻底推翻了当时体液论的模糊认知,将流体力学引入了生理学。它向人类证明:血管是一个高压封闭系统,心脏是一个强有力的液压泵。这一实验奠定了现代血液动力学(Hemodynamics)的基础。如果没有那次实验,我们对高血压的病理机制、心脏瓣膜功能的理解可能会推迟数十年。今天,当我们用袖带轻松测量血压时,不应忘记那根矗立在18世纪风中的玻璃管,和那匹为此献身的马。

斯蒂芬·哈尔斯(Stephen Hales),1677.9.17-1761.1,4, 英国牧师,在植物学 、 气动化学 和 生理学等多个科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第一个测量 血压 的人。

哈尔斯实验 : 1733年,斯蒂芬·哈尔斯首次将一根管子插入活马的动脉,实现了动脉血压的直接测量 ,建立了实验生理学的基础方法。
二、免疫学的黄金时代与“血清长城”
如果说18世纪马的贡献是机械性的,那么到了19世纪末,马则化身为人类对抗死神的生物盾牌。
19世纪90年代,白喉(Diphtheria)被称为“扼杀儿童的天使”。这种细菌感染会在喉咙形成厚厚的假膜,让无数儿童在窒息中痛苦死去。在抗生素尚未问世的年代,医生们面对这种瘟疫几乎束手无策。
德国医学家埃米尔·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提出了革命性的“抗毒素”理论。他发现,动物在接触微量毒素后,血液中会产生一种能中和毒素的物质(即抗体)。但他面临一个巨大的工程学难题:实验室常用的豚鼠和兔子体型太小,产生的血清量如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满足大规模瘟疫爆发时的需求。
目光最终锁定了马。马体型巨大,拥有惊人的血量(一匹成年马约有40-50升血液),且性格温顺,耐受力强。
科学家开始将经过减毒处理的白喉毒素注射入马体内。马强健的免疫系统随即启动,生产出海量的抗体。随后,医生抽取马血,分离出血清,注射给濒死的儿童。奇迹发生了——原本被判死刑的孩子在几小时内退烧、假膜脱落。
这就是著名的“血清疗法”。1894年起,成千上万匹马被饲养在专门的“血清农场”中,它们成为了活体的制药工厂。紧接着,破伤风抗毒素、各类抗蛇毒血清相继问世。
这一贡献在1925年的“诺姆血清接力”(Great Race of Mercy)中达到了文化顶峰——为了将白喉血清送到阿拉斯加的疫区,雪橇犬队在暴风雪中狂奔,而那救命的血清,正是源自马的血液。可以说,在青霉素发明之前,马血清是人类手中唯一能与死神正面硬刚的武器。

埃米尔·冯·贝林( Emil von Behring)( 1854.3.15-1917.3.31),德国 生理学家 。1901年,他因“血清 疗法”,特别是对 白喉 的应用,开辟了医学领域的新路,赋予医生对抗疾病和死亡的胜利武器,获首届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 他被称为“儿童的救世主”。

将减毒白喉毒素注射入马体内,免疫系统生产海量抗体。抽取马血,分离出血清,注射给濒死的儿童。

一名男孩在护士和医生的抱持下接受了抗毒素注射。镜子里父亲擦额头,妹妹从母亲裙子后面偷看。
三、琥珀色的液体——Premarin与内分泌学的革命
时间推进到20世纪40年代,医学的关注点开始从“由于传染病导致的死亡”转向“提升生存质量”。在这一时期,马再次登场,这一次它改变的是全球女性的命运。
这就是药物史上著名的Premarin(倍美力)的故事。
早在20世纪30年代,科学家们就在寻找治疗女性更年期综合征的方法。当时的女性深受潮热、盗汗、情绪失控以及严重的骨质疏松折磨,生活质量急剧下降。虽然科学家知道雌激素可以缓解这些症状,但提取高纯度的天然雌激素极为困难且昂贵。
加拿大的生化大师詹姆斯·科利普(James Collip,他也是胰岛素的共同发现者)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怀孕母马的尿液(Pregnant Mares' Urine)中含有极高浓度的水溶性结合雌激素。
这一发现促成了1941年惠氏公司(Wyeth)推出了划时代的药物--Premarin。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其来源的缩写:PREgnantMAres' uRINe。
Premarin的问世是内分泌学的一场革命。它成为了世界上第一种口服的、可大规模生产的雌激素替代疗法(HRT)药物。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它是美国处方量最大的药物之一,帮助数以亿计的女性缓解了更年期痛苦,并预防了骨折。
然而,这也是马与医学关系中最具争议的一章。为了获取这种“琥珀色的液体”,成千上万匹母马被饲养在被称为“PMU农场”的地方。为了收集尿液,它们需要长时间佩戴收集装置,且饮水受到一定限制(为了浓缩尿液)。
Premarin的历史不仅是药学的胜利,也是动物伦理学的转折点。它引发了公众对实验动物福利的巨大关注,推动了后来合成激素技术的发展以及制药行业动物福利标准的制定。今天,虽然合成雌激素已普及,但Premarin作为天然结合雌激素仍在使用,而其背后的母马们,实实在在地支撑了人类妇科内分泌学半个世纪的发展。

詹姆斯·科利普(James Bertram Collip)1892.11.20-1965.6.19. 加拿大生物化学先驱,继胰岛素发现后,在1930年代,发现怀孕母马的尿液中含有极高浓度的水溶性结合雌激素,开发出 Premarin药物,成为了一种标准的更年期治疗。

Premarin由加拿大公司Wyeth-Ayerst于1941年推出,并于1942年首次获得FDA批准。该公司于1943年与美国家居产品公司合并,后者更名为WYETH。2009年,WEETH被辉瑞收购,辉瑞现今生产PMU药物。Premarin是通过收集怀孕母马的尿液制成的。母马被关在小型站立马厩中,以限制它们的活动,避免撞乱用于收集每一滴尿液的尿袋。母马在怀孕期间以这种方式饲养,通常约六个月。母马足月准备分娩。母马能够哺乳小马直到断奶年龄,大约3-4个月,之后与母马会强制分开,母马会重新繁殖,重复整个过程。这种繁殖循环导致大量不受欢迎的小马,大多数被卖给屠宰业。

Frigga是一匹PMU母马,她大部分时间都被孕育,以便收集尿液以制造药物Premarin。多年服役后,她被送往拍卖会,面临被运往屠宰场的风险。Gentle Giants挺身而出,救了她。

四、从“脏血”到“黄金”——现代抗蛇毒技术的进化
让我们把视线转回现代。虽然许多历史药物已被合成药取代,但在一个领域,马依然是不可替代的霸主——抗蛇毒血清。
早期的马血清虽然救命,但它是一种“粗糙”的药物。马的蛋白对人体而言是异种蛋白,直接注射往往会引发剧烈的免疫反应,即“血清病”(Serum Sickness),严重时可导致过敏性休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现代生化技术对马血清进行了“分子级的手术”。这是一个关于提纯与精度的故事。
科学家利用酶(如胃蛋白酶)作为“化学剪刀”,精准地切断抗体分子。
1.剪切:抗体呈“Y”字形。上方两臂负责抓捕毒素,下方的“茎”(Fc段)则是引发人体过敏的罪魁祸首。酶将“茎”剪掉,丢弃。
2.保留:只保留具有解毒功能的“臂”(即F(ab')2片段)。
3.纯化:通过层析技术,将杂质过滤殆尽。
经过这种处理的现代马血清,既保留了中和蛇毒的强大能力,又极大地欺骗了人体的免疫系统,使其误以为这是“自己人”。
直至2026年的今天,全球90%以上的抗蛇毒血清依然依赖马匹生产。无论是在亚马逊雨林还是澳洲荒原,当探险者被剧毒蛇咬伤,最终流进他血管里救命的液体,依然源自一匹在地球某处吃草的马。


五、同病相怜的“运动员”——骨科与“同一健康”
进入21世纪,马在医学研究中的角色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转变。它不再仅仅是提供原料的“工厂”,而是成为了研究人类疾病的最佳“替身”和“病友”。
这就涉及到了“比较医学”(Comparative Medicine)和“同一健康”(One Health)的理念。
科学家惊讶地发现,作为奔跑动物,马的骨骼、软骨和肌腱结构与人类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赛马在职业生涯中遭受的肌腱损伤(如屈肌腱炎)、骨关节炎,与人类职业运动员(如足球运动员、长跑者)的伤病几乎如出一辙。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以前常用的小鼠模型,其软骨修复机制与人类完全不同(小鼠愈合能力太强),导致很多在小鼠身上成功的药物,在人类身上完全无效。
而马,成为了测试软骨修复、干细胞治疗和富血小板血浆(PRP)疗法的黄金标准。
当我们在谈论利用自体干细胞修复受损的半月板时;
当我们在研究如何让断裂的跟腱重新长好时;
这些尖端技术往往是先在马身上试验成功,甚至是为了治愈名贵的赛马而发明的,随后才反哺给人类医学。
马用它的痛苦和康复,为人类的运动医学蹚出了一条路。这是一种奇妙的“同病相怜”——我们治愈马的同时,也终于学会了如何治愈自己。

The Orthopaedic Research Center: Helping Horses and Humans
结语:在这双眼睛的注视下
在回顾这段300年的历史时,我们必须正视其中沉重的伦理考量。
从被强行插管测量血压的哈尔斯之马,到被抽取尿液的Premarin母马,再到曾经因为过度献血而倒下的血清马。医学发展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动物的牺牲。这是人类求生本能下的选择,也是文明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代价。
但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文明的进步,我们对待这位“无言合伙人”的方式正在改变。现代抗体生产遵循着严格的动物福利标准;“血浆置换术”让献血马不再贫血;退休的实验马被送往专门的养老牧场。更重要的是,基因重组技术的进步,正让我们无限接近于在实验室里完全替代动物制品的那一天。
2026年的马年,当我们再次凝视一匹马的眼睛——那双深邃、温柔、仿佛能看透时光的眼睛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草原上的自由与狂野。
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沉默的英雄。
它们曾让我们看见血管的律动,曾用血液筑起阻挡瘟疫的高墙,曾用身体里的精华抚平女性的痛楚,如今依然在为我们抵御剧毒。医学的历史,某种意义上是一部人类利用万物以求自保的历史。而马,无疑是这部历史中最慷慨、最隐忍的捐赠者。
在这个属于马的年份里,除了赞美它的矫健,或许我们更应该怀着一份深深的敬意,向这位医学史上的“白大褂”轻声说一句:
“谢谢你,老伙计。”

【参考文献】
1. https://americanhistory.si.edu/explore/stories/how-horses-helped-cure-diphtheria
2.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4361046/
3. https://www.cdnmedhall.ca/laureates/jamescollip
4. https://www.mdpi.com/2306-7381/7/1/28
图片来自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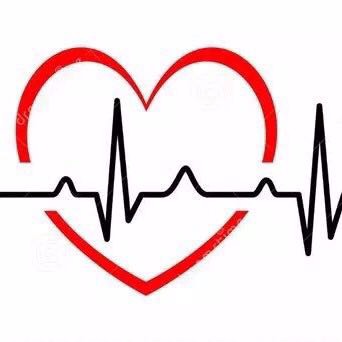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