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丨王成伦
之一:岁岁年关,母爱如灯(序言)
之二:过年,母亲备好了丰富的干菜
在豫东平原王家堂的岁月里,年味,并非只在腊月才弥漫在空气中,才澎湃在人心里。其实,它早早地,就藏进了母亲一年四季的辛劳里,藏在那从棉花到布匹,再到新衣新鞋的漫长过程中。陪着母亲准备这些,便是陪着光阴,一点点纺出过年的暖、织出过年的暖、染出过年的暖、裁出过年的暖、缝出过年的暖、纳出过年的暖、穿出过年的暖。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王家堂,虽然过年比较革命化,但每个家庭的母亲一般也都是忙到元宵节以后,才开始去挣工分;龙抬头以后,母亲们便一边参与生产队的农活,一边就开始筹划下一个过年的准备工作。最早展开的就是要在下一个除夕过年,让一家人都要穿上一身崭新的衣裳、有一双合脚的新鞋,那是全家人藏在岁月清贫里最庄重的体面。为此,母亲开始忙乎起来。

在初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陪着母亲用架子车拉鼓囊囊的几袋棉花去大队厂房轧花。轮到我家了,我看到轧花机是硬朗的,机器一开,铁齿轮咬合着,便匀速稳转起来,吱呀作响,那声响混着棉花籽脱落的轻响,在微风里荡开,雪白的棉絮从机口涌出来,棉籽簌簌落在条子筐里,母亲在一旁接棉絮,拢在用床单缝合的袋子里,絮絮的白,沾了衣角,沾了发梢,母亲眉眼间都是笑,说“这花瓤子好,过年给你做件新棉袄”,母亲的许诺,都揉进了这蓬松的棉絮里。
接着,我和母亲拉着刚轧好的棉絮到了弹棉间,当母亲把散碎的棉絮送进进料口,弹棉机便醒了。我看到电机轻吟,辊轴缓缓转动,风箱轻送,气流托着舒展的棉纤维,向着出棉口缓缓流动。经过风选的棉絮,滤去了尘屑与杂质,只留纯净的棉丝,在出棉帘的牵引下,一层层、一缕缕叠落下来。原来的棉料棉絮,此刻化作了蓬松的棉毡,软如云团,轻似落雪,触之如云朵,母亲拂过掌心拥住软软的棉,好似暖阳拥住她,母亲会心地笑了,我看得出,经过母亲的手,这些棉重获了蓬松与温暖,而后将被纺成线、织成布、做成衣,制成棉被、棉褥,裹住家人的寒冬,托着家人过年的好梦。
接下来,在农闲的间隙,母亲便开始侍弄它们。我家墙角那架柳木纺车,是时光的伙伴,木色被摩挲成深沉的暗红,锭子旁挂着小油瓶,摇把光滑如玉。白日里它沉默,夜晚在母亲手中便活了。母亲解开由蓝布床单缝合的大布袋,新弹的棉花如云朵涌出,带着阳光的干香。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取一簇棉花放在做饭的案板上,左手轻握着光滑的高粱秆将它放在棉花上,用右手轻轻细细搓捻,抽出高粱秆后形成空心长棉条“花绩”“捻子”。我家土墩屋里静极了,此时只有棉絮被撕开的轻微“咝咝”声,软得让人心也跟着塌陷。一搓,一捻,一转,一抽,胖嘟嘟的长棉条便温顺地伏进柳条筐,像一根根温润的玉簪。我常蹲在一旁看,问母亲:“妈,这棉花软软的,能直接穿吗?”母亲笑了,手指灵巧地作业着:“傻孩子,这才是个头儿,得纺成线,织成布,才能做成衣裳呢。”那笑容里,是对未来新衣的笃定和期盼。

纺线是母亲的重要事务,纺花车是母亲的一件“宝贝”。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它是我们家重要的“生产工具”。母亲真正的纺线多在农闲时或夜晚,母亲在纺车前坐定,开始她的纺线工作。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母亲坐在纺车前,她左手捏着长棉条“花绩”,轻轻拉出线头,右手慢慢摇动纺车,纺车便发出“嗡嗡”“吱呀”的声音,如同一首悠扬的歌谣,长棉条“花绩”在母亲的手中一点点变成细线,棉纤维被捻合成细线缠绕在锭子上,母亲的动作熟练而专注,她的眼神中透露出对生活的坚韧与执着。
每个夜晚,都被母亲这纺线的声音充满了,初听单调如蜂鸣,静心细品,便有了旷野的风声、春蚕食桑的沙沙声。那声音绕着屋梁,绕着母亲鬓边的碎发,绕着我昏昏欲睡的眼,那声音是乡村夜晚最温柔的旋律。母亲侧着腰,左手平稳地向后上方抽送棉条,手臂划出悠长的弧线。她的目光望着虚空某处,柔和悠远,仿佛神思也随棉线去了远方。棉线听从嗡鸣的号令,从她指尖心甘情愿地吐出,缠绕成饱满的线穗。这抽、送、扬、回,周而复始,像一场沉默而优美的古老舞蹈。我趴在温暖的被窝口,就着如豆的煤油灯看漫画书,目光却总被母亲和那神奇的纺线吸引。夜半醒来,昏暗光影幢幢,母亲巨大的身影投在土墙上,纺车依旧嗡嗡唱着,与窗外的风应和。“妈,咋还不睡?”我咕哝。“这就好,这就好。你睡你的。”那纺花车的声音,是黑夜的安稳,是母亲的歌谣,是家的暖意,也是我童年记忆中最动听的音乐。
母亲的纺线声,春天和着蛙声,夏天和着蝉鸣声,秋天和着虫叫声,从初春到初秋,纺出的洁白的线穗累积了满满的一筐。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浆洗。纺出的棉线柔软易粘连,母亲用面汤熬成了浆水,将棉线浸泡在浆水中,浸透、揉匀、揉透,挤干水分后再放在院中晾晒,风吹过,棉线绷得笔直,干了之后再用棒槌捶打使其挺括结实,便于后续织布,也经得住织布机的拉扯。

接着,准备织方格布、条纹布,会被母亲染成各种颜色。母亲用买来的染料,将它们染成深沉的毛蓝、靛青、朱红,或是朴素的土黄、赭石,染缸里升腾起特有的气味,那是过年热闹的前奏。红的像火,蓝的像海,黄的如金……这些彩色的线,不仅将为我们织出温暖的衣物,更将为我们织出对生活的美好憧憬。若计划织成白布,母亲便在织完布后,再按染布工序染成各种颜色。
当然,织布机是母亲的“舞台”,也是她展现智慧与勤劳的地方。每当浆线、染线完成后,而后便是经线、纬线,一切就绪后,母亲便会将它们整理妥帖,放在织布机上。母亲坐在织布机前,腰紧贴与织机布卷相连的腰带,一手板机档,一手握梭子,穿梳子、扣筘齿,脚踩踏板上下交替,手和脚配合默契,“哐当——哐当——”的织布声,在秋夜里敲出安稳的节奏,形成协调自然连贯而美妙的音律。梭子线在母亲的手中飞快地交织,棉布便在母亲的手中,一寸寸变长。
母亲织出的白布,白生生的,等着染成神秘的蓝、沉厚的黑,素雅的灰后,叠得整整齐齐存放,摸上去感觉它带有草木与阳光的气息,母亲用手抚过布面,眼里藏着温柔的期许,仿佛已经看到了一家人过年穿上新衣裳的模样。母亲织出的五颜六色的布,质地厚实,图案精美,不仅为我们做了衣服,还做了床单、被罩等。那些布,就像一幅幅生活的画卷,记录着母亲的辛勤付出和对家庭的无私奉献。织布机的声音,是母亲与生活的对话,也是我们成长路上最坚实的依靠。
进入冬天后,这些布匹被母亲铺在苇席上,比量着,裁剪着。蓝黑灰是主调,父亲的褂子,哥哥的罩衣,耐磨的床单被里,都在母亲的剪刀下有了雏形。女孩子总有些特别的盼头,母亲会用攒下的布票,走几里路去镇上的供销社,挑几块蓝布、黑布,细细挑拣,摸了又摸,生怕选到不结实的料子,那布票,是一家人省吃俭用攒下的,每一寸,都连着日子的甜。母亲也会选一块素净的灰布,那是给父亲做中山装的,父亲是教书先生,过年走亲访友,总要有件体面的衣裳。也会扯回些翠花布面,那翠花布,红的花,绿的叶,那是为我妹妹们过年做罩袄的外衣,在粗布的世界里,添了几分鲜活的美,那是母亲留给她女儿的小美好,在清贫的日子里,揉进了几分温柔,也藏着少女隐秘的欢喜。母亲飞针走线,棉袄棉裤外褂子,渐渐成形,厚实笨重,却饱含着阳光与棉絮的暖意。
新鞋更是费工夫,做单鞋棉鞋的工作,母亲在一年四季里都在做着准备,白天空闲时,针线就没有离开过母亲的手。针线筐,是母亲的另外一个忠实的“伴侣”,母亲的针线筐,是用细柳条去了皮编织而成,岁月的磨砺让它变得乌黑发亮。筐里装满了针头线脑、碎布条、纽扣、顶针、剪刀、尺子……这些看似平凡的物件,在母亲手中却变成了神奇的魔法工具。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只要一得空,母亲便会坐下来,打开针线筐,开始她的“创作”。她会用针线为我们做过年穿的棉鞋,缝补我们磨破的衣裳,将碎布拼接成漂亮的图案,为我们的衣服增添新的色彩。那些针线在母亲的手中穿梭,仿佛是她与我们心灵沟通的桥梁,每一针每一线都蕴含着深深的爱意。针线筐里,不仅装着针线,更装满了母亲对我们的牵挂与关怀,它是母亲爱的容器,永远装满了温暖与甜蜜。


豫东平原的盛夏,蝉鸣聒噪,暑气蒸腾,屋外的日头烈得晃眼,母亲却总在这样的时节,开始为我们兄妹几人筹备过年的新鞋。
那时的日子清简,没有琳琅满目的鞋店,没有各式各样的成品鞋,过年能穿上一双母亲亲手做的新鞋,便是孩童心里最真切的期盼。母亲做鞋,第一步总要打袼褙,这是千层底的筋骨,容不得半点马虎。她翻出家里攒下的碎布、穿旧的衣料,青的、蓝的、碎花的,都是日子里攒下的温软。麦面熬成的糊,稠稠的,带着谷物的清香,母亲用刷子细细抹在门板上,将碎布一层一层平展展糊上去,边角对齐,不留一丝褶皱,仿佛在铺展一段温柔的期许。糊好的袼褙便晾在院里的晾衣绳上,任盛夏的阳光一遍遍晒透,从绵软的布片,慢慢变成硬挺平整的“格巴子”,摸上去厚实,带着阳光的温度,也藏着母亲的用心。
待袼褙晒透收进屋,母亲便开始裁样纳底。她有好几张磨得光滑的鞋样,按我们兄妹的脚码一一比对,用剪刀细细裁下,一层又一层叠起,七八层的袼褙,便是千层底的雏形。纳底的线,是母亲用粗棉线捻的,结实耐用;纳底的针,是粗粗的钢针,顶针是铜制的,磨得发亮,套在母亲右手的中指上,是她做鞋时最贴身的帮手。昏黄的煤油灯下,母亲坐在床沿,将鞋底顶在膝盖上,针穿过厚厚的袼褙,铜顶针轻轻一顶,针尖便露了头,再用手捏住针尾,带着棉线用力一拉,“哧啦”一声,线便紧紧嵌进了布纹里。这一声轻响,伴着窗外的虫鸣,成了童年夜晚最温柔的背景音。
一双鞋底,要纳上密密麻麻的针脚,横竖交错,整整齐齐,母亲说,针脚密了,鞋底才耐磨,过年走亲戚走再多的路,也不会破。这一纳,便是六七个夜晚,母亲的指尖总在灯光下翻飞,有时夜深了,我迷迷糊糊睁开眼,还能看见她低头纳鞋的身影,鬓角的碎发贴在额前,被灯光映出一层柔和的光晕。偶尔,针尖会不小心扎进母亲的指尖,殷红的小血珠冒出来,母亲只是轻轻吮一下指尖,揉一揉,便又继续纳鞋,眉眼间没有半分倦意,只有一种淡淡的温柔,像春日的溪水,淌在岁月里,也淌进我们的心底。那一点细微的疼,她从不说,只化作针脚里的密实,藏进对儿女的牵挂里。

纳好的鞋底,厚实又绵软,接下来便是上鞋帮。母亲总挑耐磨的灯芯绒做鞋面,藏青的、枣红的,是哥哥们的,浅粉的、浅蓝的,是我和妹妹的。裁好的鞋帮,母亲会细心填上棉絮,细心锁边,针脚依旧细密。上帮时,母亲将鞋帮与鞋底对齐,用细棉线一针针缝牢,拉拽之间,鞋面便服服帖帖地裹住了鞋底,一双鞋的模样,便渐渐清晰。妹妹们的小鞋,母亲总不忘添上几分童趣,在鞋头绣上一朵小小的桃花,或是缝上一颗彩色的小布扣,简单的装饰,便让小小的鞋子多了几分可爱,妹妹们见了,总欢喜地凑在一旁,叽叽喳喳问着什么时候能穿。
日子在母亲的针线间慢慢走,从盛夏走到寒冬,从蝉鸣走到落雪,一双双新鞋便在年关将至时,整整齐齐摆在了床头。新鞋总是最先做好的,母亲会先让我试穿,刚做好的新鞋,硬邦邦的,硌着脚,我皱着眉抬脚,母亲便笑着揉了揉我的脚,轻声说:“新鞋都这样,穿穿就软和了,过年走亲戚,踩着新鞋,不冻脚。”话语简单,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满是踏实的守护,像冬日里的暖阳,烘得人心头发热。我踩着新鞋在屋里走几步,鞋底踩在地上,发出轻轻的声响,那声响里,是母亲一针一线的温柔,是年的味道,也是家的温暖。
终于到了除夕,簇新的衣裳鞋子整整齐齐叠放在枕边。粗布是硬的,颜色是土气的,远不如后来的“洋布”鲜亮。可穿上身的那一刻,那份沉甸甸的温暖,带着纺车的嗡鸣,带着母亲指尖的温度,带着棉田里整个夏天秋天的阳光,便紧紧包裹住了身体。那是笨拙的、实在的暖,一种让人心安的力度。年初一,穿着新衣新鞋走在拜年的路上,寒风猎猎,心里却像揣着个小火炉。母亲看着我们,眼里有疲惫,更有满足的光。她身上或许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袄和深蓝的外罩,可全家人的新,就是她最大的体面。

过年期间,我穿上母亲做的新衣新鞋,跟着家人走亲戚,全身暖暖的,心里也暖暖的。新鞋踩在雪地上,不滑不冷,走再多的路,也觉得安稳。那时的我,只顾着欢喜于新衣新鞋的新鲜,却不懂母亲在四季里的忙碌,不懂那一盏煤油灯下的坚守,不懂那针尖划过指尖的疼,都化作了衣服的绵软、棉鞋的温暖。如今想来,那一件件母亲缝制的新衣,那一双双母亲手工纳制的新鞋,哪里只是普通的衣服、鞋子,那是母亲用针线缝起的牵挂,是岁月里最温柔的陪伴,是藏在年节里,最醇厚、最绵长的爱。
如今,日子好了,母亲的针线筐、纺花车、织布机都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们在我心中的地位却从未改变。它们是母亲的象征,是岁月的印记,更是我心中永远的温暖与力量。每当想起它们,我就会想起母亲那勤劳的身影,想起她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如今,日子好了,衣柜里的衣裳各式各样,鞋子也换了一双又一双,可总忘不了七十年代初的那个腊月,忘不了母亲灯下缝衣的模样,忘不了那双千层底的新鞋,忘不了那件温软的新衣。那一身崭新,裹着豫东平原的烟火,裹着家人的爱,裹着岁月里最珍贵的温暖,在记忆里,永远鲜亮。原来过年的新衣新鞋,从来不止是一身衣裳,一双鞋子,而是藏在清贫里的希望,是一家人在一起的圆满,是刻在心底,永远的年味儿。
如今,每逢过年,我总会想起母亲在灯下缝衣服、纳鞋底的身影,想起那一声“穿穿就软和了”的温柔,想起身上那一件件新衣,想起脚下那一双双新鞋,踩着岁月的暖,走过岁岁年年,而母亲的爱,便如那衣服缝合的针线,便如那千层底的针脚,密密匝匝,缠缠绵绵,伴我走过往后的每一段路,温暖如初!

2026年2月10日写于北京书斋

☆ 本文作者简介:王成伦,河南省西华县人,曾任海政电视艺术中心政委,海军大校,现居北京。
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编辑:易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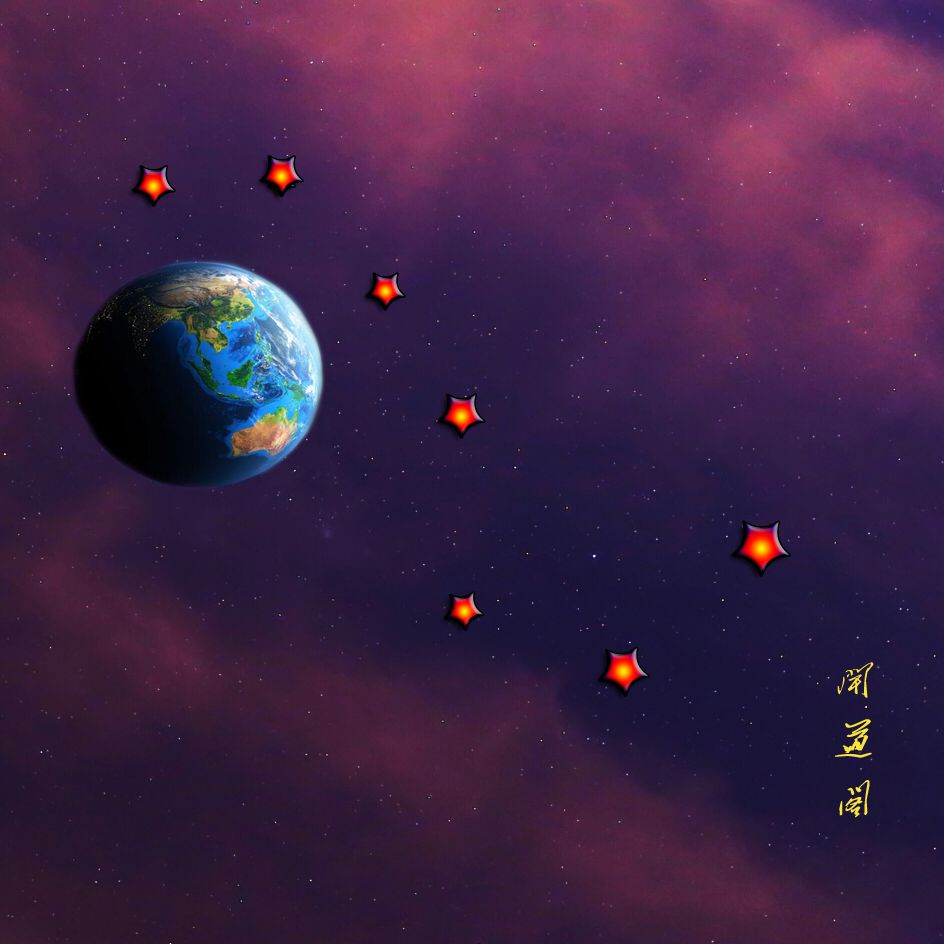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