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an Kolesnikoff
声音导演 / 茜茜


此刻正值二月,立春已过。
如果你身处北方,大概正经历着这样的春天:积雪开始消融,原本洁白的世界被泥泞的“黑”一点点侵蚀,空气里悬着冰冷潮湿的水汽,冷风呼啸而过。它不是“草长莺飞”的那种温柔春景,而更像高纬度地区初春的常态——乍暖还寒、混沌未明,仿佛春天尚在路上,却已把痕迹留在地面与呼吸里。
一百多年前,年轻的帕斯捷尔纳克在俄国的二月也撞见了这样的春天,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著名的《二月》。
全诗开篇一句“二月/蘸点墨水就落泪”,几乎是把“写作”与“哭泣”直接焊接在一起:墨水与泪水不再分属理性与感性,而像同一种液体的两种形态。
写作并非“表达情绪”的结果,反倒像情绪本身的生理反应:一蘸墨,就落泪。这是一种完全不经修饰的、近乎原始的创作冲动。
更重要的是,这首诗里的“二月”并不是日历上的月份,更像是一种物质状态。
“直到轰鸣的泥沼
燃起黑色的春天”
融雪的泥沼竟然“燃”,春天竟然是“黑”的。“燃”不是温暖的火,而是二月初春融雪翻涌、泥沼轰鸣带来的强烈动势:世界在加速、在逼迫,春天像情绪与语言一样被“点着”。
“黑”也不只是阴郁,而是初春的真实颜色与质地:雪一化,湿土、脏雪、浑水露出来,春天在明媚前先以暗色显形。
诗歌第二节的动作更像一种“自我驱逐”:离开室内,雇一辆轻便马车,穿过钟鸣与轮响,
“奔向那比墨水和泪水
更喧响的滂沱大雨中去”
诗人仿佛不是在躲避,而是在主动投身——把自己交给更猛烈的现实,让内心的哭声被外部世界的声响覆盖,反而获得真正的强度。也许只有在雨里,泪才不显得多余;只有在喧响声中,恸哭才不显得矫情:情绪被世界“合法化”了,它不再是个体的软弱,而是与季节同频的回应。
第三节是全诗最具“重力”的画面:白嘴鸦如焦梨般坠入水洼,
“……轰然间
枯涩的忧伤砸入眼底”
此处的动词“обрушить” 带很强的力度与突然性,常有“塌落、倾覆、猛砸”的感觉,这表明诗中的忧伤不是轻飘飘的情绪,而是能下沉、能撞击、能压低视线的实体。
“世界的坠落”与“目光的坠落”连成一条线:鸦群从枝头坠落,忧伤便被砸入眼底;外部的重力转化为内部的重力。读到这里,很容易想起我们自己的某些时刻:不是“我很难过”,而是难过像一块湿冷的东西突然压下来,压进眼底,也压低了视线。
而最后一节,诗的真正旨归才显露出来:
“雪融之处渐黑
风被叫声犁裂”
——世界被噪声刻出沟壑。就在这种破碎里,出现一句近乎悖论的诗学宣言:
“越偶然,越真实
诗行在恸哭中自成”
这里的反身动词“слагаться”在语感上常带一种“不是被某个主体硬写出来,而是自己在某种规律下合拢成形”的意味。此处也许诗人想表明,诗不是被“写出来”的,而是被“合起来”的、在偶然中自动归位的。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创作需要清醒、秩序、计划;但这首诗偏要反过来告诉你:当你被现实撞得破碎,当你放声恸哭,当你无法把句子说完整时,语言反而更可能找到它“唯一正确的位置”。
所谓“偶然”,不是随便,而是“真实”的体现,是一种不可辩驳的确凿感:这句非这样不可。帕斯捷尔纳克在自传中谈到创作时曾写道:“真正的创造往往诞生于内容充溢于艺术家心胸,他在匆忙中以旧的语言说出新的话语的瞬间”,那是一种被迫的急促,也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生成。
所以,这首《二月》真正引人共鸣的,并不只是它在“写春天”,而是它写出了一种我们都经历过的季节:你尚未走出寒冷,却已经听见春天的脚步;你仍在泥泞里,却不得不承认某种新生正在燃烧——只是它先以“黑色”出现。
它提醒我们:低谷并不总是空白,混乱也可能是生成。因为有时,诗句确实是在近乎恸哭的情绪里自然合成的;而我们最真实、最难以伪饰的那部分,也常常在下意识的瞬间,才显现出来。

荐诗 / 木樨
俄罗斯文学研究者
日常喜欢读诗、译诗、写诗
加郑艳琼姐姐,带你入读睡群搜诗 / 聊天 / 扩列
第4719夜
守夜人 / 小范哥
诗作及本平台作品均受著作权法保护
投稿请发表在诗歌维基(poemwiki.org)
广告&商务 微信:zhengyq(注明商务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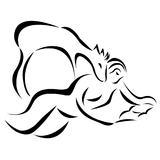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