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丨王成伦
之一:岁岁年关,母爱如灯(序言)
之二:过年,母亲备好了丰富的干菜
之三:过年,母亲为家人缝制了新衣新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豫东平原上的王家堂,腊月的寒风吹遍凝着霜的麦田,掠过村头的老柳树,刮过家家的土院墙,也吹进了户户的土墩房。腊八已过,每家的小院里,就漾起了过年的筹备声。于那时的家乡人而言,过年从不是花哨的热闹,而是实打实的筹备,最要紧的、头等的大事,便是备粮备面,备齐小麦、玉米、绿豆、大豆、高粱、红薯干各种粮,磨成各色的面,把正月里的吃食,稳稳当当攥在手里。
那时,家家日子过得紧巴,粮食都是生产队分下来的口粮,数量不是太充足,要撑过一年四季的三餐。粮食是金贵的,白面更是稀罕物,平日里舍不得多吃,多是红薯干面掺着粗粮度日。那年月,攒粮的过程,藏着一家人整年的省吃俭用,或许是夏收时多留的一袋子小麦,或许是秋收时晒得格外多的一筐红薯干,或许是平日里舍不得吃的一升绿豆,点点滴滴,都攒成了过年的底气。唯有过年,才舍得把攒了一年的家底翻出来,为的就是过年时能让全家人吃上十天半个月的饱饭。平时可以节俭点、紧吧点,可过年,不一样。过年,是穷日子攒出的一口甜,是艰苦岁月里,用粮食堆出的一场仪式。

年的味道,从父亲母亲备粮开始,便在烟火里慢慢酿浓。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就听见母亲和父亲念叨:过年的粮啊,咱家玉米、大豆、高粱、红薯干都足够,小麦还差半布袋,绿豆还得弄二十来斤。母亲吩咐父亲,拉一麻袋红薯干到集上找我舅舅帮着置换成小麦,我舅舅是交易商,有办法解决;绿豆就拿钱买吧。父亲一大早就去赶集了。我好奇地问母亲:“妈,弄那么多粮食干啥?”母亲说:“过年,不是光有新衣穿,还得吃上饭,不光要吃,还得吃得好呀。”她接着又说:“你看,这小麦磨的白面,可以蒸蒸馍、蒸花馍、做饺子;玉米面能做菜团子;绿豆面是炸丸子用的;高粱面耐嚼,混着其它面蒸馍,多一份粗粝的香呢;大豆面和红薯干面做野菜角,粗粮细作,最顶食、管饱。”母亲见我不吱声了,便一边干活一边自言自语说:“有粮有面,样样都有,样样都够,一个正月里有得吃,心就不慌了呀。”
那时我不懂,慢慢长大了,我才悟到,过年最重要的,不是鞭炮有多响,不是新衣有多亮,而是家里有粮,缸里有面,灶上有饭,人,才敢安心的过一个年。
备粮的日子,是腊月里最忙碌的光景。母亲便会从粮囤里弄出粮食,一点点翻拣。选小麦,母亲最是用心。家中粮囤里的小麦,颗颗饱满,却沾着些许尘土与麦糠。母亲搬来粗瓷大盆,把小麦一瓢瓢舀进去,倒上井水淘洗,手在麦子里反复揉搓,清水浑了便换,直到麦粒洗得干干净净,泛着温润的麦黄色。遇着天阴,便用干净的湿巾一遍遍擦抹麦粒,连缝隙里的浮尘都不肯放过。淘洗好的小麦,摊在院中的苇席上,让冬日的暖阳慢慢晒透,母亲隔一会儿便去翻搅,指尖抚过温热的麦粒,嘴里念叨着:“晒得干干的,磨出来的面才白、才香、才筋道。”晒透的小麦,颗颗干爽,抓在手里沙沙响,那是最纯粹的麦香,裹着阳光的味道。

母亲说,玉米要晒得干透,磨出来的面才不会发黏;大豆、绿豆要筛去杂质,炸出来的丸子才清香;高粱要搓掉壳才纯正;红薯干要在石臼里砸得细碎,才好磨面。母亲把每一粒粮食,摩挲了一遍又一遍,那是对粮食的敬畏,更是对过年的郑重。
腊月中旬的日子,是被石磨的转动声揉醒的。那时的王家堂,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磨房,青灰色的磨盘被岁月磨得光滑,磨齿间还留着以往的面香。石磨是村民的老伙计,厚重的磨盘,粗实的磨杆,一头连着牲口,一头系着日子。
腊月的天,亮得迟,寒雾还凝在院角的草垛上,母亲便早早去生产队的牲口屋牵牲口,她牵着毛驴缰绳走在土路上,毛驴的蹄声哒哒,母亲的布鞋踩在冻硬的泥土上,留下浅浅的脚印。
母亲给毛驴套上磨杆,蒙上眼罩,磨道里的驴蹄声开始哒哒响,石磨便跟着转了起来,毛驴转圈,磨盘哼着亘古的歌谣,从清晨到当午,吱呀的声响绕着村舍,成了冬日里最动人的乡音。麦粒从磨眼缓缓漏下,经磨齿碾磨,混着细碎的麦麸,从磨缝里涌出来,落在磨盘上,浅黄的粉屑,裹着醇厚的麦香,在冷冽的空气里散开,那是粮食最本真的味道,也是过年最踏实的开端。

我时不时踮着脚往磨眼里添麦子,母亲便笑:“慢些,别弄撒了麦子。”她腰间系着粗布围裙,发梢沾着面粉,像棵会移动的树。细箩筛面时,阳光穿过箩眼,在地上织出流动的银河,母亲的身影浸在这银辉里,渐渐也成了面粉的一部分。
磨小麦面,母亲更是细致到了骨子里。磨出来的粗面料,要倒进细箩里一遍遍箩,她只留磨头四遍的面,那面最细最白,像落了一层薄薄的雪,攥在手里绵软细腻,这是专一留着过年蒸馍、蒸大馍、蒸枣山,还有炸油条用的,是年节里最金贵的。箩面的活最是费力,母亲端着沉甸甸的细箩,前后推送回拉、颠摇拍打,腰弯着,胳膊酸了便歇上片刻,揉一揉再继续,面屑落在她的头发上、肩头、衣襟上,不一会儿,她便成了“白面人”,唯有眼睛,亮闪闪的,映着对年的期许。
接下来几天,是磨玉米面、高粱面、绿豆面、大豆面、红薯干面,母亲也会用细箩细细箩过,去掉粗渣,只留细腻的粉面,玉米面黄澄澄的,高粱面泛着浅浅的红,绿豆面、大豆面呈着清浅的绿,红薯干面带着淡淡的甜,各有各的颜色和香气。

磨面从来不是轻松的活,四五个半天下来,母亲的胳膊酸了,腰也僵了,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可她从不说累。一上午的磨房时光,石磨转个不停,箩面的动作反复不停,面粉的粉末飘在空气里,沾得母亲浑身都是白的,连睫毛上都挂着细细的面屑,她抬手擦一把脸,脸颊便添了几道白印,可看着簸箩里越积越多的细面,她的脸上总挂着笑意。那些粗面料,母亲也不肯浪费,留着平日里蒸窝头、贴饼子,她说:“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粗面细面,都是地里长出来的,不能糟践。”
我那时年纪小,最盼着星期六星期天,因为能跟着母亲去磨房,帮着她做些力所能及的活。母亲往磨眼里添粮食,我便站在牲口旁,牵着缰绳,偶尔轻轻赶一下,让牲口走得慢些、稳些,石磨便转得匀匀的,面粉便落得更细。磨完面,母亲收拾簸箕与箩,我便牵着牲口,一步步送回生产队的牲口屋,牲口的蹄声哒哒,我的小脚步喳喳,走在腊月的暖阳里,身后跟着母亲的身影,还有一路的面香。有时我会仰着小脸问母亲:“妈,磨这么多面,要蒸好多好多馍吧?”母亲擦着我脸上沾的面屑,笑着说:“傻孩子,过年嘛,就是要吃白面馍,要团团圆圆,面备足了,日子才过得踏实,年才过得有滋味。”我似懂非懂,只觉得母亲的手暖暖的,擦过脸颊,连面屑都带着甜。
磨好的面,母亲会分别装好,白面装进厚实的粗布口袋,扎紧口,放在垫得高高的木板上,防着受潮;玉米面、高粱面、大豆面、绿豆面、红薯干面,分别装进面缸里、面盆里、面袋里,放在堂屋里间靠窗户的木案上,随手便能取到。这些面,母亲总要在腊月二十前后悉数备好,看着一袋袋、一缸缸、一盆盆的面粉,她的眼里便满是安稳,仿佛备好了面粉,便备好了一家人过年的欢喜,备好了岁月的温软。


那些日子,磨房里的石磨声、箩面的颠摇声、牲口的蹄声,还有母亲轻声的念叨,混着麦香与豆香,成了我儿时记忆里最深刻的腊月声响。母亲的身影,在粮囤边、在晒麦席旁、在磨房里,被腊月的暖阳拉得长长的,她的手,虽然因常年劳作磨出了厚茧,却能把粗糙的粮食,变成五彩的面粉、细腻的面粉,也能把清贫的日子,揉得温温的、柔柔的。
如今想来,母亲磨的何止是面粉,是对一家人的牵挂,是对过年的殷殷期许,是把日子过好的执着与智慧。那一袋袋、一缸缸、一盆盆面,看似朴素,却裹着冬日的暖阳,沾着母亲的汗水,藏着最醇厚的人间大爱。她用一双手,选粮、淘洗、磨面、箩面,把对家人的爱,一点点揉进每一粒面粉里,让年节的饭桌,满是香甜,让清苦的岁月,满是温暖。
岁月流转,如今的日子好了,豫东平原的乡村早已变了模样,粮囤里的粮食满了,超市里的面应有尽有,再也不用常年攒粮食,再也不用亲手磨年面,再也不用算着日子吃面食,可我总忘不了母亲在腊月里磨面的模样,忘不了磨房里的麦香,忘不了她满脸沾着面粉的笑容,忘不了她牵着牲口、我跟在身后的腊月时光。那些母亲亲手磨出的面粉,不仅填满了我们儿时的胃,更温暖了我们的一生。
原来,那年月,母亲磨碎的是粮食,揉进的是日子,保证的是温饱,更是一家人团圆的暖,是那时过年最踏实的盼。无论时光如何变迁,那份对粮食的敬畏,对温饱的珍惜,对过年的郑重,都藏在豫东平原我家乡王家堂的年俗里,藏在一代人的记忆里。因为那面粉里,藏着母亲的爱,藏着乡土的情,藏着最朴素也最厚重的人间温暖,岁岁年年,从未消散。

2026年2月12日写于北京书斋

☆ 本文作者简介:王成伦,河南省西华县人,曾任海政电视艺术中心政委,海军大校,现居北京。
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编辑:易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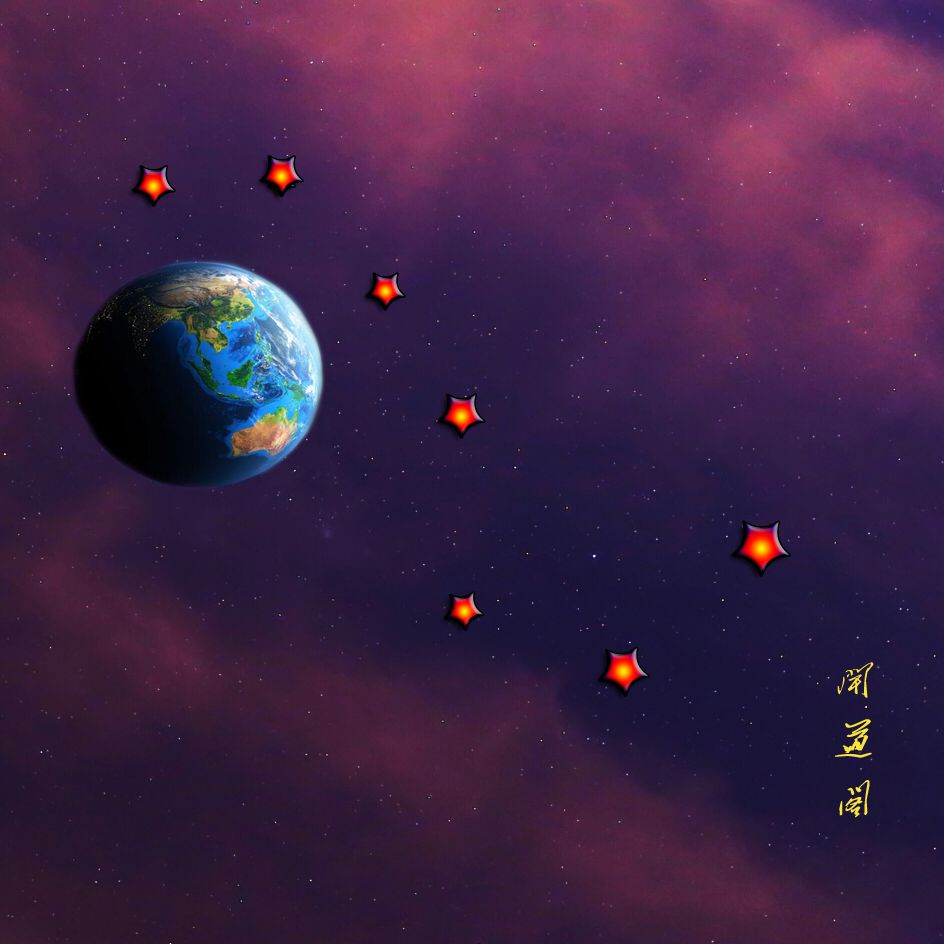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