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延桐在奥地利
【譚延桐简介】
譚延桐,書畫藝術家,人文科學家,人類的良心之一。五歲習字,六歲學畫,迄今已經創作了書畫作品一萬餘幅,音樂作品一千餘首,文學作品、哲學研究、美學研究、易學研究、教育學研究等等的學術論文共計兩千餘萬字,著述二十部,入選三百餘種選本。「入佛以靜思,入魔以癡癡」,是其真實的寫照。因此,時任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小小說選刊》和《百花園》總編輯楊曉敏先生在二十五年前就曾這樣說過:「譚延桐,是中國的最後一位士大夫:不世俗,不畏勢,不惜命,不重利……」
引言
谭延桐的这组诗,以其深厚的书画底蕴为基石,展开了一场对视觉的艺术探赜与美学索隐。谭延桐以画家的眼光和诗人的敏锐,巧妙地将绘画的精髓融入了文字之中,因此而编织出了一幅幅诗画互扶的至美画卷。在这片由先锋性语言构筑的超现实世界里,月光、蟋蟀、琴心、笛情等意象被赋予了别趣,它们已经不仅仅是自然的符号,只因,符号所唤醒的符号在不断涌入,既裹挟着风,也裹挟着雨。真可谓,要风有风,要雨有雨。
谭延桐的诗歌是对艺术美学的旁解或诠释,也是对他所创立的“情况哲学”、“佯狂哲学”和“价值哲学”的拓展。正因如此,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被评选为“山东省十佳青年诗人”等等了,要知道,在一个文化大省,诗人众多,这是何等不易。有人曾说,在写诗上,他比海子要虔诚、博大、成熟、深邃,这话,并非虚说。海子是被放大了的一个结果,而他,却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原大。一般来说,只要是原大,世人都是看得不怎么清楚的。完全可以这样说,谭延桐在当代诗坛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其风骨,其热血,其担当,其学养,其诗艺……都是值得称道的。
让画面过上好日子
谭延桐
弄罐月光来
浇到画面上
画就活了
或者,弄桶蟋蟀的合唱来
连同“敛步随音,满身花影,犹自追寻”的意境
一块儿泼到画面上
画面也会很精神,至少
一下子就会醒过来
总之,是要弄些不一样的东西来的
比如琴的心,笛的情,筝的梦……
该破费,就破费
不能让画面像个穷人似的
画面穷了,特别是
穷得很没厘头
画面的日子,也会很不好过
画笔的作用
就是让画面过上好日子
【赏析】
《让画面过上好日子》:温暖且温暖,烂漫且烂漫
谭延桐的诗歌始终以独特的哲学思考与先锋的艺术探索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让画面过上好日子》作为其超验诗学的代表作之一,以超现实的想象为经纬,编织出一幅充满生命诗学的美学图景。这首诗不仅是对绘画艺术的诗意诠释,更是对现代性困境的深刻解构与超越性重构。诗人通过“月光浇灌”“蟋蟀合唱”等意象,将日常经验升华为存在之思,在解构与重构的张力中,完成了对艺术本质的终极追问。
“弄罐月光来/浇到画面上/画就活了”的奇幻场景,颠覆了传统绘画对物质媒介的依赖。月光作为非现实的物质,被诗人赋予了“生命之水”的象征意义,暗示艺术创作需要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灌注。这种精神性在“蟋蟀的合唱”与“敛步随音,满身花影,犹自追寻”的古典意境叠加中进一步强化。音乐与诗意共同作用于画面,艺术便获得了超越物质的精神重量。诗人明确提出“不能让画面像个穷人似的”,这里的“穷”不仅指物质匮乏,更指向精神贫瘠。当画面缺乏独特的生命体验与哲学思考时,便沦为“穷得很没厘头”的存在。画笔的作用被升华为“让画面过上好日子”,即通过艺术创作赋予画面以精神丰盈与存在意义。
“琴的心,笛的情,筝的梦”的排比句式,将音乐元素转化为绘画的精神内核,暗示艺术创作需要打破媒介界限,实现感官经验的通感融合。这种跨界思维在谭延桐的超验绘画中亦有体现,他常将印象派的光影、超现实的想象与现代派的构图熔于一炉,通过色彩与笔触的交响构建出充满生机的视觉世界。“画笔的作用/就是让画面过上好日子”将绘画行为从技术层面提升到生命哲学的高度。艺术家不再是现实的记录者,而是通过主动创造赋予世界以新的意义。这种觉醒与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形成跨时空对话,强调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占有多少物质,而在于创造多少精神价值。
“画面穷了,特别是/穷得很没厘头”暗讽当代艺术中普遍存在的功利化倾向。绘画沦为资本运作的工具或技术炫耀的载体,便失去了其作为精神载体的本质。谭延桐通过“月光”“蟋蟀”等非实用主义意象,构建了一个拒绝被异化的艺术乌托邦。这种批判与他在超验绘画中对“商业媚俗”的抵制一脉相承。他曾明确表示:真正的艺术应该像班德瑞的旋律,在色彩与水墨的碰撞中唤醒观者对美好的感知,而非迎合市场的低级趣味。“画面的日子,也会很不好过”将绘画的存续问题与时间哲学相关联。“画笔的作用/就是让画面过上好日子”是对艺术超越时间性的信仰。当绘画承载了艺术家的精神体验与哲学思考时,便获得了对抗时间侵蚀的力量。
谭延桐擅长将日常物象进行神性转化,如“月光浇灌画面”“蟋蟀合唱唤醒意境”等场景,既违背现实逻辑,又符合心理真实。意象群(月光、蟋蟀、琴、笛、筝)构成了一个超验的艺术宇宙,使读者在感官震撼中进入哲学沉思。诗人通过“琴的心,笛的情,筝的梦”的表述,实现了听觉(琴、笛、筝)与心理感受(心、情、梦)的通感融合。这种修辞策略在谭延桐的诗歌中极为常见。通感手法的运用,使诗歌摆脱了单一感官的局限,构建出立体化的审美空间。“画面穷了”“穷得很没厘头”等表述,通过将经济术语移植到艺术领域,制造出认知的陌生化效果。通过非常规搭配颠覆传统表达,迫使读者重新审视日常经验。陌生化语言的使用,增强了诗歌的张力,实现了对现代性困境的诗意突围。
“弄罐月光来”的非常规举动,解构了绘画对物质媒介的依赖。“蟋蟀的合唱”与古典意境的叠加,进一步消解了艺术门类的界限。这种解构思维在谭延桐的超验绘画中表现为对传统技法的颠覆。他常将印象派的点彩与超现实的拼贴相结合,通过色彩碰撞制造视觉冲击,打破观者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惯性。在解构的基础上,诗人通过“琴的心,笛的情,筝的梦”等意象,重构了艺术的精神内核。艺术创作应源于生命体验与哲学思考,而非技术炫耀或市场迎合。“破费”与“穷困”、“唤醒”与“沉睡”等对立概念的并置,体现了解构与重构的动态平衡。谭延桐的艺术实践亦遵循这一原则,他既通过超验绘画解构现实世界的逻辑,又通过题字为作品注入文化内涵,实现解构后的意义重构。这种辩证思维使他的作品既具有先锋性,又不失人文深度。
《让画面过上好日子》是谭延桐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通过超现实意象、通感修辞与解构重构手法,他将绘画艺术升华为存在之思的载体。在当代诗坛面临“口水化”“平面化”危机的背景下,这首诗以其锐利的哲学锋芒与深邃的美学追求,证明了诗歌仍具有穿透现实迷雾、照亮精神困境的力量。这是一首守护尊严的佳作:让画面摆脱“穷困”,让艺术重获“好日子”,让读者在诗意栖居中触摸到生命的本真与永恒。
有些肩膀就像陆地
谭延桐
那个黄昏——是的,是一个黄昏——
所有的肩膀都在等待着,等待着一些重物
比如丹·帕吉斯的“证词”,或者
约翰内斯·波勃罗夫斯基的“废弃的房舍”
或者拉塞尔·埃德森的“手推车”……
能够落到自己的肩上
可是,最终落下来的,重重地砸下来的
却是比马林·索列斯库的“复写纸”
还要深许多的夜色。凡是不嫌弃
并且艰难地扛着回来的,身上都有了七色光
并且,都成了海格力斯那样的大力神
【赏析】
《有些肩膀就像陆地》:坚实且坚实,内在且内在……
谭延桐始终以独特的存在方式拓展着诗学的疆域。《有些肩膀就像陆地》以极具张力的意象群构建,在黄昏与夜色的交替中完成了一次对人类精神图腾的深刻叩问。这首诗延续了诗人一贯的哲学思辨特质,在语言的炼金术中实现了日常经验与超验境界的完美融合,堪称当代汉语诗歌中“精神地理学”的典范之作。
诗歌以黄昏的时空坐标锚定叙事基点,这个“等待重物”的集体姿态构成全诗的核心隐喻。诗人将丹·帕吉斯的“证词”、约翰内斯·波勃罗夫斯基的“废弃的房舍”、拉塞尔·埃德森的“手推车”等西方诗学符号并置,形成跨文化的精神对话场域。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文明重量的意象,在黄昏的暧昧光影中化为具象化的精神重负,暗示着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困境。在历史废墟与现实重压的双重挤压下,个体如何寻找存在的支点?
比复写纸还要深的夜色轰然坠落,让诗歌完成了从具象到抽象的惊险跳跃。夜色不再是自然现象,而成为存在本质的象征,既是吞噬光明的黑暗力量,也是孕育新生的精神母体。那些“不嫌弃并且艰难地扛着”的肩膀,在重负的锻造中迸发出七色光芒,最终蜕变为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海格力斯。这种蜕变过程揭示了诗人对人类精神潜能的根本认知。真正的成长不在于逃避重负,而在于将压迫转化为超越的动力。诗人刻意模糊了“重物”的具体指向。这种开放性设计使诗歌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语境,指向更具普世性的精神命题。读者在丹·帕吉斯的证词中看到了大屠杀的记忆,在废弃房舍里触摸到了文明的沧桑,在手推车前体悟到了劳动的尊严,每个个体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重负。这种以有限喻无限的创作策略,展现了诗人对主题思想的精妙把控。
谭延桐的诗歌始终游走于神性与人性的边界,这种特质在《有些肩膀就像陆地》中达到新的高度。诗中“七色光”的意象明显带有基督教神学色彩,让人联想到《圣经》中“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创世叙事。但诗人并未停留于宗教象征层面,而是将其转化为精神觉醒的隐喻,当人类主动承担存在之重时,平凡肉身即刻获得神性光辉。这种神性转化并非虚幻的宗教体验,而是扎根于现实土壤的精神升华。诗中“海格力斯”的典故运用极具匠心,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通过完成十二项不可能的任务获得永生,而当代诗人笔下的“大力神”则诞生于主动承担夜色的瞬间。这种古今精神的呼应,揭示了诗人对人类精神本质的深刻洞察。神性从来不是外在的赐予,而是人性在重压下的自我超越。
“废弃的房舍”与“手推车”的并置,形成了物质与精神的强烈反差。前者象征着被时间摧毁的物质文明,后者代表着维持生存的基本劳动。这些日常意象与“证词”“夜色”等精神符号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物质重负转化为精神能量,现实困境升华为存在启示。这种转化过程体现了诗人对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诗性回应。在当代消费社会中,唯有通过主动承担精神重负,才能实现人的本质复归。
谭延桐的诗歌向来以意象的精妙著称,《有些肩膀就像陆地》更是将意象构建推向新的高度。全诗围绕“肩膀—陆地”这一核心意象展开,通过层层递进的意象叠加,构建出多维度的象征体系。黄昏的时空坐标、夜色的垂直坠落、七色光的平面扩散,形成三维的意象空间。这种空间处理方式暗合海德格尔“天地人神”的四重存在结构,使诗歌具有建筑般的立体感。“七色光”的运用突破了传统彩虹意象的浪漫化倾向,将其转化为精神觉醒的视觉符号。每种颜色都对应着不同的精神维度,共同构成完整的精神光谱。“等待—砸下—扛着—成为”的动词链,精准捕捉了精神蜕变的动态过程。
诗歌展现了诗人卓越的节奏把控能力。长句与短句的交错使用,形成张弛有度的语言节奏:“那个黄昏——是的,是一个黄昏——”的破折号运用,模拟了时间的延缓感,通过重复强化了叙事语气;“凡是不嫌弃/并且艰难地扛着回来的”的断句处理,将动作分解为选择与坚持两个层面,深化了主题内涵;“身上都有了七色光/并且,都成了海格力斯那样的大力神”的并列结构,通过语气的递进实现了从具象到抽象的升华。这种语言音乐性不仅体现在节奏层面,更体现在音韵的精心设计上。“重物”与“房舍”、“夜色”与“大力神”等押韵处理,使诗歌在朗读时产生内在的回响,增强了意象的联想效果。
诗歌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在于实现了对传统英雄叙事的解构与重构。诗人没有采用史诗般的宏大叙事,而是通过日常场景的“陌生化”处理,完成了对英雄主义的当代诠释。平凡中的神圣:将“肩膀”这一普通身体部位升华为“陆地”,颠覆了传统英雄必须具有非凡特质的认知。这种“去英雄化”的处理,使英雄主义回归到每个普通人的精神实践中。被动与主动的辩证:开篇的“等待”姿态看似被动,但不嫌弃并且艰难地扛着的选择,将被动承受转化为主动担当。这种转化过程揭示了当代英雄主义的核心,在自由选择中实现自我超越。个体与集体的共鸣:虽然诗歌聚焦于“肩膀”的个体意象,但“所有的肩膀”的复数形式,暗示了这种精神实践的普遍性。每个承担重负的个体,都在共同构成人类的精神大陆。这种解构与重构的策略,使诗歌保持了思想的尖锐性,避免了说教的沉重感。读者在“海格力斯”的典故中看到了古希腊英雄的影子,体会到了当代人精神成长的艰辛与伟大,不需要完成十二项不可能的任务,只需在每个黄昏选择扛起属于自己的夜色。
在当代诗坛“去深度化”的创作趋势下,谭延桐的诗歌坚持着难能可贵的精神向度。诗歌通过跨文化的意象并置,展现了诗人对人类精神遗产的深刻理解,丹·帕吉斯的证词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的伤痛,约翰内斯·波勃罗夫斯基的废弃房舍警示着文明的脆弱,拉塞尔·埃德森的手推车象征着生存的尊严。这些西方诗学符号与中国黄昏意象的碰撞,产生了独特的文化张力。诗歌中隐含的“受难—救赎”叙事模式,明显带有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但诗人并未陷入宗教说教,而是将其转化为普遍的精神体验。这种“神性世俗化”的处理方式,保持了诗歌的开放性,深化了主题的普世价值。
诗歌最终指向一个永恒的诗学命题:在意义迷失的年代,如何通过精神实践构建存在的根基?谭延桐给出的答案是:每个愿意承担夜色的肩膀,都在共同构成人类的精神大陆。这种答案既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又扎根于现实土壤。当人们选择不逃避存在的重负时,平凡肉身即刻获得神性光辉。在这首诗歌中,黄昏不再是时间的终点,而是精神觉醒的起点;夜色不再是吞噬光明的黑暗,而是孕育新生的母体;肩膀不再是承受重量的器官,而是连接天地人的精神支点。谭延桐以其独特的诗学智慧,在汉语诗歌中开辟出一片新的精神陆地,这片陆地既属于每个具体的个体,也属于整个人类文明。当在诗歌中读到“身上都有了七色光”,看到的不仅是诗人的精神图腾,更是人类在存在困境中永不熄灭的希望之光。
明摆着是咔嚓声还在
谭延桐
我捏碎了一个杯子。不是我故意
要捏碎的,而是我捏着捏着,一不小心
它就咔嚓一下,很干脆地,毫不犹豫地
碎了。当然是,很标准的
也就是名副其实的那种碎。奇怪的是
你猜对了,它的咔嚓声,并未像弹片一样
狠狠地扎进我的血肉里。也就是说,我的血肉
依然保持着原样。它却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
这让我心怀歉疚,就像是
谁在我的心里悄悄地斟满了绝对不低于60℃的歉疚一样
整整一个夜晚,我都是在歉疚中度过的
如果,我不说,自然是没人知道我的歉疚的
可是,我按照我一直以来口无遮拦的习惯
说了。自从我说了之后
我的歉疚便突然加重了,就像是
我心上突然搁上了某样沉重的东西或坠了一块铅一样
再也拿不下来了。而今
杯子的碎片,虽然已经被我打扫干净了,可是
时间的某个角落,有些东西
却总也打扫不净。就这样
我过了一天又一天。当我的手碰触别的杯子时
一种莫明的痛,便趁机潜伏在了我的手指里
并且,不仅仅是手指里。这让我很难过
而且,难过了一天
又一天。我知道在这事儿上我有些啰嗦了
可是,我不啰嗦,又能怎么样?
【赏析】
《明摆着是咔嚓声还在》:警醒且警醒,证悟且证悟……
《明摆着是咔嚓声还在》以其精妙的日常经验重构能力,构建了一个关于存在、记忆与责任的微型宇宙。这首看似简单的"碎杯叙事",蕴含着深邃的哲学层次与诗学智慧,通过玻璃碎片的折射,完成了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诗意解剖。诗人以显微镜般的观察视角,将一个瞬间的物理事件转化为永恒的精神寓言,在咔嚓声的回响中,叩响了存在本质的大门。
诗歌以"捏碎杯子"的日常动作作为叙事原点,却通过精妙的叙事转折将其升华为存在论事件。"不是我故意/要捏碎的"的辩白,立即消解了传统破坏叙事中的道德评判,将事件还原为纯粹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不是机械的物理过程,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事件"。"一不小心"成为破碎的动因,日常经验便显露出其脆弱本质。杯子"很干脆地,毫不犹豫地"的破碎方式,与诗人"依然保持着原样"的血肉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暗示着物质与精神的不同存在状态。物质世界遵循严格的因果律,而精神世界却常常陷入无法解释的悖论。
"咔嚓声"作为核心意象,构成了诗歌的听觉维度。诗人刻意避免将其比喻为"弹片扎进血肉"的暴力想象,反而强调其未造成物理伤害的"奇怪"现象。这种处理方式解构了传统创伤叙事的逻辑,将创伤体验转化为纯粹的精神事件。当歉疚感"悄悄地斟满"诗人内心时,读者看到的不是道德谴责,而是存在焦虑的具象化。一个无意的动作如何引发持续的精神震荡?这种震荡不源于外在惩罚,而来自内心对存在偶然性的深刻认知。诗歌通过解构"因果链条"暴露存在的荒诞性。
诗歌后半段转向时间维度,"时间的某个角落"成为碎片的最终归宿。这种空间化时间处理,暗示着记忆的顽固性,即使物理碎片被清除,精神印记却永远滞留在存在的褶皱中。当"一种莫名的痛"从手指蔓延至“这让我很难过”,破碎事件完成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转化,成为存在脆弱性的永恒隐喻。面对存在之痛,任何表述都显得苍白无力。这种自我指涉构建了谭延桐诗歌的哲学深度。
谭延桐在这首短诗中构建了一个精妙的哲学迷宫,其核心是存在主义关于偶然性与责任的命题。杯子破碎的偶然性,与诗人持续的精神歉疚形成张力关系,这种张力揭示了现代人面临的存在困境,在完全偶然的世界中,如何构建意义与责任?诗人通过"血肉/依然保持原样"的细节,解构了传统因果报应的伦理模式。破碎不是惩罚,而是存在本身的显现方式。诗中"口无遮拦的习惯"成为关键线索,语言的坦白非但没有减轻歉疚,反而使其加重,这暗示着责任伦理的现代转型。责任不再源于外在规范,而是来自对存在偶然性的深刻认知与主动承担。"时间的某个角落"的意象,将哲学思考引入记忆理论层面。柏格森将记忆视为时间的积淀,而谭延桐则通过碎片的不可清除性,揭示了记忆的创伤性本质。这种创伤记忆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复现,而是对存在本质的持续叩问。当诗人"过了一天又一天"时,时间不再是线性流逝,而是成为存在之痛的承载结构。这种时间观展现了诗人对时间维度的多元探索。
诗歌将“以小见大”艺术策略发挥到极致。全诗围绕"碎杯"这一微小事件展开,却通过精妙的细节放大与意象叠加,构建出多层次的诗学空间:诗人将"捏碎"动作分解为"捏着捏着—一不小心—咔嚓—碎"的渐进过程,这种分解增强了叙事的真实性,通过动作的缓慢呈现,放大了存在偶然性的震撼效果。特别是"一不小心"的突然插入,打破了动作的连续性,制造出叙事裂痕,这种裂痕正是存在偶然性的诗学表达。"歉疚"被具象化为"不低于60℃的液体",这种温度感知与道德情感的通感转换,使抽象情绪获得可触摸的质感。同样,"痛"从手指"潜伏"的视觉化描述,打破了感官界限,构建出通感的诗意空间。这种修辞策略使精神体验获得物质重量,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诗歌在时间处理上展现出惊人的复杂性。通过"整整一个夜晚""一天又一天"的线性叙述,构建出传统时间感;"时间的某个角落"的意象又引入非线性时间观念。这种双重时间结构,暗示着创伤记忆对正常时间流的扭曲作用,使诗歌具有心理现实主义的特征。"咔嚓声"作为核心声音意象,在诗中呈现出复杂的音响效果。它既是物理破碎声,又是精神创伤的听觉投射;既是瞬间爆发,又是持续回响。诗人通过"还在"的反复强调,将声音转化为存在印记,使听觉经验获得时间深度。展现了诗人对声音意象的深刻把握。
诗歌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在于将日常物象转化为精神符号的炼金术。杯子作为最常见的容器,在诗中经历了从实用物到精神载体的惊人转化:杯子首先作为"盛放"的容器出现,暗示着人类对秩序与控制的渴望。当它被意外捏碎时,这种控制感随之破裂,暴露出存在的脆弱本质。碎片的不可复原性,进一步解构了人类修复世界的幻想。"痛"从手指蔓延的过程,构建了一个精神疼痛的拓扑模型。这种蔓延不是简单的生理传递,而是存在焦虑的空间化呈现。诗人通过身体地图的绘制,使抽象情绪获得地理维度,增强了诗歌的视觉冲击力。被打扫干净的物理碎片与无法清除的精神碎片形成对照,暗示着现代社会的清洁叙事与真实记忆的冲突。诗人没有将偶然性表现为混乱或无序,而是通过精心的意象安排,使其获得美学形态。"一不小心"的破碎被赋予"很干脆""毫不犹豫"的肯定性,这种矛盾修辞使偶然性获得形式美感,实现了存在焦虑与审美体验的奇妙融合。这种美学策略展现了诗人对偶然性书写的独特贡献。
诗歌展现出独特的思想深度。诗人通过"碎杯"事件深入到存在论层面,使日常经验获得哲学重量。这种写作策略保持了诗歌的生活根基,避免了陷入琐碎的陷阱。诗歌对创伤记忆的处理方式,与西方"后记忆"理论形成有趣对话。不同于传统创伤叙事对暴力事件的直接呈现,谭延桐选择通过微小事件触发精神震荡,这种"间接创伤"书写模式,为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了新的记忆书写范式。
给倒影颁发一个棱角
谭延桐
慢慢转化成一种有棱角的力量
(神秘的,特有的,持久的)
慢慢让力量长出一副能够让空气迅速兴奋起来的
鹰一样的翅膀。慢慢,接近岩石(如果
岩石中还有岩石,那就同样接近)
不够。我是说,如果马上就停留在这样一个并不深刻的份儿上
把碎片切得碎一些,再碎一些
直到不能再碎了为止,直到无事可做了为止
再想想别的。如果
太晚了,那就真的是晚了,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如果真的是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也就
什么都不必说了。趁现在还有说的必要
把该拽过来的力量,一一地都拽过来
把已经激动起来的空气,也一块儿请过来
和它们在一起,也就
等于是,和应该在一起的在一起了
至于身上的灰尘,包括灰尘中的灰尘
可以提前抖掉。抖掉的同时,也
顺便让力量抖擞一下
最好是和空气一起抖擞。这时候,自然就会看见
自己的倒影了
或在河上,或在江上,或在海上
倒影,也肯定是有棱角的,因为这时候的它
早已转化了一种巨大的力量
【赏析】
《给倒影颁发一个棱角》:突围且突围,趣取且趣取……
《给倒影颁发一个棱角》是一首充满哲学张力与诗学创新的力作。诗人以"倒影"为切入点,通过"棱角"的赋予与力量的转化,构建了一个关于存在、责任与超越的微型宇宙,在看似轻盈的诗行中沉淀着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传统意义上的倒影是虚幻的、被动的,是现实世界的镜像复制;而谭延桐笔下的倒影却因棱角的获得而具有了主体性。这种转变实则隐喻着存在方式的觉醒。当人类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现实的投射,而是主动赋予自身以棱角,便完成了从客体到主体的根本性转变。诗歌"慢慢转化成一种有棱角的力量"这一核心命题,揭示了存在者从混沌到觉醒的蜕变过程。棱角作为力量的具象化符号,既是对现实束缚的突破,也是对存在本质的确认。
"接近岩石"的强调,构成了存在觉醒的双重隐喻。岩石象征着阻碍与挑战,接近岩石的过程是面对存在困境的过程;岩石的坚硬质地暗示着存在本身的稳固性。诗人通过"如果/岩石中还有岩石"的递进表述,揭示了存在困境的无限性。真正的觉醒不在于征服某个具体的障碍,而在于认识到障碍的永恒存在,并在与障碍的永恒对话中确认自身的存在。这种存在观与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哲学形成隐秘呼应,强调存在者必须在与限制的永恒博弈中才能获得存在的尊严。
"身上的灰尘,包括灰尘中的灰尘"将存在觉醒引入责任伦理的维度。灰尘作为存在者背负的局限与负担,其抖落过程既是自我净化的过程,也是承担责任的过程。诗人通过"和空气一起抖擞"的动作,将这种责任承担转化为一种集体性的仪式。个体与空气(作为公共领域的象征)共同抖擞,责任不再是个人的负担,而是成为存在本身的必然要求。这种伦理观在当代社会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存在的尊严不在于逃避局限,而在于主动承担局限所带来的责任。
"把碎片切得碎一些,再碎一些"揭示了诗人对存在本质的解构主义思考。在存在主义视野中,世界本就是碎片化的,人类的存在便是将这些碎片重新组合的过程。谭延桐通过切碎的动作,强调了这种解构的主动性与必要性,只有将既定的存在形态彻底打破,才能获得重新塑造的可能。这种思想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形成跨时空对话,但诗人并未止步于解构,而是通过拽过来力量和请过来空气等动作,展现了重构的积极姿态。
"如果/太晚了,那就真的是晚了"的警告,构成了诗歌的时间焦虑维度。海德格尔曾指出,存在总是向死而生的存在,时间的有限性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根本处境。谭延桐在此通过诗歌语言,将这种哲学思考转化为具体的存在焦虑。当诗人说"趁现在还有说的必要",他不仅是在强调行动的紧迫性,更是在暗示语言(作为存在确认的方式)的有限性。在时间面前,所有的言说都可能是徒劳的,但正是这种徒劳性构成了存在的尊严。"慢慢让力量长出一副能够让空气迅速兴奋起来的/鹰一样的翅膀"这一意象,将存在觉醒推向超越性的维度。鹰作为天空的统治者,其翅膀象征着对重力的突破与对自由的追求。当倒影长出鹰的翅膀,便意味着存在者不再满足于水面的平静,而是渴望翱翔于更广阔的精神天空。这是对现实局限的积极突破。
谭延桐的诗歌常常通过悖论性意象的组合,制造出强烈的艺术张力。"倒影"与"棱角"、"柔软"与"坚硬"、"虚幻"与"实在"等对立概念的并置,打破了传统意象的单一性,使诗歌具有了多层次的解读空间。"倒影,也肯定是有棱角的"将水面的虚幻与棱角的坚硬结合在一起,暗示着存在者即使在虚幻中也能获得实在的力量。这种意象处理方式,展现了诗人对存在复杂性的深刻洞察。
诗歌在语言运用上展现了卓越的音乐性。"慢慢"一词的重复使用,营造出从容不迫的节奏感,暗示着存在转变的渐进性与必然性。这种"慢"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的酝酿。正如种子破土前的漫长黑暗,存在觉醒也需要时间的积累与沉淀。"鹰一样的翅膀"与"空气迅速兴奋起来"的表述,通过元音的重复与辅音的碰撞,制造出一种向上的、激昂的音乐效果,与诗歌的主题形成完美呼应。
诗人通过一系列仪式化的动作描写,将抽象的存在思考转化为具体的诗性经验。拽过来的力量、请过来空气、抖掉灰尘等动作,具有强烈的画面感,暗示着存在转变的主动性。这些动作不是随意的身体行为,而是具有精神意义的仪式,存在者完成了从被动到主动、从混沌到觉醒的蜕变。这种动作的仪式化处理,使诗歌具有了某种宗教般的庄严感。
诗歌将日常物象转化为精神符号的炼金术。倒影作为最常见的自然现象,在诗中经历了从物理现象到精神隐喻的惊人转化。诗人通过"颁发棱角"这一非常规动作,使倒影获得了主体性,成为存在觉醒的象征。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比喻或象征,而是通过语言的魔力,使日常经验获得神性维度。"倒影,也肯定是有棱角的",这一判断使平凡的水面倒影成为存在尊严的见证。
诗歌中的空间描写具有独特的诗意逻辑。河上、江上、海上的并置,拓展了诗歌的地理维度,暗示着存在觉醒的普遍性。这些水域既是具体的物理空间,也是精神世界的象征。"自然就会看见/自己的倒影了"实际上是在暗示,存在觉醒不依赖于特定的空间条件,而是存在于任何能够映照自我的地方。这种空间处理方式,使诗歌具有了超越具体语境的普遍意义。如何在虚幻中寻找真实?谭延桐给出的答案是:通过赋予虚幻以棱角,使其成为真实的载体。当倒影因棱角的获得而具有力量时,它便不再是现实的简单复制,而是成为存在本质的显现。这种显现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现实的超越。通过棱角的折射,看到的不仅是倒影,更是存在本身的真相。这种诗学突围,使诗歌成为当代汉语诗歌中关于存在觉醒的经典文本。
是雨的疯疯癫癫吓跑了那个下午
谭延桐
叽里呱啦地,是那些雨
那些雨,说到就到
那些喜欢无事生非的雨,说了整整一个下午
从12点说到了18点,还不是整整一个下午么
整整一个下午,好端端的一个下午
就那样,被它们的疯疯癫癫吓跑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对那些雨,不可能连一点儿意见也没有
我的意见慢慢扩大,便对云
也有了意见。可是
云,却装出了一副十分无辜的样子
我真的是弄不清究竟谁是有罪的了,只知道
而且确认了再确认:那个下午
的确,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它活得一向都是非常认真的)
我之所以格外地看重那个下午,完全是因为
那个下午,与众不同
这样说,你也许就明白得更多了
那个下午,我本是可以十分宁静地
听完太阳的那场伟大的报告的
可是,雨一搀和,一切就都泡汤了
【赏析】
《是雨的疯疯癫癫吓跑了那个下午》:创新且创新,迥异且迥异……
《是雨的疯疯癫癫吓跑了那个下午》以看似轻快的叙事节奏,构建了一个关于时间、存在与语言的微型宇宙。一场突如其来的雨不仅打乱了诗人聆听太阳的伟大报告的计划,更将一个本应宁静的下午转化为充满悖论的时间场域。诗人通过雨的疯疯癫癫与云的无辜、太阳的伟大与时间的认真等对立意象的碰撞,在语言中埋藏了关于存在本质的深刻思考。这种将日常经验升华为哲学思辨的能力,正是谭延桐诗歌最显著的特质。他总能在最平凡的场景中,挖掘出超越表象的精神维度。
"那些喜欢无事生非的雨,说了整整一个下午"。这里的"说"是时间被语言化的隐喻,雨通过持续的"说话"行为,将物理时间转化为叙事时间。诗人原本期待的太阳的伟大报告象征着对时间秩序的期待,而雨的介入则打破了这种秩序,使时间从线性叙事中逸出,成为被吓跑的逃亡者。这种时间解构是通过雨的狂欢,揭示了时间本质的流动性与不可控性。
诗人对云的无辜指控与对雨的意见扩大,构成了存在困境的隐喻。云与雨作为自然现象,本无道德属性,但诗人却赋予它们人性化的特征,这暗示着人类在面对不可控力量时的认知困境。当诗人说"我真的是弄不清究竟谁是有罪的了",他实际上是在表达对存在偶然性的困惑。那个与众不同的下午的消失,并非任何个体的过错,而是存在本身的荒诞性所致。这种困惑与加缪笔下西西弗斯的困境形成跨时空呼应,都指向对存在本质的追问。
尽管那个下午再也不会回来了,但诗人通过诗歌将其固定在语言中:"它活得一向都是非常认真的"。这里的"活"字赋予时间以生命,暗示记忆对时间的重构作用。诗歌本身成为对抗时间流逝的武器,通过语言的炼金术,将消逝的瞬间转化为永恒的存在。这种记忆的救赎功能,在谭延桐其他作品中也有体现,如《书,没有腿,却走遍了全世界……》中通过绘画将知识转化为视觉记忆,二者都展现了艺术家对时间永恒性的追求。
雨的疯疯癫癫与云的无辜构成自由与束缚的隐喻。雨看似自由地"说到就到",实则受自然规律支配;云看似被动地承受雨的降临,却通过无辜的姿态逃避责任。这种悖论揭示了自由与束缚的相对性。真正的自由并非无拘无束,而是对束缚的超越性认知。诗人通过这种辩证思考,暗示人类在存在困境中的选择,是像雨一样盲目狂欢,还是像云一样逃避责任,抑或通过艺术创造实现精神的超越呢?
那个下午的消失既是偶然的(由一场雨引发),又是必然的(时间终将流逝)。诗人通过"确认了再确认"强化了这种张力。这种对偶然性的强调,与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哲学形成对话,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控制时间,而在于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精神的觉醒。"那个下午,我本是可以十分宁静地/听完太阳的那场伟大的报告的"中的"本是可以",暗示了存在选择的无限可能性,而雨的介入则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展现了存在选择的脆弱性与珍贵性。
谭延桐的诗歌语言具有卓越的音乐性。"叽里呱啦地""说到就到""整整一个下午"等叠词的运用,营造出一种轻快的节奏感,与雨的"疯疯癫癫"形成呼应。"确认了再确认"通过音节的回环往复,强化了诗人对时间流逝的无奈感。这种音乐性建构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通过语言的韵律暗示了存在本身的节奏,既有雨的狂欢,也有云的沉默,既有太阳的伟大,也有时间的认真。谭延桐的诗歌始终关注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雨的说话行为与诗人的报告形成互文,暗示语言既是存在的遮蔽,也是存在的揭示。
诗人通过诗歌语言将消逝的时间固定下来,证明了语言对存在的重构能力。谭延桐擅长通过悖论性意象的并置制造艺术张力。在这首诗中,疯疯癫癫的雨与伟大的太阳、无辜的云与有罪的雨等对立概念的碰撞,打破了传统意象的单一性。诗歌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通过诗人与雨、云的对话,构建了一个微型戏剧场景。这种叙事方式增强了诗歌的代入感,使读者能够直接感受到诗人的困惑与觉醒。"我对那些雨,不可能连一点儿意见也没有/我的意见慢慢扩大,便对云/也有了意见"的递进表述,展现了诗人情绪的戏剧性发展。
谭延桐通过诗人的主观视角,将客观时间转化为心理时间。那个"从12点说到了18点"的下午,在诗人记忆中并非均匀流逝,而是因雨的介入而变得与众不同。这种时间的主观化处理,打破了传统诗歌对时间的线性描述,展现了时间感知的个体差异性。诗人将雨、云、太阳等自然现象转化为哲学符号,通过它们的互动揭示存在困境。雨的疯疯癫癫象征存在的荒诞性,云的无辜象征对责任的逃避,太阳的伟大象征对秩序的期待。这种解读方式使诗歌具有普遍意义,每个读者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存在困境。诗歌将一个被雨打乱的下午转化为关于存在本质的思考。这种提升是通过具体意象的并置与语言的炼金术自然呈现。诗人没有直接讨论自由、责任或时间,而是通过雨的狂欢、云的沉默和太阳的缺席,让读者在感受中领悟存在真理。
我不是巫师却做了巫师的事儿
谭延桐
野草,堆积在纸上
点燃了那张纸也就等于点燃了那些野草
说做就做,请来火柴
纸,以及纸上的野草,马上就投降了
一块儿投降的还有:地上的枯枝
以及和枯枝打成了一片的败叶
我是本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糟糕的情况的
毕竟,那幅画,是我画的
虽然画得不是很好,也可以说是很失败,但,毕竟
那些野草还是可以以它们自己的方式
继续生活下去的。如果说
一定要教训,说实话,也轮不到我
风啊雨啊雷啊电啊,是最喜欢做这等事儿了
于是,后悔之余,我便开始招魂,为那些死去的野草
也为那张死去的纸
我不是巫师,却做了巫师的事儿
而事情,并没有结束,我知道事情并没有结束
我和我的画笔一起在忙活的时候,时间
却不慌不忙。我最佩服的
便是我身边的这些修炼得很好的时间了
【赏析】
《我不是巫师却做了巫师的事儿》:别致且别致,新异且新异……
《我不是巫师却做了巫师的事儿》以一场看似荒诞的燃烧仪式为起点,在野草、纸张、火柴的意象交织中,构建了一个关于存在、时间与救赎的哲学场域。诗人通过"我不是巫师却做了巫师的事儿"的自我指认,将日常行为升华为具有宗教仪式感的象征行动,在燃烧与招魂的悖论中,揭示了现代人面对存在困境时的精神挣扎。这种将平凡事物转化为精神符号的能力是谭延桐诗歌最显著的特质,他在最普通的场景中挖掘出超越表象的深层意义,使诗歌成为照亮存在幽暗角落的火把。
"野草,堆积在纸上/点燃了那张纸也就等于点燃了那些野草"。这里的"野草"既是自然物象,又是生命力的象征;"纸"既是物质载体,又是文化符号。当两者在火焰中同归于尽时,诗人揭示了存在的根本悖论,创造往往伴随着毁灭,生长必然包含着衰亡。这种悖论在"地上的枯枝/以及和枯枝打成了一片的败叶"中进一步强化,自然界的循环法则在此显现出其残酷的必然性。
"我是本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糟糕的情况的/毕竟,那幅画,是我画的"。这种矛盾揭示了现代艺术家面临的根本困境,艺术创作既是生命力的表达,又可能是对生命本身的破坏。当诗人承认"那些野草还是可以以它们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的"时,他实际上是在质疑艺术干预自然的合法性,表达了对人类行动后果的不可预知性的担忧。
面对燃烧带来的破坏,诗人选择招魂这一巫术行为作为补救措施:"于是,后悔之余,我便开始招魂,为那些死去的野草/也为那张死去的纸"。这种选择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在现代社会,当传统宗教救赎途径失效时,艺术家往往承担起精神巫师的角色,试图通过艺术创作实现灵魂的救赎。然而,诗人立即意识到这种救赎的有限性。"我不是巫师,却做了巫师的事儿",这种自我解构揭示了现代人精神救赎的困境,在信仰缺失的时代,任何救赎尝试都可能沦为徒劳的表演。这种困境在"而事情,并没有结束,我知道事情并没有结束"的重复中达到高潮。诗人清楚地认识到,存在困境无法通过一次性的救赎行动得到彻底解决,救赎永远是未完成的进行时。
诗歌中最具哲学深度的意象是时间的出场:"我和我的画笔一起在忙活的时候,时间/却不慌不忙。我最佩服的/便是我身边的这些修炼得很好的时间了"。这里的时间被拟人化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它看着人类的忙碌与挣扎,却始终保持超然的姿态。这种描写与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哲学形成对话,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控制时间,而在于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精神的觉醒。诗人对时间的佩服实际上是一种苦涩的讽刺。当人类试图通过艺术创作对抗时间流逝时,时间却以它的"不慌不忙"揭示了这种对抗的荒诞性。
诗歌通过"燃烧画作"这一行为,揭示了艺术创作中的伦理困境。艺术家在表达自我的同时,是否应该对创作对象的命运负责?当诗人承认"虽然画得不是很好,也可以说是很失败"时,他实际上是在质疑艺术评价的标准,是形式的美观更重要,还是对存在本质的揭示更重要?这种质疑在当代艺术界具有普遍意义,尤其是在观念艺术盛行的今天,艺术行动本身往往比艺术作品更具意义。诗人通过这首诗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当艺术创作成为对自然的干预甚至破坏时,艺术家是否应该承担道德责任?
在传统社会中,救赎通常通过宗教仪式实现;而在现代性语境下,当宗教信仰式微时,艺术承担起了救赎的功能。谭延桐通过招魂这一巫术行为,揭示了这种转型的悖论性。艺术确实具有治愈精神创伤的力量,如他在超验绘画中通过色彩与线条的组合创造出的心灵治愈空间;艺术救赎又具有明显的有限性,因为它无法改变存在的根本困境时间的流逝与生命的有限。这种双重性在诗歌中通过巫师意象得到完美表达:巫师在传统社会中是连接人与神的媒介,而在现代诗歌中,诗人自指为巫师,实际上是在承认艺术救赎的替代性本质。这种自我解构不是对艺术的否定,而是对艺术功能的清醒认识。艺术救赎的本质在于对精神价值的坚持,而非对现实困境的彻底消除。
谭延桐在这首诗中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存在时间诗学。与传统诗歌对时间的线性描述不同,他通过"燃烧-招魂-时间旁观"的叙事结构,将时间呈现为一个循环往复的圆环,燃烧带来毁灭,招魂象征救赎,而时间则见证这一切的徒劳与必然。这种时间观与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形成呼应,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改变时间的进程,而在于在时间中坚持精神的觉醒。诗人佩服时间实际上是在表达对存在本质的接受,既然时间无法被征服,那么真正的智慧就在于认识到时间的不可征服性,并在这种认识中获得自由。因为时间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它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一切。
谭延桐擅长的艺术策略是将日常事物转化为精神符号。在这首诗中,野草、纸、火柴、枯枝、败叶等普通物象,通过诗人的处理,获得了丰富的象征意义。野草象征生命力,纸象征文化,火柴象征瞬间爆发力,枯枝败叶象征衰亡。这些意象的组合,构成了一个关于存在循环的微型宇宙。诗歌在叙事与抒情之间保持着精妙的平衡。表面上看是在叙述一个燃烧画作-招魂的简单故事;但实际上,每个叙事环节都蕴含着强烈的抒情性。"点燃了那张纸也就等于点燃了那些野草"既是客观描述,又是情感爆发;"时间/却不慌不忙"既是事实陈述,又是哲学沉思。这种叙事抒情化的手法,使诗歌既具有故事的吸引力,又具有思想的深度。
诗歌语言具有卓越的音乐性。"野草,堆积在纸上/点燃了那张纸也就等于点燃了那些野草"通过重复与回环,营造出一种吟唱般的节奏;"地上的枯枝/以及和枯枝打成了一片的败叶"通过头韵的运用,增强了语言的韵律感;"时间却不慌不忙"通过短句的重复,强化了时间的从容态度。这种音乐性建构不仅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更通过语言的韵律暗示了存在本身的节奏,既有燃烧的激烈,又有招魂的沉静,既有时间的从容,又有存在的紧迫。"野草,堆积在纸上"构建了一个充满质感的画面;"点燃了那张纸也就等于点燃了那些野草"通过动词的重复使用,使火焰的蔓延过程可视化;"地上的枯枝/以及和枯枝打成了一片的败叶"通过拟人化手法,使自然物的反应具有戏剧性。这种视觉化描写使读者仿佛亲眼目睹了这场燃烧仪式。
招魂这一巫术行为的引入,为诗歌增添了浓厚的象征色彩。在传统文化中,招魂是连接生死、沟通阴阳的仪式;在这首诗中,招魂则成为艺术家试图弥补创作过失的精神行动。这种象征的运用,使诗歌超越了具体事件,成为关于艺术伦理与存在救赎的普遍寓言。时间在诗歌结尾的出场,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诗人通过将时间拟人化为"修炼得很好的"存在者,赋予时间以主体性,使其成为存在困境的见证者与评判者。这种处理方式,将时间从背景提升为前景,使诗歌的主题从具体事件升华为哲学思考。
结语
谭延桐这组诗以其别致的意象群与忘我的参悟,呈现了一处处幽境。如此幽境,就犹如陶渊明的“桃花源”。也如一柄锐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现代人的一些内在痼疾,因此而展现了他的铁肩与热肠。他以诗为舟,不仅引领读者穿越存在的重重迷雾,更在每一次航行中,让读者窥见神秘之光。这组诗歌,既是对个体生命的深刻剖析,也是对整个人类存在状态的反观与审视。在这里,读者不难发现谭延桐对艺术的至诚坚守,对哲学的热切拥抱,以及对“人类的天线”的不断打磨。他的诗歌,就如同夜空中最亮的灯塔,不仅照亮了现代人的灵魂航道,更在无尽的幽暗中指引着人们去寻找某物或某境。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必将愈发显现出其不可替代的魅力。谭延桐的艺术世界,是一个醒目的象征,这,不容置疑。从如此的一个象征里,要找到已经隐身的优雅与美好等,是不难的。难的是,如何校对我们的审美。
【诗评作者介绍】
史传统,资深媒体人、知名评论家;《香港文艺》编委、签约作家,香港文学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香港书画院特聘艺术家;中国国际教育学院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国际新闻杂志社评论专家委员会执行主席。学术专著《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散见《特区文学》《香港文艺》《芒种》《青年文学家》《中文学刊》《中国诗人》《民族文汇》《河南文学》等。先后发表诗歌、散文、文艺评论2000多篇(首),累计500多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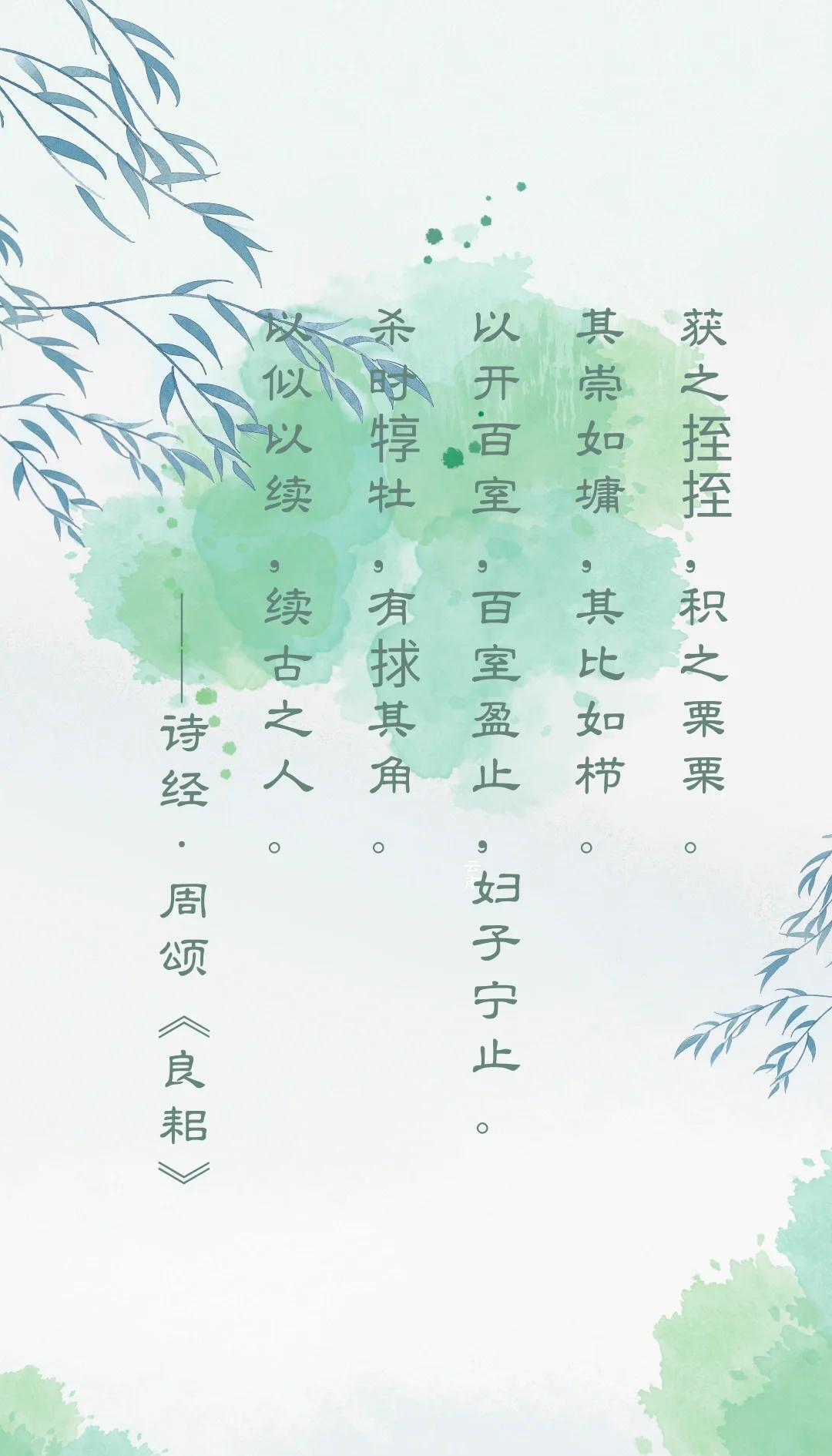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