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在桌面上震动,嗡鸣声持续不断。
屏幕的光在昏暗的房间里明明灭灭。
同一个号码。
第43个,第44个,第45个。
我盯着那个有点熟悉的尾号,手指悬在红色的拒接键上方。
一年前的画面碎片般闪过——小女孩苍白的脸,主管冰冷的声音,银行卡里被扣掉的数字。
震动停止了。
几秒后,再次疯狂响起。
第46个。
窗外的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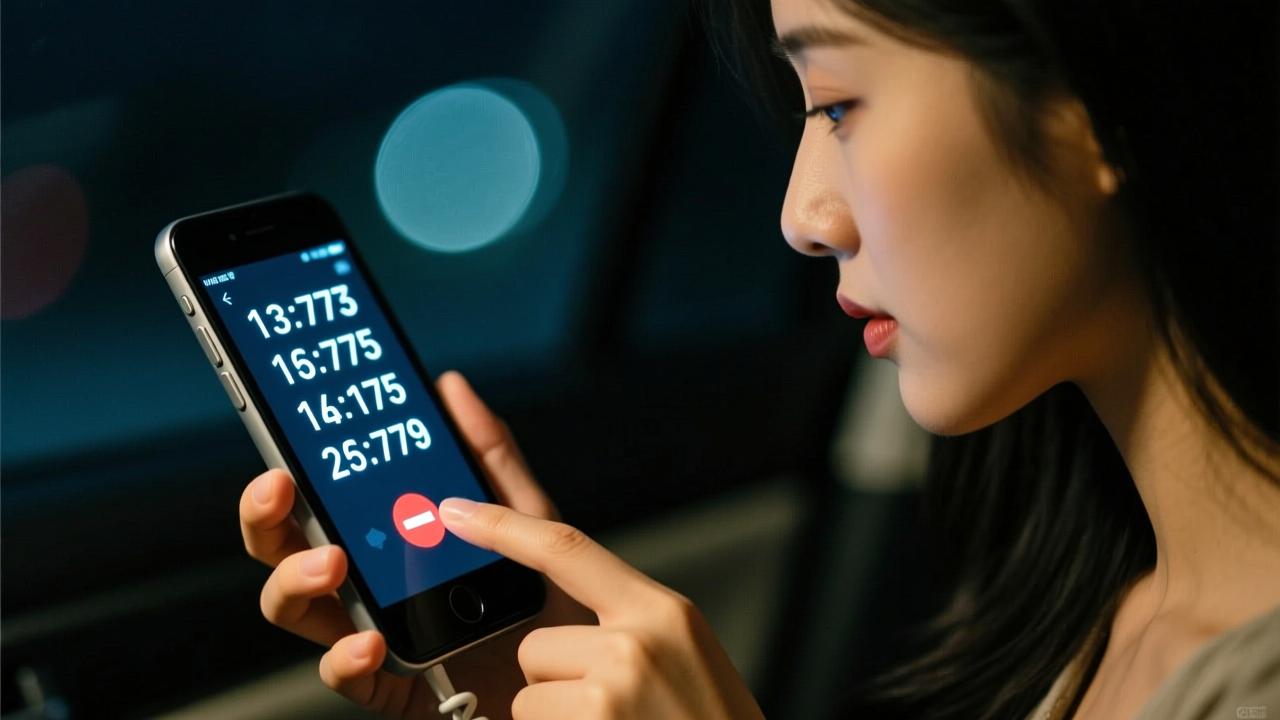
01
会议室里的空调开得太足。
冷风从头顶的出风口钻下来,我搓了搓冰凉的手指。
投影仪的光打在曾永贵脸上,将他的轮廓切割得更加冷硬。
“这个数据怎么回事?”
他用激光笔圈住报表上的某个数字,红色的光点像靶心。
“上周汇报时还是七十八万,今天就成了八十二万。”
他的目光转向我。
“彭欣悦,你解释一下。”
全会议室的人都看过来。
我翻开笔记本,找到上周的记录。
“曾总,上周说的是预计七十八万,这周统计的实际回款是八十二万。”
我尽量让声音平稳。
“实际比预期高了四万,我在邮件里标注过。”
曾永贵翻动面前的打印件。
纸张发出哗啦的声响。
“邮件?”
他抬眼看我,眼神里没什么温度。
“我每天收上百封邮件,难道每封都要仔细看?”
旁边有人低下头。
“下次有重要变动,直接当面汇报。”
他的激光笔移向下一个图表。
“不要指望别人替你记住细节。”
会议继续。
我合上笔记本,指甲在硬壳封面上压出浅浅的月牙。
季度冲刺,连续加班三周了。
今天原本该轮到我调休。
昨天提交申请时,曾永贵扫了一眼就放下了。
“等这个项目收尾再说。”
他说这话时头也没抬。
现在项目收尾了。
我趁着汇报结束的空档,又提了一次。
“曾总,今天我想申请调休。”
曾永贵正在收拾文件。
“调休?”
他动作没停。
“下周总部要来人审计,所有数据都要再核对一遍。”
他拎起公文包。
“等项目奖金发下来,再休也不迟。”
他走出会议室。
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
我站在原地,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空调还在吹,冷风钻进衣领。
同事拍了拍我的肩。
“算了,欣悦。”
她压低声音。
“他就是这个脾气。”
我点点头,没说话。
回到工位,电脑屏幕亮着。
邮箱里又多了几封待处理的邮件。
我坐下,点开第一封。
手指敲击键盘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区里格外清晰。
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
高楼大厦的灯火一盏盏亮起。
我看了眼手机。
晚上七点二十三分。
调休申请在系统里还是“待审批”状态。
我关掉页面,打开新的表格。
数字在眼前跳跃,渐渐模糊成一片。
02
加完班已经快十点了。
整层楼只剩下我这一角的灯还亮着。
我保存文件,关掉电脑。
肩膀酸得发硬。
收拾东西时,水杯不小心碰倒了。
半杯凉水洒在键盘上。
我手忙脚乱地抽出纸巾擦拭。
水渗进按键缝隙,擦不干净。
心里那点烦躁终于压不住了。
我拿着水杯去茶水间冲洗。
走廊的灯是声控的,脚步声一停就灭了。
我踩了跺脚。
灯重新亮起,惨白的光。
经过楼梯间时,我隐约听见说话声。
门虚掩着,漏出一线光。
是曾永贵的声音。
和平时的严厉不同,这声音压得很低,带着某种急促的疲态。
“……我知道。”
“血库那边还没消息吗?”
“多少钱都行,你们再问问其他医院。”
我停下脚步。
不是故意要听,只是这声音太陌生了。
“……娅楠今天疼得厉害吗?”
他的语气突然软下来。
软得几乎不像他。
“你先别哭。”
“我这边处理完就过去。”
“药按时吃了吗?”
沉默了几秒。
“好,我尽量十二点前到。”
“你先睡,不用等我。”
电话挂断了。
接着是长久的安静。
我透过门缝看见一点影子。
曾永贵靠在墙上,低着头。
灯光从他头顶打下来,在脸上投出深深的阴影。
他抬手揉了揉眉心。
那个动作很慢,很重。
然后他站直身体,整理了一下领带。
又是那个一丝不苟的曾主管了。
他推开楼梯间的门走出来。
看见我时,他愣了一下。
眼神在瞬间变得警惕。
“还没走?”
他恢复公事公办的语气。
“马上走。”
我举了举手里的水杯。
“曾总也刚下班?”
他没回答这个问题。
“明天上午九点,项目复盘会别迟到。”
他迈步走向电梯,脚步很快。
我站在原地,听见电梯下行的叮咚声。
娅楠。
医院。
血库。
这几个词在脑子里打转。
我摇摇头,把这些晃出去。
别人的家事,和我无关。
回到工位,键盘还在滴水。
我用吹风机吹了十分钟,勉强能用了。
关灯离开时,整层楼彻底暗下来。
电梯镜子里的自己,眼圈发青。

03
周末上午,我去医院拿体检报告。
人很多,排队的长龙弯弯曲曲。
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
我靠在墙边等叫号,低头翻着手机。
“让一让!让一让!”
急促的喊声从门口传来。
我抬起头。
曾永贵抱着一个女孩冲进来。
他穿着休闲服,头发凌乱,和我平时见到的样子判若两人。
怀里的女孩约莫八九岁,小脸苍白,眼睛紧闭。
“医生!医生在哪里?”
他的声音在发抖。
护士推着移动床跑过来。
他小心翼翼地把女孩放上去,手一直护着她的头。
“娅楠,坚持住。”
他说得很轻,像在哄孩子。
女孩的袖子滑上去一截。
我看见了。
细瘦的手腕上,密密麻麻的针孔。
青紫色的淤痕新旧交错。
护士推着床往急诊室跑,曾永贵紧跟在旁边。
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
我站在原地,手里的报告单被捏出了褶皱。
叫号机叫到了我的号码。
我走过去,窗口里的护士递出报告。
“一切正常。”
她例行公事地说。
我接过报告,转身离开。
走到门口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
急诊室的红灯亮着。
长椅上,曾永贵弓着背坐着,双手撑在膝盖上。
他盯着地面,一动不动。
外面的阳光很好,透过玻璃门照进来。
光斑落在他脚边,他却整个人陷在阴影里。
我推门出去。
热浪扑面而来。
走到公交站时,手机震了一下。
是工作群里曾永贵发的消息。
“下周一例会提前到八点半,所有人不得迟到。”
后面跟着三个感叹号。
我关上手机。
公交车来了,我挤上去。
车厢里很闷,混合着汗味和香水味。
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
那个苍白的女孩。
那些针孔。
曾永贵发抖的声音。
画面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到站下车,热风卷着尘土吹过来。
我低头走路,鞋尖踢到一颗石子。
石子滚进路边的排水沟,发出轻微的声响。
04
公司组织年度公益活动。
地点在市中心的献血站。
“自愿参加,但不参加的同事需要提交说明。”
行政部在群里发了通知。
曾永贵在下面补充了一句。
“党员和积极分子带头。”
后面附了参加人员的名单。
我的名字在中间。
献血站里排着队。
空调开得很足,但还是能闻到淡淡的消毒水味。
轮到我时,护士示意我坐下。
“最近有没有吃药?”
“有没有熬夜?”
例行的问题。
我一一回答。
针扎进血管时,我别过头去。
血顺着管子流进血袋。
护士看着仪器上的数据,忽然抬头多看了我一眼。
“你以前献过血吗?”
“大学时献过一次。”
“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有。”
她点点头,在表格上写了些什么。
抽完血,我按着棉签坐在休息区。
旁边有同事递过来一杯糖水。
“谢谢。”
我小口喝着。
甜得发腻。
曾永贵也来了。
他挽起袖子坐下,动作干脆利落。
护士给他扎针时,他眉头都没皱一下。
血袋慢慢鼓起来。
他的目光落在血袋上,不知道在想什么。
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屏幕,立刻接起来。
“喂?”
“情况怎么样?”
“我这边快了,半小时后到。”
声音压得很低。
挂掉电话后,他看向护士。
“能快一点吗?”
护士摇头。
“规定的时间,不能快。”
他抿紧嘴唇,不再说话。
结束后,他按着棉签站起来,脚步匆匆地离开。
连公司准备的营养品都没拿。
我休息了二十分钟,感觉好些了。
走出献血站时,手机响了。
是许英逸。
我的学长,现在在市医院血液科。
“欣悦,你在哪儿?”
“刚献完血,怎么了?”
“哪个献血站?”
“中心站。”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你的血型,是Rh阴性吧?”
我愣了愣。
“你怎么知道?”
“献血站那边有记录,系统里跳了提示。”
他的语气严肃起来。
“这种血型很少见,千分之三的概率。”
“我们医院刚好缺这种血,所以系统会特别标注。”
我走到树荫下。
“这血型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大问题,就是稀有。”
他停顿片刻。
“你以后多注意点,尽量避免受伤出血。”
“如果需要输血,这种血不太好找。”
风吹过来,树叶沙沙响。
“知道了,谢谢学长。”
“客气什么。”
他笑了笑。
“对了,你最近怎么样?好久没见了。”
“老样子,加班加班加班。”
“注意身体,别太拼。”
“好。”
挂掉电话,我抬头看了看天。
云层很厚,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
Rh阴性血。
熊猫血。
这个词以前只在新闻里见过。
我摸了摸刚才扎针的地方。
纱布下面,隐隐约约还有点疼。

05
凌晨两点,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
我迷迷糊糊地摸过来。
屏幕的光刺得眼睛疼。
许英逸的号码。
“欣悦,睡了吗?”
他的声音很急,背景音里传来医疗仪器的滴滴声。
“刚醒,怎么了?”
“你现在能不能来一趟医院?”
我坐起来,开了台灯。
“出什么事了?”
“有个小女孩,急性溶血,需要紧急输血。”
“血型是Rh阴性,血库告急。”
“全市都在调血,但时间来不及了。”
他的语速很快。
“我记得你上次献血就是这种血型。”
“你能不能……”
“在哪家医院?”
“市一院,急诊三楼血液科。”
“我马上到。”
我掀开被子下床。
换衣服时,手有点抖。
扣子扣错了两次。
出门打车,深夜的街道空旷。
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
“这么晚去医院,家里有人生病?”
“嗯。”
我不想多说话。
车窗外的路灯飞快后退,连成一道道光带。
到医院时,许英逸已经在门口等我了。
他穿着白大褂,神色凝重。
“跟我来。”
他带着我往电梯走。
“孩子情况很危险吗?”
“非常危险。”
他按下三楼按钮。
“才九岁,之前就有病史,这次突然恶化。”
“血压一直在掉。”
电梯门开了。
走廊里灯火通明。
护士推着仪器车跑过,轮子摩擦地面发出急促的声响。
许英逸推开一扇门。
“就在这里。”
病床上躺着一个小女孩。
脸色苍白得像纸,呼吸罩遮住了大半张脸。
但我认出来了。
是曾永贵的女儿。
她闭着眼睛,睫毛在眼下投出淡淡的阴影。
手腕上连着输液管,仪器屏幕上跳动着数字。
曾永贵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他握着女儿的另一只手,握得很紧。
他的背驼着,头发乱糟糟的。
听见声音,他抬起头。
看见我时,他眼里闪过一丝惊讶。
然后是困惑。
“彭欣悦?”
他站起来。
“你怎么……”
许英逸开口解释。
“曾先生,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最近的同血型献血者。”
“你的同事,彭欣悦。”
曾永贵的表情僵住了。
他的目光在我和许英逸之间移动。
“你们认识?”
“她是我学妹。”
许英逸简单地说。
“现在没时间说这些了。”
“欣悦,我们需要尽快采血。”
护士推着采血设备进来。
我卷起袖子。
针扎进血管时,我看向病床。
女孩的胸口微微起伏,很微弱。
曾永贵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
他的目光落在血袋上,又移开。
看向女儿,又看向我。
嘴唇动了动,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采了400毫升。
护士小心地封好血袋,快步送去处理。
我按着棉签坐下。
有点头晕。
许英逸递给我一杯葡萄糖水。
“慢慢喝。”
我小口啜饮着。
曾永贵走过来。
“你……”
他停顿了一下。
声音很低,很干涩。
“没事。”
我说。
他点点头,转身回到女儿床边。
继续握着她的手。
许英逸低声跟我说。
“你先在这里休息半小时。”
“等会儿我送你回去。”
“不用,我自己打车就行。”
“听我的。”
他语气不容置疑。
我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消毒水的味道。
仪器的滴滴声。
还有曾永贵低低的,哄孩子一样的声音。
“娅楠,不怕。”
“爸爸在这里。”
06
第二天我请了假。
许英逸说献血后最好休息一天。
我给曾永贵发了短信。
“曾总,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请假一天。”
他没回复。
我睡到中午才醒。
头还是有点晕,但比昨晚好多了。
煮了碗粥,慢慢喝完。
下午坐在阳台上看书。
阳光很好,晒得人懒洋洋的。
但我看不进去。
书页上的字在跳动。
脑子里反复出现昨晚的画面。
苍白的女孩。
闪烁的仪器。
还有曾永贵说“谢谢”时的表情。
那么陌生,那么疲惫。
我摇摇头,合上书。
第三天早上,我准时到公司。
刚在工位坐下,内线电话就响了。
“彭欣悦,来我办公室一趟。”
曾永贵的声音。
听不出情绪。
我起身走过去。
门虚掩着,我敲了敲。
“进。”
他坐在办公桌后,正在看一份文件。
我站在桌前。
“曾总,您找我?”
他放下文件,抬头看我。
“昨天为什么没来上班?”
我愣了一下。
“我给您发过请假短信。”
“我收到了。”
他双手交叠放在桌上。
“但你的请假理由不充分。”
“公司规定,病假需要提供医院证明。”
“你没有提交任何证明。”
办公室里很安静。
空调发出细微的嗡嗡声。
“我当时确实不太舒服。”
“献血之后需要休息。”
“献血?”
他重复这两个字,语气平淡。
“那是你的个人行为,与工作无关。”
“公司制度里没有‘献血假’这一条。”
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
“这是考勤记录。”
“你昨天无故缺勤,按规定扣发当月全额奖金。”
他把纸推到我面前。
白纸黑字。
我的名字后面,标注着红色的“缺勤”。
奖金栏那里,是一个醒目的“0”。
“这个月的项目奖金是八千块。”
“全部扣除。”
他说得很平静。
像在陈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事实。
我盯着那张纸。
纸上的字在晃动。
“曾总。”
我的声音有点干。
“我献血,是为了救你的女儿。”
曾永贵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那是两回事。”
他靠回椅背。
“工作归工作,私人归私人。”
“我很感谢你帮助娅楠。”
“但公司的制度,不能因为私人感情就破坏。”
他说“感谢”两个字时,语气和说其他话没什么区别。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个人给你一些经济补偿。”
“不用。”
“那好。”
他点点头。
“还有其他事吗?”
我看着他。
看着他整齐的领带,一丝不苟的头发,平静无波的眼睛。
昨晚那个握着女儿的手,声音发抖的男人不见了。
坐在这里的,是曾主管。
我的上司。
“没有其他事了。”
“出去时带上门。”
我拿起那张考勤记录。
纸张很轻,但握在手里沉甸甸的。
走到门口,我停下来。
他抬眼。
“你女儿……好些了吗?”
他沉默了两秒。
“好多了。”
“那就好。”
我拉开门,走出去。
门在身后轻轻关上。
走廊里,有同事抱着文件经过。
“欣悦,早啊。”
她笑着打招呼。
“早。”
回到工位,我坐下。
电脑屏幕亮着,待办事项列表长得看不到头。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然后打开文档,开始写辞职报告。

07
辞职报告交上去的时候,曾永贵正在开会。
我放在他办公桌上,用镇纸压好。
下午他回来,内线电话打到我这里。
“来一下。”
我走进去。
辞职报告已经打开了,摊在桌上。
“你想好了?”
他问。
“想好了。”
“因为这个月奖金的事?”
“不全是。”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丝探究。
但只有一丝。
“找到下家了?”
“还没有。”
“那为什么急着走?”
我沉默了一会儿。
“累了。”
这个答案似乎在他意料之外。
他靠在椅子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这个项目做完,本来可以给你升一级。”
“现在走,有点可惜。”
“不可惜。”
他又看了我几秒。
“好吧。”
他拉开抽屉,拿出印章。
在辞职报告上盖了章。
“去人事部办手续吧。”
“今天就可以走。”
“谢谢曾总。”
我转身要走。
“彭欣悦。”
他叫住我。
我回头。
他从钱包里抽出一张卡。
“这里面有两万块。”
“算是我个人对你的感谢。”
“拿着吧。”
他把卡放在桌上。
“你救了娅楠的命。”
“这是你应该得的。”
我看着那张卡。
银色的卡片,在灯光下反着光。
“我献血,不是为了钱。”
“我知道。”
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些。
“但这是我的心意。”
“就当是给孩子的救命恩人一点谢礼。”
我还是摇头。
“真的不用。”
他不再坚持。
把卡收回去,重新放回钱包。
“那好吧。”
“祝你以后发展顺利。”
我走出办公室。
人事部的手续办得很快。
交接清单,物品归还,离职证明。
最后去财务部结算工资。
会计是个中年女人,戴着老花镜。
她看着电脑屏幕,噼里啪啦地敲键盘。
“你这个月工资是六千四。”
“奖金呢?”
“奖金扣除了,曾总特别交代的。”
她推了推眼镜。
“还有其他疑问吗?”
“在这里签字。”
我签了字。
她数出六千四百块钱,递给我。
“点一下。”
我接过来,没点,直接装进包里。
回到工位收拾东西。
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
几本书,一个水杯,一盆小小的绿萝。
同事围过来。
“真的要走啊?”
“太突然了。”
“是不是找到更好的地方了?”
我笑了笑,没多解释。
收拾到抽屉最底层时,我摸到一个硬硬的东西。
拿出来一看,是一张折起来的画。
彩笔画,画纸有点皱。
上面画了三个人。
一个高大的男人,牵着一个小女孩。
旁边还有一个女人,穿着裙子。
画的下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
“爸爸,娅楠,和好心的姐姐。”
是贾娅楠的画。
可能是上次曾永贵带她来公司时落下的。
我拿着画,看了很久。
然后折好,放回抽屉里。
抱起纸箱,和同事们道别。
电梯下行时,我靠在轿厢壁上。
看着数字一层层跳。
从18到1。
叮咚。
门开了。
我走出大楼。
阳光刺眼。
我眯起眼睛,抬头看了看。
曾永贵的办公室在十八楼。
窗户反着光,什么也看不见。
我抱着纸箱,走进人流里。
08
我回了老家。
高铁三小时,再转大巴一小时。
到家时已是傍晚。
养母何玉芝在院子里摘豆角。
看见我,她愣了一下。
“怎么突然回来了?”
“想你了。”
我把行李放下。
她走过来,摸了摸我的脸。
“瘦了。”
“工作太累,辞职了。”
“辞了好。”
她接过我的包。
“那种地方,不干也罢。”
“先吃饭,我给你炖了鸡汤。”
晚饭很简单。
鸡汤,炒青菜,还有一碟咸菜。
我们坐在院子里吃。
晚风轻轻吹,带着田野的味道。
“这次回来住多久?”
“住一阵子吧。”
“好好休息。”
她给我盛汤。
“你从小就爱逞强,什么事都往心里去。”
“现在好了,回家来,慢慢想。”
我喝着汤,没说话。
晚上我睡在以前的房间。
墙上的奖状还在,只是颜色已经褪了。
书架上摆着旧课本,蒙了一层灰。
我睡不着,起来整理东西。
从行李箱里翻出一个铁盒子。
里面装着小时候的宝贝。
玻璃弹珠,彩色发卡,几封信。
还有一个褪色的襁褓。
很小的一块布,浅蓝色,绣着简单的花纹。
我拿出来,放在手里看。
布已经很薄了,边缘有脱线的痕迹。
这是我被收养时,身上包着的东西。
养母说,当年在福利院门口发现我时,我就裹着这个襁褓。
里面还有一张字条。
字条呢?
我在盒子里翻找。
找到了。
折成小小的一块,纸已经发黄。
我小心地展开。
上面的字是用钢笔写的,墨水洇开了些。
“请好心人收养这个孩子。”
“她生于三月十七日,早上七点。”
“母亲姓林,父亲姓曾。”
“实在无力抚养,万望善待。”
“来世做牛做马,报答恩情。”
我的手停在半空。
父亲姓曾。
曾。
这个字在纸上模糊,但清晰可见。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纸上。
字迹在月光下显得更旧了。
我盯着那个“曾”字。
看了很久。
脑子里一片空白。
然后许多画面涌进来。
曾永贵的脸。
他训斥我的样子。
他说“谢谢”时的表情。
他扣奖金时的平静。
还有贾娅楠。
苍白的脸。
手腕上的针孔。
画上的“爸爸,娅楠,和好心的姐姐”。
我放下字条。
走到窗边。
夜很深了,村子里没什么灯火。
远处有狗叫了几声,又安静下来。
我靠在墙上,慢慢滑坐在地上。
地板很凉。
月光移过来,照在我的脚边。
襁褓还摊在床上,浅蓝色的,旧旧的。
我想起养母说过的话。
“你命苦,但也是幸运的。”
“亲生父母不要你,但总有人要你。”
“我把你当亲生的养,一样疼。”
她确实做到了。
供我读书,送我上大学。
自己省吃俭用,却从不让我受委屈。
现在她老了,背也驼了。
我该陪在她身边。
可是。
这只是巧合吗?
全国姓曾的人那么多。
可是Rh阴性血呢?
千分之三的概率。
我拿起手机,想查点什么。
但又放下了。
查什么呢?
查曾永贵的家庭?
查他妻子的名字?
查贾娅楠的出生记录?
我闭上眼睛。
头开始疼。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
养母轻轻推开门。
“还没睡?”
她看见我坐在地上。
“怎么了?不舒服?”
我站起来。
“就整理东西。”
她的目光落在床上的襁褓和字条上。
沉默了一会儿。
“你看到了。”
“本来想等你再大些告诉你。”
她走进来,坐在床边。
拿起那个襁褓,轻轻抚摸着。
“这些年,我也打听过。”
“但没什么消息。”
“姓林的姑娘,姓曾的男人。”
“人海茫茫,哪里找得到。”
她抬头看我。
“你是不是想找他们?”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找到又怎么样呢?”
她的声音很轻。
“当年他们把你扔了,就是不要你了。”
“现在去认,图什么?”
“图他们给你留点遗产?”
“还是图他们给你道个歉?”
我摇头。
“我不是图那些。”
“那图什么?”
我答不上来。
也许是图一个答案。
图一个为什么。
图一个“我到底是谁”。
但也许,这些都不重要了。
“睡吧。”
养母站起来。
“别想太多。”
“你就是我的女儿,这辈子都是。”
她走出去,轻轻带上门。
我躺回床上。
手里还捏着那张字条。
纸很脆,我怕捏碎了,又松开。
月光移到枕边。
母亲姓林。
贾娅楠九岁。
我二十七岁。
如果。
无数的“如果”在脑子里盘旋。
最后都沉入黑暗。

09
在老家住了大半年。
我在县城找了一份文员的工作。
工资不高,但清闲。
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二十分钟路程。
养母的身体时好时坏。
我带她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没什么大病,就是老了。
开了些调理的药。
日子过得很平静。
像一潭水,不起波澜。
偶尔会想起以前的公司。
想起加班的日子,想起会议室里的冷气。
想起曾永贵训人时的表情。
但那些都远了,像上辈子的事。
直到那天下午。
我正在整理文件,手机响了。
我们有段时间没联系了。
上次联系还是我辞职时,他打电话来问情况。
他的声音很急。
和一年前那个凌晨很像。
“在县城,怎么了?”
“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方便。”
我走到走廊上。
“你还记得贾娅楠吗?”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记得。”
“她病情复发了。”
“这次更严重。”
许英逸的语速很快。
“需要大量输血,还是Rh阴性血。”
“血库又告急了。”
“我们联系了上次的献血者,就是你。”
“但你的电话打不通。”
“我换号码了。”
“怪不得。”
“曾永贵在到处找你。”
“他找到医院来了,问我们有没有你的联系方式。”
“我们当然没有。”
“他现在快疯了。”
走廊里有风吹过。
我握紧手机。
“孩子现在怎么样?”
“很不好。”
许英逸的声音低下来。
“这次是急性的,血小板掉得厉害。”
“已经昏迷两天了。”
“如果再输不上血,可能……”
他没说完。
但意思很明白。
“医院没有其他办法吗?”
“全市都在调血,但你知道,这种血型太少了。”
“上次你献血后,我们储备了一些。”
“但这次用量太大,已经用完了。”
“现在只能等。”
“等新的献血者,或者……”
他停住了。
“或者什么?”
“或者找到你。”
他说。
“你是我们目前知道的,最近的同血型者。”
“曾永贵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发了疯一样在找你。”
“他找到你了吗?”
“但他去你以前的公司,挨个问你的同事。”
“有人给了他一个号码,说是你朋友的。”
“他打过去,那个人说你回老家了。”
“具体哪里,不知道。”
“他现在准备去你老家找。”
“但他连你在哪个县都不知道。”
许英逸叹了口气。
“欣悦,我知道他以前对你不好。”
“扣奖金的事,我听说了。”
“但孩子是无辜的。”
“她才十岁。”
我没说话。
看着窗外的街道。
行人来来往往,电动车按着喇叭驶过。
“学长。”
“我需要想一想。”
许英逸沉默了。
“你想好了,给我打电话。”
“但请快一点。”
“时间不多了。”
挂掉电话后,我站在原地很久。
直到同事推门出来。
“欣悦,主任找你。”
“来了。”
我收起手机,回到办公室。
主任让我送一份文件去隔壁部门。
我拿着文件下楼。
走在楼梯上时,手机又震了一下。
是一条短信。
陌生的号码。
“彭欣悦,我是曾永贵。”
“求求你,接电话。”
“娅楠需要你。”
“求你了。”
短信的最后,是一连串的感叹号。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