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过那种工地上,五十多岁还打着光棍的师傅吗?刘建国就是。
他和王秀芬,一个砌墙,一个提灰,在同一个工棚里搭伙过了十三年。没人拿结婚证,就是累了有个说话的人,病了有口热水喝。这在他们那圈子里,不稀奇,叫“搭伙夫妻”。日子像工地的混凝土,粗糙,但能互相撑着不倒。
那时候谁也没多想,就觉得王秀芬这大姐,人挺讲究。工棚再乱,她那块地方总是干干净净;天没亮就起来,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大伙儿背地里笑她穷讲究,刘建国却觉得挺好,还帮她打水,让她能天天擦把脸。他图啥?可能就是图下班回来,有个人在灯下等着,桌上摆着热乎的咸菜馒头。这就够了。
直到王秀芬倒下。医院说是心脏病,后来才知道,要命的是胃癌,晚期。最后那几天,她话都说不出了,就死死攥着个旧布包,眼睛看着刘建国。他懂,那是留给他的。
人走了以后,刘建国在空荡荡的工棚里打开了布包。里面不是他以为的几件旧衣服,而是一封信,一张银行卡,还有一份他看不太懂的文件。
信上的字,娟秀得不像出自一个提灰桶的女人的手。
“建国,对不起,骗了你十三年。我不叫王秀芬,我叫林婉清。”
信很长,刘建国蹲在床边,借着昏暗的灯光,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他这才知道,这个和他一起吃糠咽菜的女人,曾经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风光无限的时候,被最信任的丈夫和亲生儿子联手做局,卷走了所有钱,把巨额债务和烂摊子全留给了她。公司破产,众叛亲离,债主堵门。她从高楼一跃而下想解脱,却没死成。心死了,就用另一种方式活——扔掉名牌衣服,抹黑脸,混进了南下的民工潮,成了最不起眼的“王秀芬”。
信里写:“来工地的头一年,我每天都想死。直到遇见你。你给我打的那盆热水,是我三年来感受到的第一丝暖。你不问我过去,不嫌我古怪,就是实心实意地对一个人好。这十三年,是我偷来的。我用‘王秀芬’这个身份,尝到了这辈子最干净的感情。”
她说,胃癌是早就查出来的,没治。那笔积蓄和那份股权文件,是她最后能给他的东西。文件涉及她早年以别人名义做的一点投资,如今公司起来了,值些钱。她写道:“钱不多,但够你离开工地,安稳过完后半生。别拒绝,这是我欠你的,也是我……爱过你的证明。”

刘建国捏着信纸,手抖得厉害。他想起她总在深夜捂着胃,说老毛病;想起她吃得极少,说在减肥;想起她看他时,眼里那种复杂的、他读不懂的光。原来那不是工友间的依赖,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在绝望里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根稻草,给了他毫无保留的温暖。
工棚外,打桩机还在轰隆隆地响。但刘建国的世界,彻底静了。他坐了整整一夜,抽光了半包最便宜的烟。
第二天,他去工头那儿结了账,辞了工。收拾行李时,他把王秀芬——不,林婉清——那几件洗得发白的旧工服,仔细叠好,放进了最底层。他买了一张去往林婉清家乡的车票,地址是她信里提到的,一个她从未带他回去过的江南小镇。
他不知道那小镇什么样,也不知道股权什么的该怎么弄。这个在钢筋水泥里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的男人,第一次感到一种茫然的沉重。但那沉重里,又生出一点陌生的力量。
他不是去追索什么,也不是去享受那份遗产。他就是觉得,得去她来的地方看看。得知道,那个叫林婉清的女人,前半生是在怎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好像只有这样,他才能把“王秀芬”和“林婉清”这两个名字,在心里完整地拼成一个人。
火车开动的时候,他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工地景象。那里埋葬了他作为建筑工人的大半生,也埋葬了一个女人隐藏了十三年的惊世秘密,和一份至死才敢言明的深情。
未来会怎样?他不知道。但他手里紧紧握着的,不再只是磨出老茧的拳头,还有一张银行卡,一份文件,和一封被泪水浸得字迹模糊的信。
这大概就是生活最吊诡的地方:你以为是两个苦命人在抱团取暖,却不知其中一人,曾见识过山顶的风景,也跌落过最深的谷底。而她最后找到的温暖,恰恰来自谷底另一块冰冷的石头。
这份迟来的真相,对刘建国来说,不是解脱,更像是一份需要用余生去慢慢拆开的、沉重的礼物。而礼物最深处藏着的,是一个女人在生命尽头,所能给出的全部真心与歉意。这就够了,真的。比多少钱都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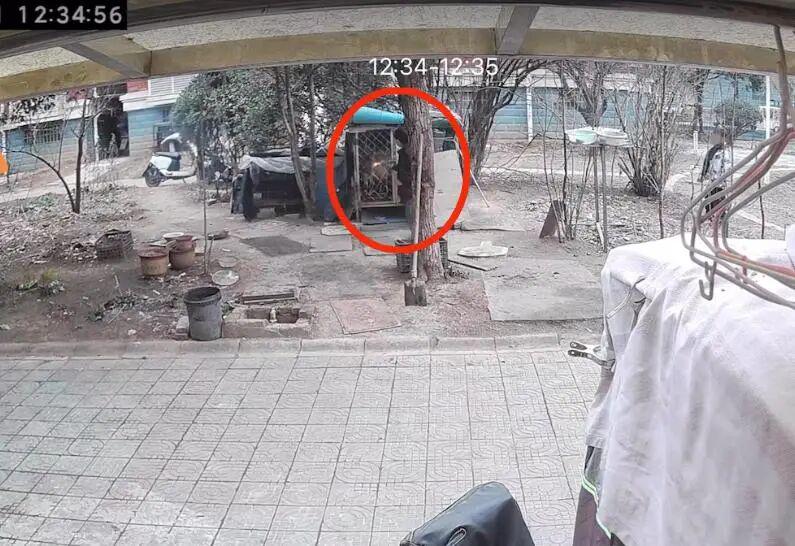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