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初秋。深圳市某监狱。
细如牛毛的雨丝打在牢房玻璃窗上,化作了数串雨珠直流而下,使人感到沉网和孤独。这是一间三平方米大小的女犯单人牢房。除了地板上铺着一张席子,一条薄被和墙角的一只便桶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女犯江萍坐在席子上正在梳妆,她平稳而熟练地梳理着头发,又用手指舒展一下眼角。从她的动作表情上几乎看不出她是个犯人,倒像在演出前精心打扮的女歌星。这时监房外传来了脚步声,江萍抬头向外望,站起身来。女看守用钥匙打开了牢门,不久后法官宣读了执行书,随后她被押赴刑场……

1977年的一个夜晚。在深圳市的一个亭子间里,四个女孩子围着一张小方桌边喝着麦乳精边谈有二个多小时了。四个女孩对前途都充满各种退想。她们是建筑工人,成天爬脚手架,与油漆、水泥、黄沙打交道,这个工种当时的社会地位是不高的。她们议论也很现实,什么“准备将来去读大学”啦,“发挥女性优势,找个好丈夫”啦,等等。江萍那年刚好二十,她却觉得这种议论与现实差得太远,毫无意义。
放在五斗橱上的“三五牌”台钟敲了七下,想起女伴朱丽琴邀她今晚务必去一次。她急忙出来,匆匆登上电车而去。下了电车,江萍来到朱丽琴的家里。不巧,朱丽琴还未回家。正当她失望地想离去的时候,朱丽琴的哥哥朱杰却热情地请她进屋坐会儿。
“你不是很崇拜这一带撑市面的何富强吗?今晚他正好在我家聊天。”
“真的!太幸运了!”江萍有点喜出望外。
几年前,她就听说这一带有位叫何富强的人如何刚强仗义,豁达耿直。她却一直没有见过。今天她能与这位“乱世英雄”见面,不整然心动。
她步入客厅,看见临窗的桌子旁坐着一位英俊酒脱,二十八、九岁的男子,高高的个子,白皙的脸。
“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何富强。”朱杰指着江萍说:“这位是我妹妹的朋友江萍。”
江萍想象中的何富强应当是一位高大魁伟的鲁莽汉子,而眼前这位竟是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简直出乎意外。
“今天你们有幸在这里相逢,想必是天赐良机吧!”朱杰的俏皮话说得江萍脸上热烘烘的。
“也许是丽琴故意安排的?不然她怎么偏偏不在家?”江萍蓦然闪过这个念头。
“何大哥在什么地方工作呀?”江萍寒暄着。
“街道小厂,混饭吃嘛!”何富强直率地说。
“他可是被社会埋没的人才呀!”朱杰插话说:“他有个叔叔在海外,迟早要出人头地的。”
江萍听了这话心里一跳,暗暗瞟了何富强一眼。
“哪里!哪里!”何富强谦逊地摆摆手,轻声地嘘了口气。
不知是同病相怜,还是“海外”这两个字有吸引力的缘故,两个人说话十分投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朱杰见他们谈兴正浓,推说去准备夜宵,悄悄地溜走了。屋里额时空荡荡地剩下了这对青年男女。江萍用期待的目光打量着何富强。虽然,眼下她还与另一青年周金华保持着某种关系,可那算不上什么恋爱,何况小周哪能和眼前的何富强相比呢?想到这里,江萍的脸忽然红了。她心中想说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何富强意识到有一道灼热的目光向他射来,他慢慢抬起头,从眼神中,何富强明白了江萍的意思。
“我们出去走走?”何富强发出了邀请。
春风沉醉。两个人默默地在江畔走着。

时针指向十一时了,江萍的母亲坐在沙发上等女儿回来,沙发边茶几上放着一封信。
雪白的信封上写着江萍收,下面署着周金华的名字。母亲认识这个小伙子。一年前江萍在技校还未毕业时就带他来家玩过。以后两人一直来往。她对这件事一直不满意,她从周金华的穿着打扮看出他家境不怎么好。多年来,母亲一直把女儿看作自己的希望,因为她音质好,嗓子清脆,将来一定会有发迹。发现这个小伙子给女儿写情书,母亲有一种预感,好像他会把女儿夺走。
母亲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刚刚站起身,门铃就响了。“这么晚了,你到哪儿转去了?现在该有分寸了!”
“我懂!”
“光懂得有什么用。”母亲责怪着,手指着茶几上的信说,“又给你来信了,那个周金华,你至今还与他往来,你真喜欢他?!”
“我们只是玩玩而已。”
“玩玩?我的小姐,你也太随便了。难道等将来跟他去喝西北风?”
“烦死人啦!我可没说过要同他结婚。”江萍抓起茶几上的信往卧室走去。
江萍躺在床上,打开台灯,她撕开信封,抽出信纸看下去:江萍:打了几次电话,写了无数封信,都不见你的回音,不知你身体可好,真想你呀!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日子,半年前的今天,我们过得多愉快呀。谢谢你,我太高兴了,你那天肯定吃了一惊,是吧……
江萍看到这里,感到浑身火辣辣地发烧。信中说的“那天”,正是江萍委身周金华的日子。这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一种解脱,是临近考试时,她的功课自知难以过关,为了要周金华帮助,和他发生了关系。她边看信脸上边发着烧。
江萍迅速从床上爬起来,心安理得地给周金华写了一封回信:周全华同志……爱本来就是不可捉摸的东西。发誓永远相爱,话虽漂亮,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让我们成为好朋友吧!祝你获得真正的幸福。
江萍踢开周金华之后,开始与何富强频约会。

正当两人沉缅于卿卿我我的儿女情长时,何富强忽然从朋友们那里听到了江萍在少年时代的三次不寻常的罗曼史。
何富强听了朋友们的议论,心中不乐,他觉得像江萍这样的女人实在难以相信,自己已到而立之年,不愿把恋爱当成一场赌博,更不愿意成为江草母亲手中的第四张废牌。
一个初夏的夜晚,何富强和江萍见面了,这次是他主动约江萍的。他想趁双方感情还未陷得很深的时候,彼此明智地分手。
两个人来到绿化地带,找了块僻静的地方坐了下来。何富强冷静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当然,她闭口不谈,这次感情变化的起因是他承受不了她的浪漫性格。江萍仔细听着,脸上露出惊讶与不安的神色。
她是个聪明女子,立即意识到何富强的突然变卦,一定因听到自己过去的传闻有关。沉默了片刻之后,她坦率地说:“难道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过去我年幼不懂事,经受不住外界的诱惑。现在我成热了,能理智地按自己的意愿寻找一个称心如意的爱人。可你却要撤开我,你是不是在计较我的过去……”
“你说到哪里去了!”何富强惶惶不安地说。他没想到江萍居然会这样快洞察他的内心,把话挑明,他有点狼狈地说:“我完全替你考虑。你还年轻,有足够的时间去选择。我却是耽误不起的。希望你慎重考虑。’
“不!我什么都不想考虑。我爱你!”江萍突然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他狂吻,将整个身子倾倒在何富强的易上。
幸福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何富强有点受密惊。她的这种大胆的表露使得何富强不得不改变了这次约会的初衷。
自从江萍点燃了何富强心中的爱火后,他开始攻读外语了。他心中明白,这个比他小九岁的漂亮姑娘之所以爱上他。完全是因为他有海外关系,而要达到出国的目的,只有从掌握外语入手。
江萍呢,她也有自己的算盘,她一方面抓住何富强不放,一方面刻苦练习唱歌。在一位声乐专家的指导下,她的进步很快。

这对恋人就这样各自怀着不同的目的相爱着,拼搏着。
一晃就是三年,秋天终于来到了。几乎在同一季节,何富强被外事部门招聘当了翻译,江萍也挤进独唱演员的行列。
一个细雨绵绵的下午,何富强看完了江萍的演出,向她送上了一束鲜花,两个人打着伞在闷热的雨中行走,心里甜甜的充满着信心。
“江萍,我们结婚吧。”何富强以胜利者的口气大胆说:“我伯父在香港的一家公司聘请我去当公共关系部长。我已经在申请出境证了。”
“真的!”江萍兴奋得惊叫起来,“可我还没对妈说过咱俩的事呢。”
“应该对她说了。”何富强满有把握地说:“你我在事业上都有成就了,再说我已三十三岁了,我想你妈会同意的。”
江萍回到家里,母亲正等着她。桌上放着丰盛的夜宵,江萍在饭桌前坐定,沉默了一会,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妈,有件事我瞒了你三年,你不会生气吧,我已有男朋友了。”
“什么?你这个死丫头!”母亲用手指戳着女儿的额头说:“他是什么人?”
“翻译。”
“啊呀呀!翻译有啥稀奇!你是昏头了吧!”
“人家马上就要去香港了。”
“听妈话,要找就得找美国、法国、日本的,好地方多着呢。”
“我们谈朋友已经四年了。我要结婚!”
母亲急着说:“你的前程还刚刚开头。就准备自己毁了呀?”
“妈!我都已经二十四岁了,你以前不是说,男人三十一枝花,女人三十豆腐渣嘛。你真要让我变成豆腐渣才出嫁呀!”
“你可不同,你是歌星呀,你看看,那个演员不是很晚才成家的!”母亲固执己见。
啪!江萍把碗筷往桌上一丢,生气地坐在沙发上,母亲心疼了,她灵机一动,来了个缓兵之计:“妈答应你,不过有个条件,一定要让他先出去定居,然后你们才能结婚。”
第二年春天,何富强去香港了。消息传开,至爱亲朋纷纷跑来祝贺,江萍感到有一种优越感。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这对牛郎织女天各一方。两年当中他们有时通长途电话表表爱心,有时在广州相会度蜜月,更多的是靠书信互诉衷肠。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外,半年前在信中还自称“日夜思念你的娇妻”的江萍,半年之后却投入他人的怀抱。
如今,女歌星在豪华宾馆的卧室,江萍对着镜子精心梳妆打扮起来。这是一个大套间,布置得高级大方。

四十八岁的皮尔逊住进这房间来,已经有半个月了,他原是某国跨国公司派往深圳洽谈业务的代表,一个道地的“中国通”。在一次联谊会上,皮尔逊和女歌星江萍相识了,很快发展成了这种同居关系。这次江萍与南方某大城市签订了演出合同:起码要一个月时间。江萍立即让皮尔逊以洽谈业务为名,赶往南方这大城市。她的算盘打得很精确,自己住宾馆,要皮尔逊把住处安置在她演出场所和宾馆的当中。这样,皮尔逊就找到了目前下榻的酒家。江萍每次来,一定都在中午,这样就不会引起工作人员的怀疑,混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不易被人发觉,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啊!
皮尔逊穿好了西装,用一只肘支撑着身子斜躺在沙发上吸烟,目不转晴地看着江萍的背影。
“我打扮得很美吗?”江萍一边说着,一边从镜子前支起身来,满脸笑容地问皮尔逊:“我们相识的时间不短了,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能带我去贵国吗?”
“你去干什么呢?”皮尔逊双肩一耸,做出无法理解的神态。
“唱歌呀!我在国内还有点名气的。”江萍自信地说。
“No! No!”皮尔逊连连说着:“请别生气,你唱的歌我听一遍就腻了。你又不懂外语,唱给谁听。”
“可以先去念书嘛!”江萍几乎在恳求了。她感到有点自卑。
“念书?!那得花很多钱!我可没那么多钱!”皮尔逊一口回绝。
“我们可不是一般关系,你总得想想办法。”江萍十分沮丧,没想到皮尔逊如此无情。
“你可以和我结婚。这是到鄙国去的捷径。”皮尔逊亮出了“底牌”。
“那怎么行,我们都有家庭呀。”
“可以离婚嘛!不然,要婚姻法干什么!”
江萍没法说下去了。她想,和这个外国人结婚,不能指望有什么幸福。可是,她想到自己一旦出国,灿烂的人生大门就会向她打开,地位、金钱、名誉就会接踵而来。她的虚荣心似乎得到了满足。

她有点尴尬地对皮尔逊说:“让我想一想再答复你。现在几点了?”
“四点半。”皮尔逊抬起胳膊,看了看手答:“你的演出不是在晚上吗?吃了晚饭再走吧。”
“不了!”江萍最后凝视了一眼,心里盘算着,为了出国,和丈夫离婚,似乎有点利己主义,但只要手续合法,不能说不正当吧。在没有正式离婚之前,同皮尔逊的关系仍然要保持下去。这是她的打算。
江萍准备和何富强离婚的决心,是在回深圳市后的当天晚上和母亲商量后才下定的。
母亲比女儿更狡猾,她说:“你已经是个有名气的歌星了。公开提出离婚,会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
“皮尔逊的目的很清楚,不与他结婚,他绝不会带我出去。”江萍有点困惑了。
“可以让何富强自愿提出离婚嘛!”母亲给女儿出了一个极妙的主意。
第二天,一封“家有急事,见电速归”的特急电报,发往了香港,何富强怀着不安的心情,从香港真飞回。这时分开半年的夫妻又相会了。

这是一次辛酸的最后会面。
“我有件要紧事告诉你,这件事关系到我们的命运和前途。我怕打长途电话讲不清楚,所以拍电报让你赶回来了。”江洋偎依在丈夫怀里,沉重着嗓子说:“我要出国了。”
“出国!怎么这样快呀!你从未谈起过呀!”何富强感到太突然了。
“现在就缺三万美金了,机会难得呀!”江萍故弄玄虚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当然,隐瞒了皮尔逊不可告人的关系。
何富强相信了。但不同意去她去。一来自己拿不出这么多钱。二来怕江萍只身到了国外,将自己甩了。
“我看你还是到香港去吧。我已经在办居住证了。”何富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香港我绝对不去。”江常气呼呼地从丈夫怀中挣脱了出来,“我明确告诉你,去的决心我已定了。你不去,我一个人去。”
“我拿不出这么多钱呀!你怎么去?”何富强一筹莫展。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江萍侧过身子想:母亲这一着棋真高明,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何富强拿不出钱,提出离婚就有理由了。同何富强分手是她计划中的一部分。这种想法无论走到哪里都说得通。
江萍用肩膀碰了碰何富强的背脊说:“我们还是分手吧。既然我们之间的爱已经到了不能发展的地步,分手也是十分自然的。”
何富强万万没有想到,江萍拍电报让他回来是离婚的,然而,江萍毕竟是他相爱多年的妻子,他想用感情去融化她,就像当初江萍融化过他一样。
他重新将妻子搂在怀里:“江萍,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呀!”
“去去去!”江萍粗暴地将丈夫推开:“你不要用爱来束缚我的自由。爱是爱;自由是自由。你不肯花钱让我出国,说明我们之间根本没有爱可言,这样共同生活还有什么幸福。”
“我真不明白,难道我们之间的爱情非要到外国去才能发展?你看看周围,有多少人能出国?他们不是生活得好好的吗!”
“人家怎么着不管我的事。”江萍狠狠瞪了丈夫一眼:“我不想束缚你。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白,束缚对方并不是爱。承认对方有自由,祈求对方自由发展幸福生活,这难道不是真正的爱吗?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好呀!拿三万美金来,皮尔逊可以马上保我出国。”
“什么皮尔逊。”何富强既吃惊又恼火:“你大概与皮尔迅搭上了吧!”
“搭上了又怎么样?”江萍干脆摊牌了。
“好!你把与他的关系老老实实写出来,我可与你离婚!”何富强气得浑身发抖。

不知什么时候,天上下雨了,落在屋檐上,很快就化成了滴滴水珠。
第二天清晨,江萍来时。发觉何富强已经走了,床头柜上的台灯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万万没有想到,我们之间的感情如此脆弱的,难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一点值得留恋的东西吗?我把爱情视同生命。失去你,我也就失去了生命。想一想吧,我在母亲家等候你的回音。如三天后你依然固执已见,我将用生命来唤醒你的人格和良知。富强85,12,4。
何富强的本意想用“死”来规劝江萍回心转意。然而,此刻的江萍已完全失去了人的感情。
她听人家说过,真正想死的人是不会将打算告诉别人的。她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三天后”几个字上,一个罪恶的念头在她头脑中涌现:“何富强想用死来威胁我。他就留下了自杀的证据,我何不顺水推舟,帮助他真的死去。”
江萍开始向罪恶的深渊一步一步走去。
1985年12月7日晚上九时,她以去外地演出为名,告别了母亲,在外面游荡到十时左右,在残月的微光下,悄悄地溜进了何富强的住所。四周一片寂静,人们都已早早入睡。当时,何富强正坐在床上看书。
“你是来看我是不是死了吧?”何富强看见江萍轻手轻脚走了进来,神情冷漠地说。今天是他纸条上写的“三天之后”的最后一天,他估计江萍会来的。
“我对不起你,富强!我越想越后悔。”江萍一头扑到丈夫的怀里:“我不该逼你。我想通了,我还是跟你去香港吧。”
何富强似信非信。尽管江萍狂热地吻着他,他还是用奇异的目光看着她:“你不是骗我吧。”
“你不信任我!”江萍边说边脱衣服:“我们毕竟相爱几年呀!”江萍钻进了何富强的被窝里:“我,永远属于你的。”
何富强不能自持了。
“看你,这几天瘦多了。都是我不好。”江萍伸手在持包里掏出一瓶“青春宝”,“这是根据明朝永乐间太医院的廷秘方研制的,算我向你请罪!”江萍说着打开瓶盖,取出了两片,“把嘴张开。”
何富强乐不可支。
他失算了,江萍给他吃的是这两天她躲在家中精心加工的剧毒品。他只期望得到妻子的爱情,而忘掉了妻子的残暴……

深夜十点,江萍看着何富强不动弹了,急速穿好衣,又悄悄地溜了出去。登上了一辆开往火车站的公共汽车。
江萍在外地演出的日子里,提心吊胆地度过了一个星期。第八天下午。当她刚走出深圳市火车站。两名便衣公安人员立即将她塞进了一辆装有警笛的车中。
当晚,江萍就受到了审讯。预审员给她侧了杯水后,就摊开了“审讯笔录”边问边作记录。
“你丈夫死了,你知道吗?”
“呀!死了!江萍喃喃地说着。忽然嚎啕大哭了:“哎呀,早知他真的要自杀,我就不该去外地演出了呀!”
预审员淡淡地一笑,扬了扬从她包里搜查到的纸条说:“你保留着何富强写的这张纸条,是想告诉我们他有自杀的动机吧!”
“不,我估计他不会自杀的。”
“这就对了。所以你就想方设法谋杀了他。何富强是在你计划去外地的那天晚上十点死的。当时你在什么地方?”
“在火车站候车室。”江萍拼命抵赖。成败在此一举,不能承认,她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了头上:“火车票就是我不在现场的证明。”
“你说谎!你晚上九时离家,一时四十五分开车,这恰恰证明你有作案时间。”
预审员用冷竣的目光注视着江萍说:“我们掌握着证据,”说着,从一个白信封中掏出了“青春宝”塑料瓶,“这上面留有你的指纹。”

江萍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作案时慌乱中忘了拿走瓶子。但她还是想作最后的挣扎:“这补药是我买给他的,当然会有我的指纹,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再说,我为什么要毒死他?”
“你说对了!何富强确实是被毒死的。至于动机嘛,就要听你老实交代了……”
江萍瘫倒在座椅上,雨越下越大,玻璃窗上“啪啪”作响。
江萍讲完了自己可悲的人生旅程,悲哀地低下了头。她给自己描绘了人生的蓝图,以及自己的野心、自负、希望,一切一切都已崩溃了,她失声痛哭起来!
每个人当然有为自己美好的前途奋斗的自由和权利,但过分的自私,终于导致了这个女人的毁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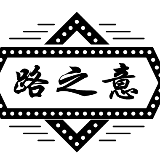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