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流水,不知不觉间,我从工作岗位上已退休几年,在县城定居。然而,我却常常念想起生我养我的农村老家,还有老屋和老乡们。
我出生在浙赣交界的一个小山村,中学毕业前,几乎没有走出过本县之外。即使中学毕业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我仍然在老家的几平方公里内打转转。我在老家的土地上,走读、砍柴、割稻子,家乡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一水一山,是那样的“熟视无睹”,也不知道什么叫“乡愁”。
哪曾想到,在一个立冬之日的下午,我在生产队砍杉树的劳动中,不小心打伤眼睛。经过本地卫生院治疗一个星期后,仍不见好转。来年的正月里,听说相邻的某市下级卫生院有一位眼科医师特别厉害。我跟着表哥,第一次坐上了绿皮火车,来到了该卫生院。经过医院检查,需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表哥是他家中的主劳力,也没有功夫天天陪我,第二天就打道回府了。
在卫生院煎熬的日子里,我才第一次感到了背井离乡的苦闷。虽然医院里的几个病号成了我同病相怜无话不说的朋友,但我还是日夜都在想念家人,想念家乡。然而,那时候老家没有电话。思来想去,只有通过写信方能与父母亲联络。于是,在漫长的夜里,我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问父亲在家里干些什么农活,要注意休息,叫母亲别担心我的眼睛,这里医师水平很高,另外,请家里再准备些钱,可能还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
过了几年,我考上了“离乡不离土”的干部,来到了距离老家十多公里的乡政府工作。
在乡政府的日日夜夜,虽然此地的生活习俗与老家相似,但我仍然时常想起老家:门口的小溪水是否还是那么清澈,屋后的毛竹林是否依然茂盛,乡亲们是否依旧延续着传统的耕作方式。
记得有段时间,乡政府工作忙,我一直没回家。在那个寒冷的冬雨夜晚,我在一篇短文中这样写道:“夜,令我难以入睡的夜。我想给远方的老母捎一封家信,可是,我的母亲却不识字,我不愿用别人的嘴去传递我们的母子之情……人们常说,举目无亲是一种痛苦。而我想,思念远方的老母,又不能相见的时刻——不更是一种折磨吗?!”
又过了几年,我调到另一个乡镇工作。没多久,根据组织安排,我来到离老家数百公里的绍兴政法干校培训。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学校规定不能离校。那时我已结婚,儿子还在读幼儿班,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家中的大小事全靠妻子张罗。学习期间,我为家里的事放心不下,因而,每到晚上,就用写家书打发。可是,爱人文化程度不高,一直以来不喜欢书信表达,我一连写了几封信寄出去都杳无回音。
正当我不知所措想请假回家的时候,突然,妻子来信了。大意是说“秋天已经过去,冬天来了,千万记得加衣服,今天寄来了冬衣……”我的心里顿时热乎乎的,虽然信中还有几处错别字,有的标点符号不妥,可我却像冬天里晒到了温暖的太阳。当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回想起多年来妻子一直忙里忙外累垮了身体,唯独忘了自己学文识句。第二天一早,我买来一本《新华字典》,连同一封厚厚的家书寄了出去。
后来,我调到了县电视台工作。每当休息日回老家,都有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首先见到的是村口的小桥,桥下潺潺流水声是那样的亲切;一会儿摇着尾巴的小狗也来到我的身边;村上的大嫂大娘用乡音呼唤着我的小名;母亲在门口的小溪里浣衣;父亲在不远处的自留地里耕锄。几位发小看到我,一再邀请我到他家喝一杯。
待我要返回城里的时候,父亲早已准备了自己种植、刚刚采摘来的新鲜蔬菜;母亲轻轻地叮嘱着我什么,还把我送到村口的竹篷底下,等到我上了公交车,她还久久不愿离去。
进入新千年,父母亲先后离世,老家的老屋变得长年“铁将军把门”。到了2013年,在“三改一拆”的进程中,老屋终于被连根拔起,只剩下一片杂草丛生的老屋基。从此,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
最近,我又回了一趟老家,静静的老家——山水依旧,楼房林立,绿树成荫。可是,不见了袅袅的炊烟和父老乡亲忙碌的身影,难道是天上的大雁带走了我的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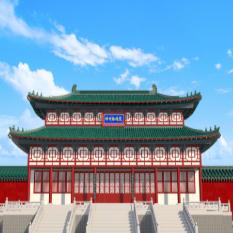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