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云
怎样正确看待“诡案”?“诡案”是否真的是鬼怪或其他非自然力量所为?了解和破解“诡案”对现代人到底有什么意义?
一谁把猪头换成了人头?
乾隆二十八年,福建长乐县。
这一天的傍晚时分,一位捕役在县署门口,看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提着布囊经过,随口问:“小哥袋内盛何物?”少年说是猪头,捕役看那物什透过布袋露出的形状,不大像是猪头,多问了两句,少年火了:“非猪头,岂人头耶?!”一边说一边把布囊扔在了地上,谁知滚出的竟真是一颗鲜血淋漓的人头!
少年“大恐,啼泣”,捕役办了一辈子差,头一次见到这么诡异恐怖的事情,立刻将他锁拿,带进县署。县令也十分惊诧,把少年细细审讯了一番,听到的事情更加匪夷所思。
少年的母亲名唤李氏,是本地的民妇,25岁那年生下儿子,过了半年丈夫去世,家里只剩一个婢女和一个男仆。李氏全力抚养儿子,她的贞节让乡里乡亲都竖起大拇指。这天早晨,李氏起床,忽然见到一个白衣男子站在床前,她大喊大叫,男子钻到床下。婢女和男仆冲进屋,床下却空无一人。到了中午,在外面上学的儿子回家吃午饭,突然看到那白衣男子又站在床前,“骇而呼,男子复趋床下没”。
李氏对儿子说:“听说财神就是穿白衣服的,咱们这屋子祖居至今已经百余年了,难道是先人显灵,指点我们埋藏金银财宝的地方?”于是打开床下地板,只见一张青石大如方桌,“上置红缎银包一个,内有白银五铤”,李氏大喜,跟儿子说:凡是挖掘宝藏应该先祭祀财神,你去集市上买个猪头当牲礼,祭祀之后再打开青石板。
儿子于是来到集市上,买了个猪头,这时想起没有带钱,就把那个红缎银包给了卖肉的屠户说:“这里面包有五铤白银,先当做抵押,我到家拿钱再换回来。”然后把猪头装在布囊里回家,路上遇到了那个喜欢刨根问底的捕役。
县令马上下令,将卖肉的屠夫抓来,屠夫说确实有红缎银包换猪头这件事,红缎银包他还没打开,现在“以银袱呈上”。等打开那银包一看,里面却是一块血染的白布,哪里有五铤银子,“中包人手指五枚”!县令大骇,亲自带着一班捕役来到李氏家,启开青石板,只见里面躺着一具无头男尸,“衣履尽白,右五指缺焉,以头与指合之相符”。
案件发展到此,所有人都认为这是鬼怪作祟,只能把屠夫和李氏的儿子暂时拘押在监狱,过一阵子再释放,而“长乐奇案”也成为一起无法结案的悬案。
二没有垫脚物是怎样悬梁的?
相信读者看到这里,已经明白何谓“诡案”了:凶案是真实的,受害者是真实的,此外的一切一切,都诡异莫名。
“长乐奇案”记载在清朝文学家袁枚所著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子不语》当中,过去人们常常将这本书视为鬼故事集锦,却忽略了书中所写的许多案件,都有真实的事迹可循,如《田烈妇》写的是雍正年间广有影响的“田烈妇冤魂显灵案”,《王弼》写的是以恐怖血腥而闻名的“中书鬼案”等等,而从时间、地点和叙述的详细程度来看,长乐奇案应该也是以真实的刑事案件为素材的。
像此类的“诡案”,在史料笔记中数不胜数。
例如清代史料笔记《履园丛话》(钱泳撰)卷十七写“沈西园命案”:光州一个老贡生,儿子远游,家里只有儿媳妇和五岁的小孙女相伴。邻居见其儿媳貌美,就说老贡生之子出游前曾向他借钱,“书一伪券,以妻作抵”,然后拿着伪造的借据去告官,时任光州刺史幕僚的沈西园与另一吏目收受贿赂,判决“以媳归邻某”,老贡生认为借据有伪,又无计可施,愤而上吊自杀。儿媳妇先将五岁的女儿勒毙,也自缢身亡……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初七,沈西园“夜见一戴顶者,携一少妇幼女登其床,教之咳嗽,旋吐粉红痰。自此三鬼昼夜缠扰,遍身拧捏作青紫色,或独坐喃喃,自为问答”。这样迁延到正月十五日,沈西园在卧房里突然一声惨叫,家人冲进卧室,他已经死了,“其尸横扑椅上,口张鼻掀,须皆矗立,双目如铃”。
清代笔记小说《客窗闲话》(吴炽昌撰)中的一则“童子自缢案”,更堪称具有代表性的“诡案”:有个十二岁的小孩子,“父母以疫相继亡”。伯父母将他收养为继子,让他单独住在一间屋子里。一天,过了中午,小孩子还没有起床,呼之不应,打开窗户一看,孩子已经悬梁自尽了。“夫妇惊泣,呼邻里掇门入室”,发现“室中仅有土炕,无椅桌之类。自炕至所悬之梁,相距九尺余。童子何能跃而上?奇矣!”拿了梯子将尸体解下,发现小孩子是用四尺余裤带自缢的,而裤带绕在悬梁的梁木上有三尺,“项上仅有尺余”,脖子勒得紧紧的,那么是怎么“先给扣而后入颈”的?在发现“脑后八字不交”(自缢者的缢绳经耳后越过乳突,升入发际,在头枕部上方形成提空,所以索沟不闭锁,这是鉴定死者是否自杀的参考要素之一)之后,官府确认孩子是自缢身亡,至于他是蹬着什么器物到房梁下面的,又是怎样将脑袋伸进比脖子的直径大不了多少的缢索中的,答案只能付诸鬼神了。
三冤魂右耳为何挂一条白练?
还有一类“诡案”,虽然最终成功破获,但侦破过程却比案情本身更加不可思议。清代笔记小说《池上草堂笔记》(梁恭辰撰)中有一则“鬼魂诉冤奇案”,即是此类典型。衡水县有个男人死了,死者的侄子向官府控告,说死者是被谋杀的,但是仵作验尸之后,没有发现凶杀的迹象。侄子不服,上诉到巡按那里,巡按派另一个县的县令邓公去衡水县复审。邓公到了衡水县,反复验尸,也找不到他杀的证据。
这天深夜,邓公在馆舍里批阅案子的卷宗,不觉已到三更时分,桌上的烛光突然变得黯淡,一阵阴风吹来,墙角出现一个人影,乍隐乍现,然后就跪在桌案下,发出低微的啜泣声,好像在倾诉什么。邓公惊惧之时,觉得那人的身形酷似白天所验的尸体,而且右边耳朵垂下一条像白练似的东西,忽然有所领悟道:“你可以走了,我一定会替你雪冤!”那冤魂磕头拜谢之后,消失无踪了。
桌上刚刚黯淡的烛光,重新摇曳起了光焰。
第二天一早,邓公找来衡水县令和仵作。到了停尸房,邓公命手下检查尸体的右耳孔,仵作一听,大惊失色。结果从尸体的右耳里掏出了足有半斤重的沾了水的棉絮。原来,凶手是趁着死者熟睡时,用长钉从右耳凿入,刺入其脑髓,使其一命呜呼,在控干了耳中流出的血水之后,用沾了水的棉絮塞进耳洞,掩盖伤口。那仵作因为收受了凶手的贿赂,在验尸过程中自然也就“卖个人情”了。
而公案小说和古代戏剧中,这一类的“诡案”就更多了。《包公案》的《木印》写包公来到一个叫横坑的地方,发现“忽有蝇蚋逐风而来,将马头团围了三匝”,包公觉得“莫非此有不明之事”,派人跟着蝇蚋而去,结果在一棵枫树下发现一具死尸,原来是死者化为蝇蚋向包公申冤。还有以“中国第一鬼戏”而闻名的《乌盆记》,富商刘世昌路遇大雨,投奔到开窑厂的赵大家,被赵大夫妇杀害,肢解焚尸后,骨灰掺入乌盆,三年后赵大把乌盆送给张别古抵债,刘世昌的冤魂一路跟来,请求张别古替他申冤,最终包公审理此案,将赵大夫妇绳之以法。
四对“长乐冤案”
的推理
让我们循着这样的思路,对前面提到的几个案子试做破解。
首先是“长乐奇案”。
刑事侦查学的相关研究告诉我们:物证比人证可靠,而在人证中,远离事件中心的人提供的证词,比接近事件中心的人提供的证词更可靠,这是因为越是远离事件中心,其由于利益或恩怨做伪证的可能性越小。
在“长乐奇案”中,最有价值的物证是人头、尸体和断指,它们说明了案件的本质: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被埋在李氏屋子的地板下面,人头和右手的五根手指被割下。再来看人证,不难发现,导致案件变得诡奇叵测、云雾缭绕的,统统是李氏及其儿子的供词——婢女和男仆并没有见到活着的白衣男子,他们对于白衣男子的印象都源自于李氏及其儿子的口述。在诸多人证中,卖猪肉的屠户距离事件中心最远,他的话可信度最高。
屠户告诉我们什么?一、他收到红缎银包一个;二、他给了李氏儿子一个猪头。
那么谁能把猪头换成人头呢?只有李氏儿子一个人。再考虑到如下条件:李氏作为一家之主,其卧室他人不能擅入;床下的青石板绝非一个人所能搬动,买猪头是李氏让儿子去的,我们基本可以认定:是李氏和她的儿子杀了人,并策划了这起“诡案”。
案件的真相推理如下:李氏和儿子前一天晚上杀死白衣男子之后,因为事情突发,只能把尸体藏在地洞里,由于婢女和男仆都住同一个宅院,不可能大张旗鼓地从外面捣腾泥土进屋掩埋,尸体很快就会发出异味,导致罪行败露。于是母子俩横下一条心,将案子变成“诡案”——在我国古代,相当一部分官员十分迷信,只要凶案与鬼怪挂上钩,或者笼罩着一股诡异气氛,他们就不会深究。于是,李氏和儿子割下受害者的首级和右手五指,分别放在布囊和红缎银包里,把红缎银包放在青石板上,重新压好地板。第二天早晨,儿子去上学,李氏开始表演“看见白衣男人”的独幕剧,让婢女和男仆以为真有神灵出没。到中午,儿子回来吃饭,再次声称看到白衣男人,加固诡异气氛,然后李氏假意说是“财神到”,打开地板,“发现”红缎银包,再差遣儿子去买猪头。儿子把受害者的人头先藏好,进集市买了猪头,并用红缎银包当做抵押,屠户忙着做生意,没有打开红缎银包——如果当时打开,提前案发,李氏儿子把白衣男子之事一讲,除了发现“无头尸”,结果不会有什么不同——李氏儿子出了集市,把人头装进布袋,猪头扔掉,再去县署附近溜达,故意引起捕役的注意,接下来的一切,就按照他们的策划来发展了。
至于犯罪动机,我非常不厚道地认为是长期守寡的李氏与白衣男子有了奸情,受到他的敲诈勒索,才跟儿子一起下了毒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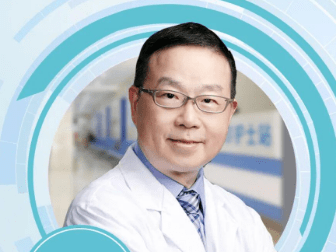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