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鸡婆鞋
(原标题:鸡婆鞋)
说到鞋,我们便会想到各种各样的鞋。然而,再贵再漂亮的鞋,都不如我的婆(奶奶)曾为我做的鸡婆鞋。 说起鸡婆鞋,你也许会嗤之以鼻,说:“好丑的鞋呢。” 是的,与现在那些漂亮的鞋们相比,鸡婆鞋的确是丑。然而,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的婆给我做的鸡婆鞋,却温暖了我的整个童年,在我眼中,它便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最温暖的鞋。 自记事以来,我的婆,眼睛和耳朵都不怎么好。我父亲排行老幺——老十二,等有了我的时候,我的婆,便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 纳千层底儿的麻线儿,是我的婆自己做的。 记忆中,我的婆,种了一片麻。在麻收获的季节里,我的婆,把麻杆割回家,去掉麻叶,把麻皮剥下来,泡在水里,然后用一把专用的剔麻的刀,一遍一遍地剔着麻皮,剩下的纤维,便是婆要的麻。 我喜欢看我的婆捻麻线儿。一根根粗细不一长短不齐的麻纤维,在婆的搓捻下,成了一根长长的粗细均匀的麻线儿。我的婆一边捻麻线儿,我一边把它挽成线团儿。 “惠儿,挽成麻团儿。”婆说。 “不会啊。”我说。 婆搓捻完了那些麻线儿,便开始教我挽麻团儿。那麻线儿在婆的手中,挽啊挽,挽啊挽……同样是挽麻线儿,我挽出来的线团儿没有看样儿,放在地上,便会滚来滚去。我的婆挽出来的麻团儿,像一层一层的网格整齐地排列着重叠着,精致极了,放在地上,它像一个小小的鼓凳,静静地站在那里,绝对不会东倒西歪。 我的婆,教会了我挽麻团儿。以至于后来我在给女儿织毛衣的时候,我挽出来的如麻团儿一样的毛线团儿,得到了同事们的赞美,每当那时,我会很自豪地说:“是我的婆教我的。” “惠儿,帮我穿针。” “嗯。” 婆的眼睛不好,她总是等我去她那里陪她的时候,让我帮她穿针。给婆穿针,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在我的记忆里,婆的眼睛,是看不清那密密的针脚的,她全靠手指去触摸那细细的针脚,凭着感觉,摸索着纳千层底儿。那时候,我真是佩服我的婆啊,她的眼睛看着别处,却还能一针接一针地纳着鞋底。 鸡婆鞋的鞋帮和鞋面,一般里层用花布,外层用或青或蓝的灯草绒,两层之间,再夹一层厚厚的棉花。为了让我能穿得紧实,我的婆,在鸡婆鞋的后跟处缝了两根布绳,在穿鞋的时候,把布绳绕在小腿上缠两圈,再套上,不管跑多快,鞋也不会掉。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在那些冬天也只能穿一双破胶鞋的日子里,能穿上婆做的厚实而温暖的鸡婆鞋,是多么的奢侈。 每当穿上婆做的鸡婆鞋,我便舍不得出门。我走在干燥的屋子里,从里屋走到堂屋,在堂屋里转几圈,再回到里屋去。我不愿意到灶房里去,那里灰多,我害怕弄脏了我的鸡婆鞋。如果是下雨天,或雨过天晴路上还有稀泥,我是铁定不会穿鸡婆鞋出去的,一定要等到路面干透了,走在上面,鞋上一点也不会沾泥的时候,我才会把鸡婆鞋穿出去。 有一回,我穿着一双新的鸡婆鞋,路过池塘边的时候,不知道是谁,从池塘里弄了许多稀泥上来,把那段路弄成了泥泞小路。我可不愿意把鸡婆鞋弄脏了,便脱了鞋,光着脚,走过那段泥路,朝婆的屋里跑去。 “哟,冷不?”我的婆,从保温瓶里倒出热水来,一边给我洗脚一边问。 “不冷。”其实,我冷得牙齿也打架。 婆看见了我手里提着的鸡婆鞋,说:“穿龌龊了可以洗。” “洗了晒不干。”我说。 “烤干。”婆说。 我在心里想:弄龌龊了再洗,洗了再烤干,这样的鸡婆鞋,就不再是新的鸡婆鞋了。 后来,我的婆,再也不能为我做鸡婆鞋了,就连到我家去,也需要我一路扶着才行。 婆的鸡婆鞋,只能镌刻在记忆里了。 (作者单位:江津区李市中学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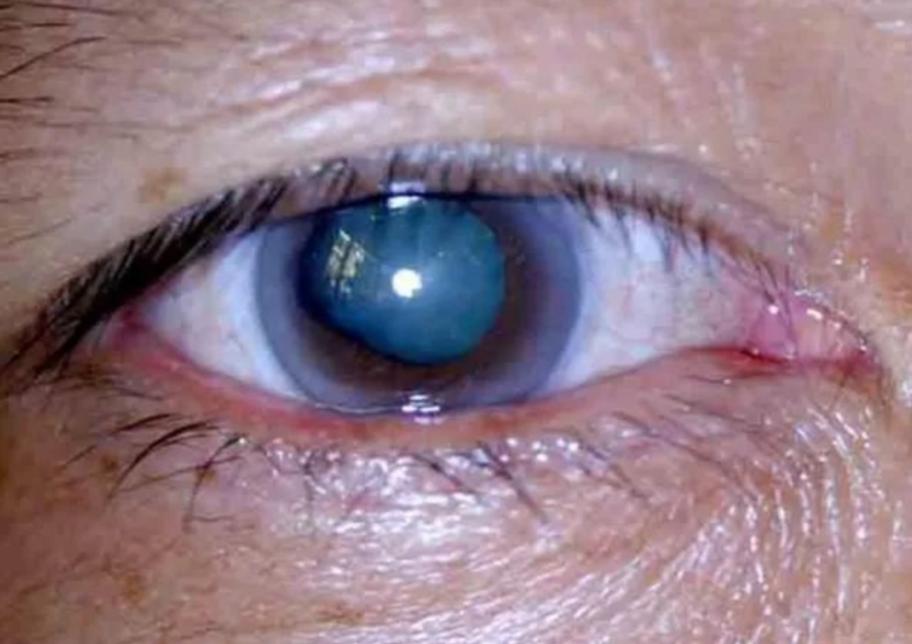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