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老街的过去式
黯然无闻的老街大抵酣睡无醒,未做旅游文章。可一旦粉墙黛瓦,游人接踵,脂粉气便随之而来。无论倾圮坍塌,还是完好无缺,再则修复如初,都是赝品了。真正的老街在哪里,在老人的回忆里,在里长巷短里,在人文轶事里。
我所叨念的老街,是“沥海”的老街。而沥海,原属上虞,现归绍兴滨海新城,谓东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
曾经就读的学校,三面砌墙,一边濒临小河,河水仅及脚踝,几近枯竭。就此毫不起眼的沟河,老师竟然说是护城河,我不禁狐疑地审视起沥海城。细味之下,也尽然。沥海素有东西南北门之说。没有城墙,何以有门?南门外,是我出生地,谙熟如掌纹。北门外,有汽车站,是通往百官的官道,迎来送往,熟稔得很。至于西门,从无涉足,现在还是。东门因有粮站,经常光顾。那时尚留一坨城墙,大概早已了无踪迹。约三层楼高,黄泥夯筑,几株稀疏的冬青树在顽强地生长。
据记载,沥海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古城,民族英雄戚继光曾在此抗击倭寇。
沥海城是方形,主街十字形,像个“田”字。老街宽不足三米,青石板铺就,被岁月沧桑磨洗锃亮的青石板上,跑过嬉戏的童稚,笑声咯咯犹在耳畔;踏过荷担的挑夫,粗布短葛下露出强健的臂肌;还有那水滴石穿的屋檐水……无不留下匆匆的印迹。街旁平房楼屋错落有致,平房屋檐低矮,触手可揭瓦。东西走向的老街相对平静,平静中透着人世沉浮。南北走向的老街喧闹非凡,店商云集。而十字街口,最是闹猛。它的南面,是沥海的最高食府,命名“大众饭店”。它的北面,是鱼虾鳗鳖的聚集地。
在老家,对于岁纹丛生的老者,一说起大众饭店,往事迎面而来,哪怕木讷者也能滔滔不绝。远的清楚,近的迷茫。这是物质匮乏的年代,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在我的回望里,大众门口的早餐,具有无可抗拒的诱惑力。每天清晨,大众门前香气四溢,热气腾腾。氽油条、煎大饼、蒸馒头……三分,半两粮票,可买一根油条,连这也要掂量一下。店内八仙桌、小方桌、条桌,高低俨然。其色彩,一如岁月,已被时光打磨得油光闪闪。没有殷勤穿梭如燕,吆喝声清脆悦耳,只有喝大时的粗声粗气,醉意蹒跚。“喏,这个败家仔,又去吃大众!”时至今日,那语调,宛若春水浸泡的种子,生长在记忆的深处。冠以“败家仔”,我想不至于。按春秋笔法,只是懂得享受而已,特定年代,特定称谓。
行文至此,讲一趣闻。改革开放后,沥海已是有名的建筑之乡。在上海淀山湖,一市委高官来此视察,他听到了熟悉的口音,得悉眼前农民工来自上虞沥海,就问“大众饭店”还在不在,末了遂一一握手,令甲方人员目瞪口呆。个中原委,此高官任地区级市委书记时,曾在沥海接受劳动改造。劳动之余,到大众饭店就餐,被拒,辩之用自己钱无有不可,告之也不行。如烟往事他还耿耿于怀,大众饭店的名气由此一斑。
大众饭店像一缕轻烟已飘散在远方,符合元稹的“白发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倒是老街的市场,历经风雨吹打,依然屹立。北门外,早已有大菜市场。然后在午后片刻时光,就陆陆续续在老街两边支起摊位,使得本已狭窄的老街愈加步履维艰。幸而仅短短一段,是微型市场,似与大菜市场分庭抗礼。
原先的市场是何模样?黄鳝泥鳅是野生的,河虾鲫鱼是天然的。至于海鲜,是从后海头捞的。哦,此处的后海头,就是杭州湾。印象最深当属鲚鱼、鲻鱼、小梅鱼和白虾。鲚鱼油煎,洒些盐花撒点葱,香气就上来,出锅时粘连似大饼,煞是好看。鲻鱼虽小,清蒸亦佳,现在倒是尝过大鲻鱼,色香味俱往矣。小梅鱼头大如斗,尾细如针,入口即化,那种滋鲜飘到现在也不曾散尽。白虾通体透明,沸水汆过,渐成淡红,头部有一粒红膏。有船用渔网,否则“抢潮头”,听说抢潮头是非常凶险的。如何凶险法,不得而知。只知潮汛来时,鱼也来了。抢了潮头,跨上“永久牌”自行车飞奔而来。一骑红尘食客笑,时人皆知海鲜来。俯仰之间,已摆上鱼摊。曾目睹小鲻鱼尚未断气,口一张一翕,肋间一起一伏。现如今老街上依然有海鲜,只是一部分早已被饭店买去,一部分提前被“吃食户”截留在北门外。
我在想,现在年轻人不知以往的老街。待到他们垂垂老矣,现在的老街就是他们记忆中的老街,天道轮回。
(原标题:老街的过去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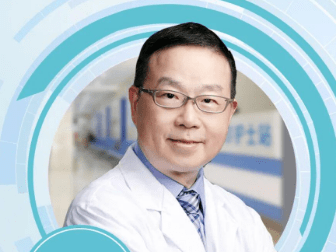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