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发生后的第三年,公元757年,唐朝廷终于迎来利好。这年10月,唐朝军队收京后,捷报频传,当时“虽相州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至758年春,叛军安庆绪已是“困守孤城,人心离”,朝廷胜利在望。
益
在这种形势下,朝廷里以唐肃宗为首,大多数人都陶醉在“中兴”的喜悦之中。认为当务之急应为重整朝仪、庆贺升平。他们不顾相当一部分地区仍处在战乱之中,不考虑刚刚安定下来的朝廷尚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对胜利后如何方能长治久安更无远虑,一味忙着祝捷庆功。
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左拾遗的杜甫写下了长诗《洗兵马》。
这首长诗语句工整,用词典丽,气势雄浑。表面上以歌功颂德为主,实则“寓讽刺于颂祷之中”。它是杜甫在举朝欢庆胜利之时,写给皇上的一份别具一格的“谏书”。
自两京收复后,杜甫一直跟在唐肃宗左右,亲身体会着“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中兴”气象,过着一种“天颜有喜近臣知”的生活。起初,他对形势也非常乐观,曾和王维、岑参等同僚互相唱和,写下不少歌时颂圣的诗篇。
但是,渐渐地,他身居禁掖之中,透过升平的外壳,看到了朝廷内外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且预感到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在“致君尧舜”的信念和作为谏官的强烈责任感的支配下,他觉得应该向皇上提出告诫。于是,他采用诗歌的形式,把时弊和自己的见解统统反映了出来。
杜甫究竟讲了哪些问题?

01 表面歌颂“中兴诸将”,实际反对借兵回纥
诗歌开篇,杜甫就高度评价了“中兴诸将”的历史功绩。杜甫认为,正是有了“成王”李俶,即后来的唐代宗、“郭相”郭子仪、“司徒”李光弼、“尚书”王思礼等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所以才再造了唐王朝和平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他在诗中尽情地歌颂他们,希望皇上能奖赏并重用他们: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
对这几个人的评价,在当时是并无异议的。但作为“谏书”,杜甫的这些赞词还包含着其它意思:这里面暗含着他对回纥军队的反感,和对皇上借兵这种做法的讽谏。
唐肃宗即位后,深怕自己只靠着“区区适长之名,未足以惮压天下”,故借兵于回纥。回纥当时是个生产力发展低下、“以寇抄为生”的游牧民族。安史之乱前基本上与唐王朝和平相处。
回纥善骑善射,勇于战斗。本来如果处理得好,向他们借兵也未为不可。但是,由于唐肃宗过于轻看自己的军队,一上来就同回纥达成了“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的错误协定,从而使得这种借兵,竟成了引狼入室的一种卖国行径。
对这一严重的失策,杜甫大为不满。早在《北征》、《收京三首》等诗中,他就一再指出,这样向回纥借兵,不仅会给百姓带来灾难,还会给朝廷带来威胁。其实,当时如能对自己的军队调动适宜,是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收复两京中原的。
所以对回纥兵多借不如少借,少借不如不借。既已借了,就应提高警惕。但唐肃宗根本不听。结果两京收复后,回纥“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财物不可胜计”,与贼无异,百姓不胜其弊。
在这种严酷的事实面前,唐肃宗不但不觉悟,反而“惟其所欲”,并在《封回纥叶护忠义王制》中称其“蒙犯曾不辞其劳,急难无以逾其分”,使回纥充分尝到了抄掠的甜头。于是提出要继续输入兵力,说是为了“余孽”。这分明是回纥“意犹未厌”,欲借机再行虏掠,而唐肃宗竟然“优诏许之”,使杜甫更生忧虑。
讨除
他觉得肃宗这样做,关键是不相信自己的将士。为扭转皇上这一偏见,他极尽颂扬之能事,把“胡危命在破竹中”归功于“独任朔方”,把“整顿乾坤济时了”归功于“二三豪俊”,把己方将领的形象刻画得十分高大,而对于被皇上誉为“功悬日月”的回纥军队,却毫不称许。
只一句“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喂肉葡萄宫”,杜甫就点明了其危险性,它使人意识到回纥的贪婪本性,使人对于京师里充满了这种人而深深担忧。
杜甫用心良苦。然而遗憾的是,唐肃宗急于求成,一意孤行,至使回纥恃功自傲,“略华人,辱太子,笞杀近臣,求索无倪”,唐朝“引外祸而平内乱”,终于不胜其弊,吃了大亏。

02 借歌颂玄宗旧臣,用以贬斥肃宗周围的新贵
杜甫在诗中,提到了另外几个人物:
“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
这里杜甫一没写出真实的姓名与官职,二没有平均使用笔墨,因而引起后来读者的纷纷猜测和议论。
其中“张子房”借指张镐比较肯定,《通鉴》记至德二载夏四月“以谏议大夫张镐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旧唐书·张镐传》记他为人“不交世务,嗜酒好琴”,天宝末“自褐衣拜左拾遗”,《新唐书》称其“仪状壤伟,有大志。”这都和杜甫描写的特征相符合。
而“萧丞相”最有可能是借指房琯。这不仅仅因为房琯曾“自蜀奉册留相肃宗”,并于758年春仍在京师做太子少师的缘故,而且据《汉书·萧何传》记载,他的主要事迹之一是“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为刘邦组织了兵力。
而房琯的主要事迹则是建议诸王分镇天下。据说安禄山一见分镇诏书,立刻哀叹:“吾不得天下矣”,因为“难危之际,以亲王重藩分布外镇夹辅王室,统系人心,自是长策”。这说明房琯之策也有组织兵力的作用,杜甫这么比是有道理的。
杜甫把房琯、张镐比作萧何、张良,引起了许多后人的疑问。如宋代《蔡宽夫诗话》云:
“镐虽史称有王霸大略,然当为相、收复两京时,不闻别有奇功……岂史事或有遗耶?”
人们对“萧丞相”的争议,也是这个意思。于是有人解释说,杜甫是因为和房张私交甚密才这样做的。的确,杜甫和这两人关系不错,但是如果说杜甫只为这个抬高房张的声誉,不仅小视了杜甫,而且忽略了其中的深刻含义。
自从唐肃宗即位灵武,朝臣们自然分成了蜀郡、灵武两个集团。新旧两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房琯被罢相,首先因为遭到了新派人物贺兰进明的谗毁;张镐虽代琯为相,但此时相位也已岌岌可危。因为他“未尝降情结纳”那些得势的新贵,从而被这些人诋毁为“无经略之才”,使肃宗对他很不感兴趣。
杜甫在禁掖之中,深知这些情况,他很忧虑。因为一旦张镐再被罢相,下一个候选人就很可能是个灵武新贵。杜甫并非出自派性而反对灵武集团。
事实上,张镐,房琯等玄宗旧臣,虽不尽是张良、萧何式的人才,但多数作风比较正派,具有复兴国家、整顿纲纪的抱负。而靠滥封滥赏爬上来的灵武新贵,则多是投机取巧的小人,并怀有野心。
这种人上台,势必给“中兴”带来危害。因此,杜甫才有意抬高玄宗旧臣,并着重为张镐制造舆论,因为“琯已罢矣,犹望专用镐也”。
这个谏议当然更不会被肃宗采纳。没过两个月,张镐罢相,杜甫因与旧党亲善,随之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贾至、严武等其他蜀郡官员也接连贬出京师。正如钱谦益指出的:
“琯败师而罢,镐有功而亦罢,意不在乎功罪也”。

03 关心玄宗、肃宗、成王三代之间的关系,劝诫唐肃宗尽力弥合其矛盾
《洗兵马》诗中最尖锐也最含蓄的内容,是通过对李泌等人的描写,揭示皇上父子之间的矛盾。诗中写道:
“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
李泌于收京后“固辞还山”,是当时的一件大事,故此处“隐士”即指李泌是肯定的。李泌是肃宗朝真正的“张子房”式的人物,从马嵬坡分兵到收复两京,肃宗的每一个胜利,都和李泌分不开。但杜甫对他的丰功伟绩只字未谈,只提出他归隐一事,这其中大有文章。
李泌归山肃宗是有责任的。公元757年9月,李泌提出辞归时对肃宗说:
“臣有五不可留,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
这就明确表示他担心肃宗会像勾践那样杀功臣,并透出李辅国等企图加害于他的消息。这显然是对肃宗的试探。如果肃宗真像他说的那样:
“岂有如朕而办杀卿耶?”
他完全有力量为李泌创造条件,让他继续为相。“然奈何泌反复数百言,而肃宗终不喻耶。于是固请而必去矣”。
其实肃宗哪里是“不喻”,他这时从心里很希望李泌走开,因为李泌妨碍了他。李泌于肃宗朝有两大功劳:
“作群臣奉笺以迎上皇,使肃宗得上保其父……下保其子。”
而实际上这所谓两大功劳,正是肃宗必去李泌的原因。自从“玄武门之变”以来,唐朝几任皇帝几乎都不是按封建传统法制正常取得皇权的。后来是皇帝与太子之间矛盾重重。
玄宗时矛盾尤为尖锐。737年他黜杀太子瑛改立肃宗,肃宗在东宫时又“势几危者数矣”。安史之乱爆发,玄宗逃蜀,给肃宗造成夺权之机。
但玄宗并不甘心失掉皇位,他想利用房琯的诸王分制之策“以分太子之权”,使肃宗深感不安。李泌为肃宗“上保其父”,自然不会令肃宗高兴;另一方面,肃宗在得到皇位后,也开始嫉恨起太子。
尤其他看到李俶功高业大、百姓崇服,心中颇不舒服。于是犹疑反复,对李俶的封赏由楚王到成王迁移不定。李泌又“下保其子”,更使肃宗恼火。所以他才听任李泌归山。对这种宫廷秘史,杜甫只提归隐一事,让皇上自己去反省。
杜甫在《洗兵马》中这样话里有话地责备肃宗不止这一处。如说“成王功大心转小”,就是通过成王的谨慎来反映其内心的不安,据说李泌曾嘱李俶委曲顺之以保住地位;再如“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二句,也是“以颂寓规”,希望肃宗“昏定晨省”,克守子道。
但不久,玄宗就被软禁了起来,只是成王因善于韬晦,仍被立为太子,唐王朝最高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从此愈演愈烈。

04 批判攀龙附凤的小人,对唐肃宗的滥封滥赏进行讽谏
唐肃宗一心早成大功,不仅对外失策,对内也有许多不当。尤其突出的是他的滥封滥赏以及他的用人问题。757年4月,肃宗下令:
“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名器之滥,至是而极焉”。
收京后,此种情况更加严重。另外,唐肃宗还以降将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子七人皆除显官”;至于自我标榜为“拥戴元勋”的李辅国更是势倾朝野。当时,“人竞乘时以希高位,而不知所厌止”。
杜甫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对那些投机小人非常厌恶。因此,他在诗中尖锐地写道:
“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
杜甫认为,两京虽已收复,战乱并未平息,当前根本不是滥行封赏的时候,更何况在收复两京的过程中,这些攀附者没有立下丝毫的功劳。如此不加区别地封赏,势必会使功臣不贵、小人不贱,继而造成“贤者不为尽节,怨乃以生”的局面。
这不仅会使“中兴”之业功败垂成,还将使朝政趋于腐败。在这一点上,唐朝是有过深刻的教训的。安史之乱的爆发就和唐玄宗晚期滥封滥赏有关。在当时杜甫就说过“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并于《丽人行》等诗中一再抨击“请公衮衮登台省”,“炙手可热势绝伦”的现象。
此时,他害怕肃宗重蹈覆辙,所以他以夸张的手法,把滥封滥赏的局面写得十分严重,以图使皇上觉悟,刹住这一歪风,免得朝廷大权落在小人手里。
然而,肃宗当时已被一伙小人捧得飘飘然了,杜甫的这番逆耳之言根本不起作用。结果政权终于落在了李辅国等人手中,朝政日益腐败。
杜甫向皇上做了这四方面的“谏议”之后,于长诗结尾处,突然渲染了一番“祥瑞”气象:
“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
传说虞舜时,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又传说王者刑罚中时则银瓮出。杜甫用这类典故写时事,似乎是对肃宗朝的高度赞誉,可读起来却和前面的内容很不协调。
可不是吗?杜甫把一个存在着那么多问题的朝廷比作圣世,实在让人难以信服。而这正是杜甫的用意所在。
收京后,肃宗“颇好鬼神”。于是,当时各郡县官吏争相效仿,搞得一时乌烟瘴气。杜甫以为,一个明智的君主,即使胜利了也应安不忘危,何况目前尚有这么多的问题。这时候搞迷信谶讳,不仅是自欺欺人,而且能削弱斗志,给小人以可乘之机,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所以,他有意识地用前后矛盾的写法,让皇上自己去体会其中的劝谏意义。并且作为鲜明的对比,指出什么是当务之急:
“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这里,杜甫终于正面提出了劝谏的最终目的,希望皇上识别轻重、为民造福,早日实现真正的中兴。
杜甫在朝廷上下一片欢呼声中,能提出如此尖锐、深刻的谏议,实在难能可贵。特别是他在房琯事件后,处境已很不妙,而仍能不顾个人安危,以诗歌为谏议,更令人钦佩。
遗憾的是,他和他的“谏议”都以同样的悲剧命运告终,唐室“中兴”的幻想也最终破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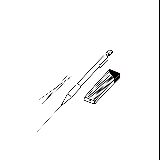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