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彩有三颗恒牙已经萌出,乳牙却还未掉。每次约看牙的时间都很头疼,需要同时满足几个因素:周六或周日、牙医有档期、彩彩有档期、我有档期。所以我很希望去了就能解决问题。
上周六终于约到了。
去的路上,彩彩不时问我:妈妈,不会拔牙吧?我不想拔牙。彩彩有过两次没给麻药被徒手拔牙的光荣历史,所以我将她的担心解读为“过口瘾,说着好玩儿”,只随口应付了她两句。
牙医检查后建议三颗都拔掉。
彩彩开始哭起来“妈妈,我不想拔牙,我怕”。
我一边在心里烦躁,一边安抚她:“你是担心疼吗?医生可以涂麻药”。
“不是,我就是不想拔。妈妈,我不拔牙!”越哭越厉害。
我只得放弃试图速战速决的心理:“这样吧,我们再聊聊”。
带她去到大厅里,我告诉她如果今天不拔,等开学了她的时间更不好安排,而且我也不一定有空陪她来,那个时候她想拔都不行。
她思考了一会儿,说:“妈妈,我就是不想拔”。
“你以前没打麻药都可以做到,今天医生可以涂麻药,不会疼的。”对于她今天这么抗拒拔牙,我不太理解。
“我觉得那个钳子冷冰冰的,伸进嘴巴里很不舒服,很可怕”她给出一个理由。
“可是你以前都不怕。”我并不打算接受。
“妈妈,我就是不想拔,我没有准备好。而且我好几颗牙齿都是自己掉的。”她想说服我不需要拔牙。
“刚才医生已经说了,你的恒牙已经长出来了好多,如果乳牙过几天还不掉,恒牙会长歪。如果是因为钳子的原因,我可以在拔牙的时候给你播放视频分散注意力。”来都来了,哪能轻易放弃。
不管怎样,她平静下来了,同意考虑一下。
过了一会儿,她告诉我,她很怕,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如果今天不拔,过几天牙齿还不掉,那个时候妈妈又约不到时间来处理。可是她今天真的很紧张,没准备好。
我摸摸她的手,果然凉凉的,这是人在紧张时会产生的生理反应。
我有点心软了。
可要是今天能拔了,多利索。或许我坚持下去,再给她做做思想工作,好说歹说不拔就不回家?
正纠结着,彩彩说话了:“妈妈,我想上厕所。你能陪我去吗?我想妈妈陪。”
忍着怒气,我亲了一下她的额头,对她说“妈妈爱你”,牵着她往洗手间走去。因为我知道她已然感知到我的情绪,这已经触及她的安全感,她提出这样的要求只是在求证:妈妈还是爱我的。
(备注:“‘妈妈’是爱我的,我不会被遗弃。”是个体最初安全感的来源,这个地方的“妈妈”是象征意义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类婴儿必须依附于他人才能存活,“妈妈”是照料TA,帮助TA抵御危险的那个人,因此,在儿童的潜意识里,如果“妈妈”不再爱TA,TA就会被遗弃,TA就无法继续生存。)
去洗手间的路上,彩彩模仿幼童的声音问我:“我们等会儿再聊聊,就算我还是不想拔,妈妈也不会生气是不是?”
(备注:模仿低龄孩子的声音说话,是一种明显的“退行”。一般个体在感受到危险和压力时,会采取这种防御机制。)
嗨,我都把她逼到这个份儿上了!
后来,我们再次进到诊室咨询是不是今天必须拔。牙医说最好今天拔,如果实在不拔,就回家自己再多摇一下,半个月以内没有掉就必须拔掉,不然会对恒牙生长造成很大影响。
就这样,我们回家了。
彩彩这个星期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摇三颗牙,而我也不得不做好还得再去一次牙科诊所的准备。
人最难战胜的是自己。这句话套用在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中一点不为过。
我们有我们的期待和计划,他们有他们的偏好和想法,两者难免冲突。无数次,多希望他们就顺着我们的来,那样会少许多麻烦,效率也更高啊。
静下心回想一下我们和孩子互动的种种场景,我们那么想要夺取到控制权,真的全都是为了“少些麻烦,效率更高”这些客观原因吗?是不是有些分歧,连孰优孰劣都谈不上,仅仅是各人有各人的偏好?有时候我们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是不是仅仅因为那样做心里感觉更舒服些?
孩子其实是一面照妖镜。我们试图控制住一些什么,是为了舒缓深藏于内心的些许恐慌、不安。这些恐慌和不安来自于哪里呢?或许恰恰是过往的“被控制”。是的,我们也曾被控制,至于工具嘛,或许是一条黄金棍,或许是一句厉声呵斥,或许是一个嫌恶的眼神,或许是“都是为你好”的情感绑架。是的,我们也曾经渴望有人能亲亲额头,说一声“妈妈爱你,不管你听不听我的话,妈妈都爱你”。我们的父母,甚至是父母的父母,又何尝不是呢。
要控制我们的控制欲,意味着放下虚伪,承认并不是真的全都是为了孩子好,有时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安全感需要而已。要控制我们的控制欲,意味着要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敌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回家路上,彩彩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感到生气?”我说:“是的,因为我的计划没有实现,受到挫折了,我觉得愤怒。而我需要时间处理,你暂时别跟我说话,等回到家里,妈妈的气应该就生完了。”
“好的,妈妈,那我自己听故事了,你继续生你的气吧。”
以前很多次,我没有做到,也许以后还会有很多次,我也做不到。不管怎样,这一次,我做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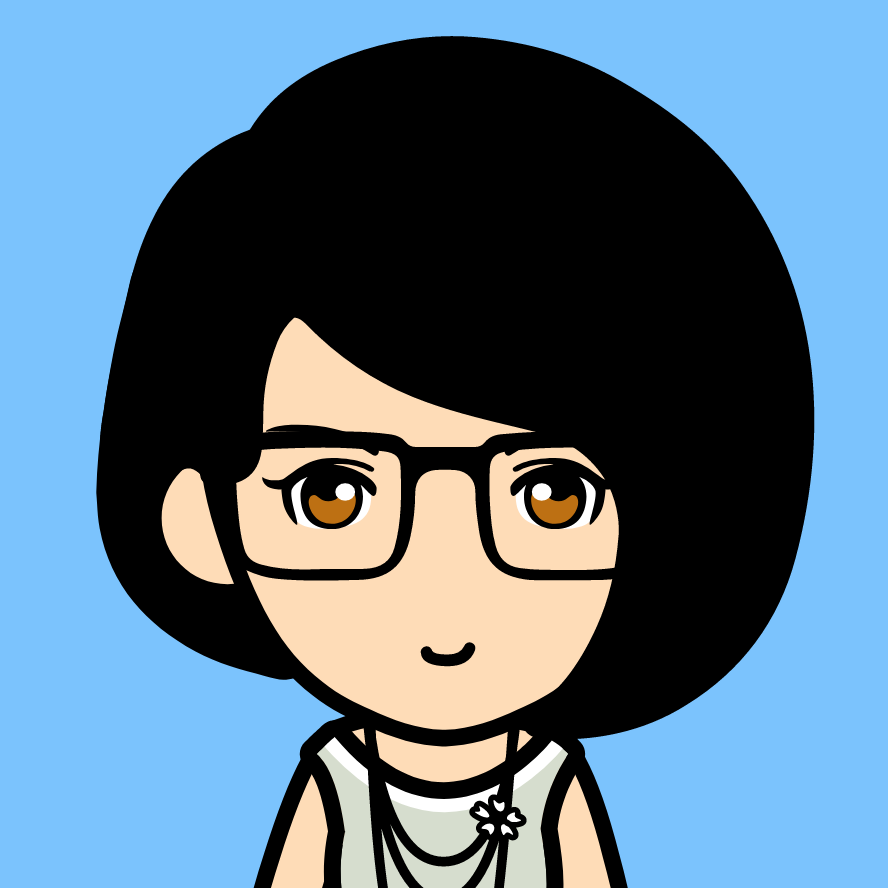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