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一块红布
马福礼来到剧院,他告诉在场的所有人,30年前,是一个面子比真相更重要的年代。
真相不再重要、名誉、灵魂、名字,自我,也都不再重要,它们都没有面子重要。
是的,面子最重要。
于是,所有人的焦点都是那红布背后被压抑的性欲,概念被偷换,扯下红布,居然成了解放天性。
可红布背后究竟是什么?
是不能放入正片的最后一个彩蛋,是不存在于叙事中的一场血雨,是马福礼背后,这三十年来的一片狼藉。
第二回:我的剧团早完了
马福礼找苟哥喝酒,苟哥喝的兴起,和剧场里的小年轻划清界限,愤懑的说:
那是他们的剧团,我的剧团早完了。
苟哥是性情中人,酒劲上来了,眼里容不得沙子,借着酒劲,唱着《奇袭白虎团》,把剧院里蝇营狗苟的先锋派,打的躺了一地:
痛歼敌人在今晚,绝不让美李匪帮一人逃窜。
教员曾说这部戏“声情并茂”,但就像在剧团呆了三十多年的老苟一样,早完了,不仅完了,唱这出戏的老苟,还要当众念检讨。
早完了,唱着“趁夜晚出奇兵突破防线,猛穿插巧迂回分割围歼”的老苟,成了话剧院看门苟;
对钱睁一只眼,对私生活闭一只眼的傅正团长,和大家把酒言欢。
第三回:跳楼会死,所以钻圈
生存还是毁灭,不是一个问题。
先锋派的陈建斌,曾自嘲:
其实我顶看不上那帮先锋派,在舞台上搞十个八个破电视,在舞台上放十个八个废纸盒子......分明是现实主义的功力不够,所以才来哗众取宠。
剧里警长对陈建斌饰演的疯子说:
不过我们这是排跳楼的戏,您看您是愿意现实一点从窗户跳呢,还是愿意先锋一点儿钻圈?
陈建斌走了几步,抑扬顿挫:
跳这边这个(窗户),那叫庸俗的现实主义,小名叫庸现,早就被我们扬弃了,我当然选择先锋派的钻圈了。
胡昆汀在众人眼皮底下和贾梅怡撇清关系,他对贾梅怡的感情放不上台面,或者在他一无所有前,他不敢放上台面。
现实主义下的爱恨,对胡昆汀而言就是“庸现”。
在胡昆汀一无所有前,他并不是为戏生存,而是为面子活着,逃避事实,自诩“先锋”的语境下活着。
生存还是毁灭,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单一选择题。
毁灭了,什么都没了,所以,一定要“活着”。
第四回:放弃幻想,实事求是
生是大梦一场,死是万物皆空,屁哥听别人说,要学会放下。
别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屁哥听别人说,要学会忍耐。
后来老爷子走了,屁哥不听别人说了,他说,要相信科学。
“死亡证明”出来前,屁哥是抱有幻想的,他信漫天神佛,他信佛祖基督。
东风也好,西风也罢,别人说什么能救老爷子,他就信什么,他是个孝子,一个想尽了各种方法救老爷子的孝子。
可老爷子终究还是走了,东风也好,西风也罢,别人说的话,都没有用。
屁哥的加长豪车里,再也没有各路神祇,有的只是蓝色的海洋球,他对马福礼说的那句:
豆花咸了就是没盐味。
老爷子真的走了,也走了很久了。
听别人说是没用的,要放弃幻想。
第五回:反抗虚无的瘸子
那是你的历史,你的历史怎么是虚无的,我们要斗争,我们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白律师总是义愤填膺的,他要马福礼反抗,和这世上的不公反抗。他和屁哥就是马福礼心中的两个魔鬼,提线着马福礼的一言一行。
是的,反抗,豪情万丈,可白律师让马福礼反抗的究竟是什么呢?
历史的虚无,被侮辱的名誉,众人“误解”的真相,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像点了肾上腺激素,亢奋了一夜又一夜。
可当翻案无望时,我们发现这个慷慨激昂的男人,是个瘸子,是个脚无法落地的瘸子。
喊口号很容易,实事求是很难,遇到挫折,百折不挠更难。
屁哥的和解,不代表就是妥协;白律师的愤懑,也不一定和当下有关。
第六回:小马就是枕头、枕头就是小马
马福礼和妻子金财铃参加了枕头大赛,主持人说这两口子太可乐了:
小马就是枕头,枕头就是小马。
但对两口子来讲,这有什么可乐的呢?
为了保护女儿,只能用这个办法。没人在乎枕头是不是小马,也只有自己在乎,小马又变成了枕头。
大家都说“小马就是枕头,枕头就是小马”,可对于这两口子而言,枕头就是枕头,小马就是小马,小马不能和枕头是一回事。
十年前,也有人说过类似话:
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
说这话的人,和陈建斌一样,骨子里都在反抗,小马就是小马,枕头就是枕头,浦东就是浦东,上海就是上海。
第七回:大梦不曾变
陈建斌老师说窦靖童是天才,陈老师说的对,窦靖童是天才。
和周迅、陈建斌搭戏,窦靖童应该是“最弱”的那个支点,但是她的叛逆气,给了她喘息的空间,云霄飞车上的表情转化,夜里颤抖的手指,每一个细节,如灵魂触电。
《第十一回》很偏爱近景镜头或特写镜头,窦靖童撑的住,也撑的好,骨子里的硬气,让整部电影变得嗟吁。
金财铃生金多多时,男方跑了,金财领把女儿抚养长大。
金多多怀孕了,有妻有子的男方劝金多多把孩子打掉。
这是两代人的一场噩梦,梦的模样可以变化,但引起噩梦的,从未改变。
这个孩子很重要吗?
为什么他就不认为这个孩子很重要?
这是我的孩子,难道不是他的孩子吗?
被抛弃的人,能有多重要呢。
第八回:透明、折射、反光、碎片
《第十一回》中有很多的镜子、电视,陈建斌老师在采访时大致说道:
这像很多记忆,又像很多的人格,碎片化里折射着每个人。
马福礼有没有杀人,没人关心,这是铁案;马福礼为什么杀人,也没有人关心,红布下的苟且之事,才是众人的兴趣所在。
记忆反倒变得不再重要,本就透明的事物,因此愈发的晦涩。
是旁观者的不作为,让主体的自我开始模糊起来,是旁观者的冷漠,让记忆失去了温度。
马福礼的荒诞故事,保全的到底是他的面子,还是偷情者的面子。
这本就重要的一切,被冷漠的大多数,封存于时间,时间,让它变得“不重要”起来。
记忆的每一次折射,都会发散,无数发散的记忆交错,形成了新的记忆,“这对狗男女”不一定是真的,“车滑坡了”,不一定是假的,这是一个人的《罗生门》。
第九回:冒犯观众
我冒犯了强者的什么权利?我冒犯了虔敬的什么要求?我冒犯了无视规则者的人的什么规则?
这是彼得·汉得克《冒犯观众》(骂观众)里的台词,也是《第十一回》里胡昆汀拳锤窗户,对老苟发出的狠话。
在《冒犯观众》里,我们看不到斯系的“第四堵墙理论”,梅耶荷德的“假定性”,大众熟知的“三一律”,有的只是舞台下,一个个被痛骂的观众。
《第十一回》里,观众也被痛骂。
当胡昆汀用刺眼的白手电,刺激一个个台下观众的眼睛,假装寻找着什么时,他所做的,和冒犯观众,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他开始“审判观众了”,审判着没有温度的看客,审判着当年的缄口不言,审判着今日的低头不语。
第十回:体温
《第十一回》里看似“痴狂”的人有很多,但化为戏痴的,只有贾梅怡
一个人。
她在满是先锋派的话剧团里,做了一件极其“庸现”的事。
她拉回了当年的拖拉机,把胡昆汀带到了当年的“案发现场”。
拖拉机下刻着那张渗血的结婚证,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这是令人苦笑的荒诞,我们摒弃的庸俗的现实主义,可为了探寻历史的真相,只能在庸现里寻找答案。
我们活成了一个笑话,马福礼这三十年,胡昆汀的这场戏,都成了一个笑话,一个在臆想里,离真相越走越远的笑话。
可活成笑话,并不意味着过的并不幸福。
人世间最大荒诞莫过于此,真相不重要,活成笑话也不重要,过的幸福,才重要。
第十一回:一块红布
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参考
^影片的故事背景是2019年,30年前,即1979年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
^《一块红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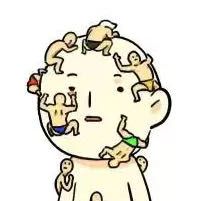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