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每一份礼物,都暗自标好了代价
《超级的我》是一个关于欲望和梦,“自我”和“超我”抗争的故事。 当一切都来的太容易时,人不一定会道德滑坡, 但他一定会为此支付代价,未经审视的天降之物,打开才发现,原来它的名字叫“潘多拉”。
所以,整部《超级的我》有两个逻辑,一个是表层逻辑:
关于王大陆饰演的桑榆,如何被机械降神眷顾,然后又为其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桑榆是一个穷困的编剧,有着再潦倒也不放弃编剧梦的傲骨。 梦里总有人追杀他,他无法反抗,每次在梦中被杀,方能惊醒。
直到有人告诉他,如果梦里有人追杀,你就喊“我在做梦”,便能从梦中苏醒。
桑榆照做了,他逃脱了梦魇的追杀,并从梦里顺走了宝物。 对于这个在梦里被杀疯了的人来讲,没有比现在更好的结果,逃离噩梦的同时,还能发家致富。
这是一段非常奇幻的创作,梦中取物成为桑榆,变成“有为青年”的路径依赖。 在导演张翀的创作下,这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让观众早有预期的感受到伏笔的存在。
这一切来的都太快,以致于财富变成了《超级的我》中最廉价的事物。 我们可以把这一段理解为世界观被改变后,金钱迅速贬值。
与之相对的,就是爱情、友情、亲情等情感需求的价格迅速拉高。 电影中的桑榆,为了获得这些情感需求,不得不为此付出更为昂贵的代价。
花儿,是桑榆的朱砂痣,也是白月光,她比桑榆稍长几岁, 开着一家没有多少客人的咖啡店。成为“有为青年”后桑榆追求她, 但因为年龄、性格等关系,两人若近若离。
而当花儿愿意接受桑榆时,桑榆却遭到了梦的反噬,梦里的创伤, 渐渐渗入桑榆肌肤,他开始逃离花儿,犹犹豫豫,这是他盗梦的代价。
这是爱情的代价,不疾不徐,来的刚刚好。
三哥,是在桑榆潦倒时,还希望桑榆坚持编剧梦的男人。 桑榆成为“有为青年”后,三哥很快便折服在桑榆的大腿下。
从此开始,三哥的味道发生了变化,除了那句“建一座全世界穷人都能居住, 管吃管喝的塔”以外,在金钱和欲望的折服下,他丧失了自己最开始的决断力。
他将拥有“梦里取物”能力的桑榆当做神的使者来看待, 二人不再平等,原先的朋友之言,变成了崇敬者对神的膜拜。 以致于桑榆被绑架后,三哥赎人路上判断失误,孤身前往,一同被擒去。
这是友情的代价,不疾不徐,也来的刚刚好。
张翀导演的《超级的我》先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代价”的故事, 这故事很简单,通俗易懂,即使缠绕了一圈奇幻色彩,也能让读者看到这部电影的明色。
但张翀导演,可能在《超级的我》中更想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欲望和梦, “自我”和“超我”抗争的故事。
在电影中,桑榆的每一次“梦中取物”都会遇到山羊造型的摆件。 有山羊为柄的剑,亦或是挂在死人腰上的金腰带,此类暗示,在电影中还有很多。
山羊的存在,是一件非常西方元素的事。山羊在西方本就恶魔化身之意。 比如巴弗灭,便是基督教恶魔之一,今日最为人所熟知的羊头恶魔。
这个恶魔长着一个羚羊的头颅,人类的身躯、鹿一样的下半身,双脚是山羊的蹄子, 而且它还有一根蝎子的尾巴,在蝎子地毒钩顶端则燃烧着一团绿色的火苗。
在西方流传的恶魔中,巴弗灭是最特殊的一个恶魔,他几乎是所有恶魔的综合体, 甚至被世人称为第二原罪。
但在《超级的我》中,“山羊”传递的是欲望。
所以这也就有了《超级的我》的第二个逻辑,里层逻辑,也是整部电影的“底色”:
梦里追杀桑榆的,是桑榆的“超我”;盗取梦中宝物的, 是桑榆的“自我”,二者相互的预警,产生了欲望的交错。
桑榆“自我”对梦的每一次偷盗,实际上都是一种对财富的路径依赖, 放弃的实事求是本身,也是对桑榆“超我”尊严的一种冒犯。
放弃的实事求是本身,也是对桑榆“超我”尊严的一种冒犯。
哪怕桑榆是因为生活客观窘困,产生了初心动摇,梦魇也不会以这些客观原因进行转移。
因为梦魇里的“超我”在守护着桑榆,他以各种方式对桑榆进行预警, 但“自我”困局下的桑榆,随着欲望的不断下沉,对“超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冲击。
后来当桑榆选择放下时,“超我”机制对自己的反噬,伤口逐渐爬满全身。 他开始选择和解,可这欲望作祟后代价,无法躲避。
这也就有了在欲望和人格斗争后人格醒悟,“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于是乎,桑榆的“自我”和“超我”在电影中有没有和解, 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万事万物,并不是只有和解了,才一定好。 但可以肯定的是,《超级的我》是一部寓言色彩极其浓厚的电影:
那时我们还太年轻,不知道生命中的每一份礼物,都暗自标好了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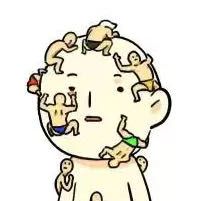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