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敦煌的佛教艺术源自印度。就莫高窟而言,留存下来的约 10 个朝代的艺术,不仅有印度艺术的成分,而且呈现了中国艺术在这里形成和演变的过程。
一
印度线法与中国线法相融合的早期艺术
印度佛教和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后,在南北朝时期迅速蓬勃兴起,经历过秦汉鼎盛时期的汉民族文化,一时之间受到了佛教艺术的巨大冲击。敦煌莫高窟大概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
据考证,莫高窟最早为公元 366 年开凿。从莫高窟北魏第 254 窟的弥勒佛塑像(图 1—1)可以看出,汉民族艺术家对外来艺术的表现形式感到某种压抑和无所适从,只能一味模仿,形象及服饰大多仿照印度的样式,“依样画葫芦”的塑像与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的装饰线法塑造(图 1—2)一模一样。尽管如此,中国艺术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艺术语言,率先在绘画上改变了印度艺术的线法,将其融入了汉民族绘画语言,并获得了成功。


印度绘画中的线法是装饰线法,即以形为主、线为辅的造型方法,其晕染与西洋绘画中形体的明暗塑造相似。(图 1—3)晕染不仅依形体块面而染,而且还有浓淡渐变的层次。但印度绘画中的明暗表现又不似西洋绘画那般明显和重要,所以必须用线条加以辅助来表现形体,线只能服从于形体,本身无法独立表现情感。而莫高窟早期开凿的北凉第 275 窟壁画中的人物造型,身上(手指、胸、脸部等处)的细线画法虽然也是模仿印度的线法,但这些细线都是用中国毛笔画出的具有丰富情感的线条。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人物身上沿 形体细线而画的粗黑线(原为淡红色,由于当时的红色颜料中含有铅,经氧化而变黑),是一道晕染线。它完全不像印度绘画是块面的晕染,而是变成了一道线,一道用中国毛笔画成的线。(图 1—4)用笔起止洒脱,行笔粗犷有力,充满了中国绘画线条的情感。莫高窟早期艺术中也曾出现过类似印度的装饰线法,但面积很小,仅在北魏第254 窟南壁的《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中的三位太子身上出现,线条硬而细如发丝,凭肉眼才能在原画中看见,这可能是使用从印度引入的工具画的。汉民族画家无法接受这种画法,所以在同一幅画中改用较粗的中国线法来勾勒。印度装饰线法在之后的壁画中也未曾出现过。


由于印度线法和晕染改为中国线法的成功,这种表现方法一时间充满于莫高窟早期的壁画艺术之中。然而,早期的艺术家们并没有感到满足,因为在这些形体的塑造中,虽然用中国的毛笔画出了带情感的细线,但形体上的细线仍受装饰线影响,线的表现受到压抑。而且画完形体细线之后,还要再画一道晕染线,这对汉民族的“线即是形,形即是线”的艺术审美来说显得繁琐累赘。
到了西魏时期的莫高窟,出现了用土红线造型的线法,在此以前也曾出现过土红线,但仅作为起稿之用。莫高窟西魏第 249 窟窟顶北披下方狩猎图中的野牛(图 1—5),全用土红线造型,不设色,笔法写意流畅,富有变化,造型生动逼真,可以看出作者当时是一气呵成。毫无疑问,这完全是汉晋时期画像砖(图 1— 6)的绘画线法和造型,画者在这里用汉代线法做最初的探索。另外该窟的一些树干树叶的画法也采用了汉代绘画的笔法,都采用画像砖上常用的土红线来勾画。汉代线法的运用,使西魏以后的线法和画面有了大的变化:造型线条多用土红线,一次勾勒成形;线条转向粗壮并追求书写的变化;画面底色大都采用白色,使土红线和色彩高度明朗。这种背景设色的画面也是汉民族喜爱的一种表现形式,第 249、285 等窟中也能看到(见前图 1—5)。


西魏时期的绘画,在用土红线勾完形体之后,设色加彩,最后根据画面的需要,用墨线勾点眼睛或衣纹,或提神,或醒线。这一种画法与前朝明显不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晕染的人物造型,类似汉代以前的“素面”人物画,同时,出现了一种不同于前朝的新的晕染形式。
在西魏以前人物晕染是依形体的低处而染,高处不染,即“染低不染高”的“低染法”,画史上有人称之为“凹凸法”(见前图 1—4)。新晕染法正好相反,只染高处,不染低处,在人的颧骨、上眼睑、额角、下颌等高处染一块淡红色,这种新的染法称为“染高不染低”的“高染法”。
这一时期往往以上三种染法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之中,说明艺术家们审美心理的不定,也看到艺术家们在做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这种不晕染的“素面”(见前图 1—6)和“染高不染低”的晕染都符合汉民族的审美习惯,在酒泉丁家闸五号墓出土的十六国时期的西王母像,脸上颧骨高处就出现“高染”的红色晕染。另外,在西魏时期的人物形象和服饰上,出现了不少汉民族形象及当时汉地的服装。(图 1—7)尽管它与外来的形式混合表现,但仍说明了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正在努力地向着汉民族的审美回归。

二
北周时期中国线法的形成
西魏时期,艺术家们利用土红线造型摆脱了印度式的装饰线和晕染线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使中国线法有了新的表现,但由于没有摆脱前朝色彩的约束,使得土红色的造型线条受到新的困扰。因为艳丽的色块覆盖在土红线上,加上色彩多得“面面俱到”,使得土红线处于次要的地位。
在中国绘画中,线表现一切,线的表现应该排在首位。艺术家们心中的渴望和追求,终于在北周时期的艺术中实现了。特别是北周第290、296 等窟的绘画,作者仍采用土红线造型,大胆地舍去了许多形体上的色彩,留出了线的表现。(图 1—8)线在这里表现得激越而舒坦,无拘无束地展现了线的艺术世界。这些线起笔时藏锋稳健,行笔时中锋敦厚有力,收笔回势明显,线条肥壮,首尾粗细统一。这种“笨拙”的线法与汉字大篆的书写笔法是一致的。线在这里不仅完成了对形体的塑造,而且体现了线本身的情感。

为了体现线,会留出大量的形体“空白”不设色,即使设色也是根据画面需要来铺置,甚至这些形体上的色块几乎都画成了抽象的色彩符号。用线来联结这些色彩符号,使宁静的色块与有运动方向和情感的线形成对比。所以,尽管色块艳丽浓重,线造型仍不失主导地位。这是艺术家对整体创造的高度把握。由于色块的减少,线条肩负起表现形体体积和空间的任务。
形体由于线的张力充分地显现了重量感,线也表现了塑造块面的能力,如第 290 窟佛传故事中的 3 个菩萨(图 1—9),脸上、身上及四肢的肤色的用笔,都是由线的符号组成(原为淡红色,现因氧化变黑)。这不仅完成了色块的塑造,又表现了体积的厚度。这时的人物形象也采用了“染高不染低”的晕染法,在脸部、身上及手脚的高处都一一晕染(亦因氧化变黑)。这些晕染用笔随意,挥洒而过,与其说是晕染,不如说它是笔、是线。

为了用线来表现空间,画者在勾完第一遍土红线后,刷上一层白底色,然后再用土红线勾画。后一次勾的土红线是根据整体需要来画的,有的交错进行,有的保留底层线不重勾。刷过白粉底色的土红线与后勾的土红线自然形成了浓淡两个层次,从而巧妙地塑造了体积空间,这种“线加线”表现空间的方法实在令人叫绝。特别是用这种方法表现的树木丛林,线条远近交错有致,无限的空间层次铺展。线在这里演奏着“二重唱”。
北周第 290、296 窟出现了中国画史上少有的艺术“减法”,即把不需要或不协调的线条用白粉覆盖,从而更加突出线的表现。这为线造型的中国绘画开辟了新的表现方法。绘画艺术的“减法”,在西洋绘画中常有,但因为中国绘画材料的性能不同,很少有人用到这种“减法”。
在北周第 290、296 等窟中,为了突出人物或动作,或由于线条过密等阻碍了视觉的整体表现,画者用白粉大胆地对许多线条作删除或减弱的处理。如佛传故事画中这个披着大袍的骑者(见前图 1—8),由于大袍袖管同时出现了四条平行线,显得平板无生气,所以,画者用白粉将四条线作了减弱处理,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块面。如北周第 290 窟佛传故事画中的这片树林(图 1—10),树枝交叉处线条过密,画者用了一笔白粉盖去,树林显得朦胧幽远。这里有许多人物的双脚也用白粉盖去,使腿以上的形体变成了装饰画面的抽象符号。把人物当作装饰景物来画,这种具有现代绘画构成的意识令人惊叹。

北周时期第 290、296 等窟的艺术,不仅为佛教艺术中的中国线法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为后来者展现了中国线法表现体积、空间、色彩等的能力。线条表现了自身,在画面中既有独立性,又有整体的统一性。这种汉民族审美意识的省悟,使得莫高窟艺术从此大踏步地走向中国绘画风格。这并不是说北周时期复制了汉时期的艺术,而是经过了北凉、北魏、西魏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探索,从形象、线条、色彩等方面走出了一条适应佛教艺术的新道路。特别是色彩方面,将外来的佛教艺术色彩巧妙地结合并统一在中国线法之下,这一点对后来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影响。
北周第 290、296 窟的艺术,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线法,引起了同时代艺术家的共鸣,莫高窟这时期出现了许多近似的表现方法(北周时期也有少量前朝画风),如第 299、301、428 窟以及北周末期隋代初期的第 302、303 等窟(图 1—11),特别是第 302、303 等窟,仍沿用了第 290 窟勾完土红线后再刷上白粉底色,塑造双层线的方法。莫高窟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呈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

三
隋唐时期中国线法表现的鼎盛
北周第 290、296 窟形成的中国线法,不仅影响了同时代,而且深深地影响着之后的艺术。到了隋代,这种线法的表现形式得到了较普遍的发展。隋代艺术家彻悟到中国线法表现的要领,开始用北周第 290 窟的造型方法,创作出真人大小的菩萨形象(北周第 290 窟的人物很小,仅约 15 cm 高)。隋代的第 276 等窟出现了真人大小比例的壁画(图 1—12),也采用土红线造型,线条粗而长,挺拔有力,人体肌肉部分施以白粉,衣带设色也更多留出线的表现,保持了以线为主的造型特色。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类似表现手法的壁画艺术,如第298、313、314、394 等窟。

但由于这种线法造型的画面色彩偏少,于是隋代又出现了一部分画家,试图将北周以前的色彩结合到这种线法上来。他们仍然用土红线造型,并用北周形成的粗壮有力的中国线法,设色明显增多,如莫高窟第 305、390、397、402、419 等窟。(图 1—13)尽管这些洞窟的色彩已经达到了无比瑰丽的程度,但土红线的表现如同西魏时期一样,再次被色彩淹没了。这种历史的反复在艺术创造中是常有的事。

怎样才能让壁画既有情感丰富的线条,又有艳丽多彩的颜色,使线的表现立于色彩之上呢?唐代的艺术家们总结了前人的成功与不足,悟到了线与色二者之间的深机妙理,他们用改变造型线条的色彩和浓度的方法,使线与色的矛盾得到了突破性的解决。在唐代初期,艺术家首先改用浓重沉着的朱砂色勾勒造型线,朱砂色不仅厚重而且色泽亮丽,能在众多艳丽的色彩之间不失其色。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用浓墨线、淡墨线与朱砂线相结合,土红线与淡墨线相结合,以及淡墨线与浓墨线相结合等几种造型线法。不管哪一种线法,都是以在画面上突出线的表现为目的。这些线都是采用莫高窟北周第 290、296 窟形成的中国线法,线条粗壮肥美,用笔钝厚有力,所以在色块中仍能保持其情感表现。如莫高窟初唐时期的第 79、220 窟壁画,采用淡墨线起稿,后用朱砂线重勾,所以画面色彩虽然鲜艳繁杂,但仍不失线造型的主导地位。(图 1—14)又如初唐时期莫高窟第 57 窟北壁以墨线造型的绘画,都非常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线法表现的情感。(图 1—15)


中国线法在色彩上实现了突破,线已经远远不满足于形体轮廓线的表现范围,开始进入色块的表现。在唐代的画面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由色彩线条塑造的形体,如云彩、装饰纹样等,特别是一些璎珞首饰及莲花宝座,用好几种色线层层画出,塑造了一个彩色的形体。这种“线加线”的塑造方法,又比北周时期的表现更进了一步。唐代线法也如同北周时期一样,多用中锋行笔,笔法粗犷有力,圆润厚实,不同的是,唐代线法收笔多为渐收之势,显得挺拔犀利,不似北周的“即止即收”的大篆钝厚收笔法。(图 1—16)

另外,唐代线法出现了多种变化的形式,有的线条起笔处很细,采用“空中落笔”的书写笔法画成,有的线条两头细中间粗,人称“兰叶描”,多用于画眉、眼、衣纹的线条……(图 1—17)

唐代线法在画面上的制作极其严谨,一般采用画两遍的方法,第一遍用较淡的线作为起稿的造型线,第二遍用较浓的线,但并不是“面面俱到”,是以画面的需要为原则。在唐代,艺术家往往喜欢用朱砂或土红线重勾表现人体肌肤的线,用浓墨线重勾衣纹线,使画面色彩产生更丰富的变化。这种将线分成浓、淡两遍来画的线法,与北周第290 等窟将土红线刷过白粉后又勾土红线的方法和表现意图是一致的。唐代线法对色彩的主宰,色彩对线的服从和统一,使线与色二者之间均可无拘无束地尽情发挥和表现,从而造就了唐代艺术的辉煌和伟大,使中国线法和色彩的表现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艺术高峰。(图 1—18)

唐代艺术的强盛,并不是单一的、不变的表现形式,而是在不断创新、不断变化、不断追求新的表现形式下展现时代风貌。正当唐代绘画的线法和色彩表现登峰造极时,另一部分画家又试图打破这种完美,从另一个角度寻找新的艺术出路,如以莫高窟盛唐时期第 103 窟壁画作者为首的一批画家。(图 1—19)

莫高窟第 103 窟东壁的维摩诘经变画和北侧文殊菩萨等人物画,大都是以单独的墨色线来表现,颜色用得极少。这对当时色彩富丽的唐代壁画艺术而言似有“格格不入”之感。从造型线条及布局等功力来看,这些壁画应出自当时的一位绘画高手。他也许窥视到单纯的墨线可以表现一切的意境,性能活泼的水墨是记载情感的最好颜料,因此在这里作一种试探性的表现。
这里的线法仍与唐代的双层线法相似,即第一遍用淡墨线起稿,第二遍用较浓重的墨线重勾或作点醒提神之笔,但这第二遍线是用带写意的笔法画成。如图中维摩诘额角上的线法,是用笔的侧势依形体起伏转折随意写成。由于笔法奔放洒脱,出现了“飞白”的书写效果,这个维摩诘的额角的线看上去“断”了两处,但气势连贯,加上底层还有一层淡淡的墨线,所以形体显得十分浑厚。而且作者已开始领悟“笔”在画面上的功能,如维摩诘(见前图 1—19)右肩的一条长线,依靠笔的功能,画出由笔产生的“抑、扬、顿、挫”的变化线条。“笔即是线,线即是笔”的审美意识,为后来的水墨画大为推崇。
唐代第 103 窟的线开始注意到“水”在墨中的作用,即利用毛笔中水分的多少,画出有浓淡变化的线条。该画中第二遍线是用笔尖处浓、笔肚中淡的笔法勾勒的线。从线条起笔处的积水和外渗的程度,可见笔中的水分饱满。另外从维摩诘腰带上的墨点浓淡渐变的节奏,也可以看出笔中的水分含量比较高。所以,这幅画虽为线描,仍令人感到水汽淋漓。
之前的绘画在一笔画出的线中大都不求浓淡变化。不管是色线或墨线,一般都先调好色或墨后统一勾勒,勾淡线时不蘸浓墨或水,线的首尾浓淡差不多,只有粗细或干枯之分,一笔之中出现浓淡变化的很少。第 103 窟作者用水墨线法组织了这个色调高雅、形象生动、令人耳目一新的画面。它的成功,无疑吸引了同时代画家的目光,许多洞窟画中的线条开始追求浓淡变化。如莫高窟第 444 窟西龛的比丘头像(图 1—20),利用线的浓淡轻重表现了形体骨骼的起伏变化。还有莫高窟盛唐时期的第 45 窟南壁观音普门品画、中唐时期的第 225 窟东壁下方的女供养人(图 1—21),以及第 9 窟中心柱西面向的白描画中的线条(图 1—22),都明显地追求线条本身的浓淡变化效果。第 9 窟的人物画,已经很熟练地画出了毛笔在运转中自然产生的粗细变化的线,“笔”在线中体现得很充分,展示了单纯水墨线法表现一切的能力,进入一个水墨画的世界。



莫高窟第 103 等窟的绘画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为唐代辉煌的艺术增添了一朵奇葩,而且为后来的水墨画艺术的兴起提前打开了一道艺术之门。
四
宋元时期线法的发展
唐代绘画在线和色彩上表现的绝顶高峰,使得唐以后的画家有点“日暮途穷”之感,但他们很快从唐代绘画中萌芽的以单纯墨线为表现手法的形式中看到光明,在宋代形成并兴起了文人水墨画,为中国绘画开辟了另一条新的艺术道路。
也许由于水墨画多用纸、绢作画,水墨画在中原地区的兴盛,对于五代、宋朝前后的莫高窟壁画艺术影响不大。这一时期的洞窟绘画仍运用唐代线与色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但也出现了一些艺术变革,比如用土红线再次勾成形体线,色彩做许多减法,不过都没有冲破前人的樊篱。这一时期的山水画中的线法有了新的进展,线法依形而用“笔”画出山的形体转折,线条有粗细、浓淡等各种变化,特别是利用笔的顿挫画出了山形坚硬锐利之感。(图 1—23)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皴染形体的笔法。

到元代,水墨画的线法及其表现形式才正式影响到莫高窟。如莫高窟第 3 窟以及榆林窟第 3 窟等以墨线为主的表现形式。这时的线条与唐代第 103 窟维摩诘的线法有许多共同之处,如线条用墨来勾勒,用色比较简单,线条采用两遍画成的方法。但这时的线法更注意浓淡变化和转折的停顿,使形体的转折处线条变化多端,特别是衣服飘带与饰品的画法,不仅有粗细起伏的用笔变化,而且非常注意线条在物体的前后空间以及主次的表现,即近处物体的线条用笔都比较浓重粗大,次要的及远处的线条比较淡而细。(图 1—24)另外,不管浓线还是淡线,笔中的水分都大大地增加了,线的浓淡变化更为生动自如。

与此同时,在壁画中又出现了另一种造型线法,该线法仍以墨色勾成,且多用较浓的墨,线条不求浓淡的变化。这一点与唐代早期线法相似,但特别强调起笔的效果,起笔以侧取势,锋转停顿后,转中锋行笔,收笔作渐提收势,力送尾部,不留明显回锋之势,有明显的“钉头鼠尾”的效果。这种线条挺拔有力,造型严谨,布局匀称工整,疏密穿插自然贴合。以上两种线法造型都已不太注重色彩,而是保持墨色清淡高雅的画面,线完全走向独立表现不错的水墨线法世界。这两种线法一直沿用到今天的绘画之中。(图 1—25、图1—26)


元代的敦煌艺术中还有一种线法,这是一直受到印度佛教后期艺术影响的西藏佛教密宗艺术。密宗艺术传入敦煌地区后,汉地画家采取了两种表现手法:一种是如上述的莫高窟第 3 窟的画中,用中原的水墨线法造型;另一种就是保持了印度《佛说造像量度经》的造型规则的壁画艺术,线法用一种极其工整而细小的墨线来造型(图 1—27),线与线之间交接严谨,许多形体都是用无数的线表现构成。尽管这些线条极细,但仍不是印度式装饰线法,线仍然承担着表现形体的重任,同时也注重线的情感表现。这是汉地画家把西藏艺术融入中原绘画所产生的一种风格。这种带有外来成分的表现形式也许不合汉民族的审美习惯,所以并没有流传下来,只有西藏的唐卡艺术保留至今。元代艺术虽然是莫高窟约十个朝代艺术中的最后一个,但它在中国线法的追求和发展中作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为莫高窟艺术绽放了最后一道耀眼的光芒。

敦煌艺术展现了古代艺术家们对艺术追求的探索和付出的艰辛努力,以及孜孜不倦地对自己民族艺术审美的追求。不管是对外来艺术的吸收或融合,还是对艺术本身的创新和变革,他们始终让民族特有的精神之魂—汉字书法和绘画共有的具有丰富情感表现的中国线法,时时处处地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每当中国绘画大变革时,艺术家们都会首先放弃色彩或形体表现,突出线的表现,在线得到充分完美表现之后,才进入其他表现内容。莫高窟北周时期与盛唐时期第103 窟以及宋代水墨画,始终把线放在表现的第一位。由于中国线法的重要和表现的特性,宋代的艺术家最终悟到了中国线法可以表现一切的天机,创造了文人水墨画(图 1—28)。经过元、明时期的发展(图 1—29),特别是明代中期至清代初期水墨画的突破,中国线法在水墨画的表现上又出现了一个绝顶的艺术高峰,经久未衰。然而,时代在前进,艺术更需要不断创新,对古代艺术的了解,是否对我们今天的水墨画创新和突破有所帮助或启示呢?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作者以自述的方式带领我们逆时光长河而上,走进敦煌这一艺术宝库。敦煌艺术历经一千多年连绵不断的发展,特别在唐宋时期,其圆融、飞跃的状态,奠定了汉民族艺术审美体系的成熟自信、博大包容。
敦煌壁画之中,线与色交融,流光溢彩;敦煌雕塑与建筑,乃空中妙有的艺术塑造。透过它们的璀璨光芒,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中国各个朝代艺术的传承和演变的脉络。特别是散落海外的艺术明珠——敦煌藏经洞绢画,更是让我们理清了中国卷轴画、唐卡艺术发展的源头。
在有“石窟艺术奇葩”之称的莫高窟第290窟,我们更是可以看到敦煌相当精美的佛传故事连环画。那种同声同气、同频同振的心声,让我们能直接感受到远古人们对艺术、对信仰的真诚。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凭借上苍赋予的灵性觑见了艺术的神韵,将毛笔书写象形文字的情感线条用于造型艺术,那是传递物体形神的非凡超越,让我们的心灵直接与先祖神灵产生艺术对话。

近 期 好 书
点击图片可查看详情
扫码或搜索ID:DungxingzheBook
添加【读行者微信小助手】
回复“入群”即可收到邀请
加入博集天卷读行者书友群
解锁更多资讯与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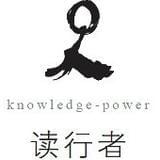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