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贝若洋
牙痛突如其来,纠缠整整一夜,破晓时稍稍平缓麻木。正午,头顶烈日,搭乘定时的小巴赶赴镇上的中心医院。嗅闻着气味,像认命的俘虏一般排着队:第七位,每名患者诊治约需二十分钟——时间无声的滴答被疼痛一下下刻记。女医师告知并非口腔溃疡(起先判断有误),是最深处的蛀牙发作了。无用的一颗,她说。意思是得拔除。丝毫不愿加以解释的专断口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何况她一副戴眼镜的女王模样。
挂号,诊断,付费,取药……这整套程序无法坚持。福特流水线是该诅咒的发明!脱离队伍,溜到附近的药店照方抓药(奥硝唑片,布洛芬缓释胶囊。这些都比较强劲,也戕害身体)。在一间小商铺(开着冷气)买瓶水,囫囵咽下药片后,耐心等候专线小巴,清凉中历数我的病史。沿途十来个站点,途经一顷瞩目的湾景。暴虐阳光下,大海的运动,“始终不渝地冲刷着同样的海岸”。
药效已过,下午爆疼继续。夜晚右眼珠爆凸整个左脸神经系统被这复辟的霸王所支配。 三十而立,欲远行,曾仔细诊治过一次——成年后仅有的一次。对医院的敌视是自觉的深深偏见。那之后,习惯性的疼痛,它的迅猛与暴虐似乎被抑制住了。阴影被扫到地毯下面。从幼年到成人,口腹之欲于我常如凶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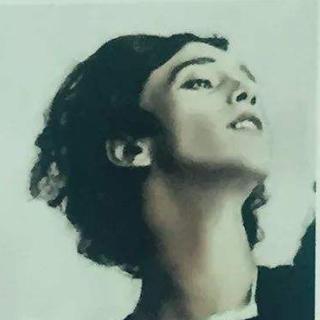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