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网易戏局栏目出品。
切齿梳:里弄离奇事三桩
前言
戏局新作者谢十三,带来发生在打浦桥新式里弄的几桩离奇事。
记录者是一个传奇小说作家(自称),姓曹。
第一场
1999年,春天,打浦桥新式里弄的一套四层小楼租了一个隔间出去,月租六百八十八块,需和上下两层的六户人家共用一个“灶劈间”,也即是厨房。厨房有两个灶,已经装了煤气,因此尽管使用面积一样,公摊部位大小相仿,房租却比隔壁楼还在用天然气的贵三十块钿。卫生间也是隔用,里面墙壁上原来钉着三四个塑料的篓子,用来装草纸,上面还要用红色的油漆笔各自写好各家的姓氏。
新租客姓曹,男,廿七八岁模样,个子很高、人精瘦,皮肤偏白,戴着当时很时兴的无框眼镜,看上去很有知识分子的派头。他来了之后表示不习惯用篓子和草纸,自己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个不锈钢的卷筒架子,像式像样地装好,又不吝于时时补充洁白柔软的卷筒草纸,避免了许多犄角旮旯里带着特殊气味的纷争,因此很受各家阿姆的喜欢,很快就被自来熟地称为小曹。
叫人意外的是,小曹是个写小说的,当旁人进一步询问的时候,他就会说:“我是写奇情小说的。”
没人知道奇情小说是个什么类型的小说——大家又一窝蜂地开始叫他曹作家。
曹作家(据他自己说)是来采风、体验生活的,他有一个夹板,上面永远夹着厚厚的、有凹槽横线的稿纸,用以记录日常听闻的、他所感兴趣的所有事。记录一般发生在中午、或者晚上,在声音嘈杂的灶劈间里。参与者众多,主要讲述的可能是一个,补充说明、或者在旁边加以纠正的另有几个。通常做一顿饭的时间过去,曹作家已能写满厚厚的几页纸。
而曹作家在隔间厨房里听完的第一个故事,是有关这栋楼里一个叫做张春燕的女人的。
他们都这样称呼她:那个女精神病。
第二场
张春燕,前租客,本地人,十四五岁响应国家号召插队落户至外省,在妇女卫生所工作,于当地结了婚又离了婚。伊是大专生,90年代初沪上人才引进,因她会教一些古文,得以迁籍回沪,开始在一个区重点高中里面教语文。
她回来的时候身边带着一个小孩,惊呆了父母、兄弟姊妹与朋友,在滇十年音信渺渺,只听闻她五六年前离婚的消息,竟不知道她曾经生育——是一个小女孩,当时大概两岁还是三岁。为了给非婚生的女儿上户口,张春燕跑了无数次派出所,到93年补缴完所有社会抚养费,小姑娘才算有了个正式的身份,正好赶上可以上职工幼儿园。
张春燕人长得漂亮,气质娴静,又是高中老师,虽然离异还有一个小孩,但还是很多人愿意给她介绍对象,却都被她以女儿还太小为理由拒绝了。又过了大概一年多,有个年轻又斯文的男人开始频频造访,他个子不高,人很瘦弱,总是戴一顶鸭舌帽,也不与旁人讲话。邻里听到小女孩叫男人“林老师”,猜测是幼儿园的某位教师,与张是同行。
后来,就在小姑娘开始上小学的那一年,张春燕把她的前夫砍了。
事发地不在打浦桥,而是在张工作的学校附近。那个男的也是知青,比张春燕晚了几年回沪,想要找张复婚,得知她离婚后几年居然多了一个女儿,并且有一个稳定的“男朋友”之后,那长眠许久、在别处也不怎么用得上的男性自尊突然觉醒,天天去她单位门口蹲守,写信给校领导,说她生活作风有问题。此人甚至还出具了一份证明,说张在云南的时候就罹患某种精神疾病。
男人来过里弄一次,整个过程歇斯底里,上一分钟跪在地上哭,下一分钟又跳起来骂,林老师闻讯前来劝架,争执过程中从木质楼梯上滚落下来,摔折了一条腿,自此不再出现。一切并没有结束,因为男人发起癫来真的潜力无穷,后一个礼拜他继续神通广大,一路跟到了张小女儿的小学门口,揪住那个一年级小姑娘的胳膊说,你知道吗?你妈她脑子不正常。
张春燕之前到底是不是精神病,谁也说不好,讲这件事的那个阿姆总结说:“她办那件事那么利落,你其实不好说她是精神病的,但兴许是办了之后疯的呢?你办了这种事,再说不是精神病,好像就说不过去了。”
张春燕具体办了什么事呢?她将前夫约到学校附近的招待所见面,声称要与他复合,十分配合地脱掉了身上所有的衣物(所有),以此成功地诱使对方喝下兑入大量安眠药的啤酒。在男人昏迷后,她取出藏在随身挎包里的管制刀具,开始实施犯罪。过程不可详述,但她完成一切后,将自己冲洗干净,然后穿上没有沾到一丝血迹的衣服,平静地离开了招待所。
民警是从课堂上带走她的,整个公诉过程相当困难,因为张春燕拒不开口,招待所没有监控,也没有相关目击证人,从流程上来说,没有疑犯口供便无法很快结案。同样影响案件进度的还有死者身上一个令人费解的伤口:除却大部分非致命的刀伤外,死者后颈部大动脉处有并排的五个孔洞,是用尖锐利器扎入的,等差距排列,令人毛骨悚然。
刀具已经于张春燕家找到,但造成齿孔型伤口的凶器,至今下落不明。
曹作家默不做声地听完,此时才问:“那张春燕最后定罪了吗?”
“不太清楚。”旁边一个邻居炒完一盘蒜蓉茄子,很熟练地装盘,“反正伊现在一直在宛平南路的普慈医院。”(曹作家不是本地人,后来听人说,那是本地的精神卫生中心。)
接下来的故事就比较简单,张春燕表现出较强的攻击性后,死者父母反而彻底偃旗息鼓,没有再为难张的父母与两个兄弟——很可能是怕张的精神病是遗传的。小姑娘被张的父母接走,之后都再没有回过打浦桥。
曹作家听故事只做记录,不发表任何评论。
第一个礼拜,他刚刚来的时候,在安装不锈钢滚轮轴前,曾对那个逼仄的、在各处角落蒙着一层厚重污渍的卫生间做过一次彻底的清扫。在抽水马桶左手边那个门轴都已经快烂掉的木头橱柜背后,他发现一把布满灰尘的梳子。
它很脏,造型笨拙,是铜制的,有着五个异常尖锐的齿梳,好像被人无数次摩挲、并打磨过一样。
第三场
隔间第二个故事里的主人公,至今还在里弄里拥有一套房票本,曾是沪上颇有名气的一个摄影师,姓梁。曹作家所租的套间,承租人就是老梁。他三十几岁,长相英俊,间或回到里弄里来,缴房费、或者拍几张照片。
曹作家与他见过一次。老梁看到人时基本不讲话,蹲在天井里、时间长久地看着一盆花。是那种土胎的花盆,非常重,很难挪动,原来架的是葡萄藤,后来因为爬类植物影响房屋结构,被房管所连根铲除。这会儿盆里种的大概是薄荷,因为照不见什么阳光,所以萎得厉害。
曹作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问你在看什么,他问,你要不要凳子?
老梁回过头来看他,眼珠子缓慢地转动,无法聚焦,嘴唇颤抖。隔了一会儿,忽然又直愣愣地盯着曹作家,说:“位子是我的。”
曹作家:“什么?”
老梁又重复讲了两次,并手舞足蹈起来,曹作家实在不解其意,看老梁家里的司机来接他,就走开了。
后来在隔间的闲谈里得知,老梁原本在机关任职,做宣传工作,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还会摄影。沪上各区有援建指标,老梁人年轻、登样,常被派去各地公差。他早先长袖善舞,很得领导、同事的喜欢,二十多岁科室里提拔科长,老梁觉得无论是讲资历还是看能力都应当轮到自己,可后来临门一脚,组织上从市里调来一个宣传科长,他没能当上这个科长。
得知这个消息的老梁回到家里,好几天没有睡觉、也不愿意吃饭,后来再开口,就只会木木楞楞地讲一句话,位子是我的。
说来也有意思,老梁当不上科长之后,运气反而好起来,不日便因皮相优越,脑子糊涂,被一个领导的女儿相中并闪婚,几个月后便有了第一个女儿。据闻他自此在单位获批长病假,得以常年不去上班,但几幅摄影作品却相继得奖,渐渐竟变得有名起来。
隔间里的阿姆们总结,可见一个人有没有精神病,与其本身精神状态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看他/她“最后变成个什么人”。
总体来说,老梁的故事未见有尖利的齿梳或死于谋杀的前任,实在算不上稀奇。曹作家照例未做评价,他住的就是老梁早先的房间,因此在见到老梁前,已通过房间里胡乱堆放的杂物对他有所了解。譬如老梁的摄影技术其实连入门都算不上,拍的崇圣寺与洱海都没有基本的准线与构图。但他拍的人像相对较好,曹作家在那一叠没有上色的照片里,找到一张镜头姿态尤其鲜活的,照的是个三四岁的小女孩,穿着绒线衫与灯芯绒的小裙子,捧着一块红宝石蛋糕,一派天真地看着镜头。照片的后面用圆珠笔写着:1994年3月19日,摄于邻居张小茜生日。
张小茜就是张春燕的那个女儿。
那堆杂物里还有数不清的私人信件,曹作家当然不会去翻看。他将照片归列整齐,放回那个蓝色的饼干筒内。他还注意到他有很多未寄出的信件,不曾写地址,只写了一个收件人,是一个叫连红的人。听名字,或许,这是个女人。
第四场
入夏的时候,曹作家收到一封信,信是带着邮戳、规规矩矩投入他信箱的,未曾写收件人,只写了他现在的地址。寄件地址是云南下关,寄件人叫娄晓芳。
曹作家不认得此人,因此当然也不便拆信,楼下阿姆看到他站在邮箱旁踟蹰,探头过来看了一眼,十分了然地叫他可以不用管。当天在隔间里,曹作家听完了这栋楼里,其他人都老早知晓的、有关娄晓芳“万里寻亲”的故事。
娄晓芳来找的是她的女儿,或者说,是她女儿带走的一笔钱。她大约是在93年末,张春燕与老梁都离开打浦桥之后几个月第一次出现,而早在那之前,她的信件已经被里弄堂里的人们熟知。
信是由人代笔,老太太因为笃定女儿曾住在这栋四层小楼中,但又不确切地知道是哪一个房间,因此孜孜不倦地给这栋楼里的每一个房间写信,信中阐述了老家的家人生活如何艰难,要求女儿不能独吞抚恤金,应当将这笔巨款交出来,重新进行分配。
由于谁也不曾回信,几个月后,老太太风尘仆仆地杀到,她瘦小而干瘪,像夜里栖息在树上的猫头鹰,会用阴鸷的目光死死地盯牢楼洞门口,看每一个进出的人。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不到女儿,她登堂入室,一家一家地敲门,甚至硬闯入别人的房间。居委为此报了警,民警将老太“请”出来的时候,老太还在恶狠狠地诅咒,信誓旦旦是有人故意将她的女儿藏了起来。在无数次的拉锯战中,在老太那如雷般的嗓门里,大家渐渐拼凑出一个相对完整(也可能是臆想)的故事来。
娄老太育有一子一女,女儿初中即辍学打工,儿子尚在读大学。娄老太的丈夫,据说“顽固、没有文化、且脾气暴躁”。有一天伊出门走亲戚,叫女儿早点下工去照顾老父,回家后见老头倒卧在女儿的梳妆台前,满头是血,身体已经凉了,应系酒醉后摔倒碰撞到桌面上的琐物,戳破大动脉所致。老太这辈子以儿子和丈夫为天,哭天抢地,痛骂女儿疏忽照顾,将其骂跑。再几个月后女儿回家,已经是大着肚子,问肚子里的孩子哪里来的,她也不说。当时孩子已经快要八个月,她被老太硬揪到卫生所做了流产手术。之后由老太做主,保了个媒,将其嫁给了当地一个五十多岁的装修工人。
新婚不到三个月,新婿被一根从天而降的钢筋砸中,死在了工地上,女儿拿了一笔抚恤金,没有多久说自己生了病,要去上海治病,自此杳无音信。
“生什么病?她的钱不是家里的钱?她弟弟要翻新房子,要养她弟媳和外甥,这笔钱她怎么能自己一个人用?你们谁见过这么凉薄的子女?”
有人提醒老太:“你女儿的钱未必就是你的钱,要等她死了,你才有处置这笔钱的权力。”
老太偏不信,她整天地坐在台阶上,在新里弄和派出所之间来回折腾,直到儿子打电话来骂她,问她知不知道请一个保姆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叫她赶紧滚回家带孙子。
娄老太走得很不情愿,她临走的时候恨恨地望着这栋外墙整洁、窗户明亮的建筑,满心仍以为她的那个很不安分的女儿隐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享有一笔巨款,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她没有再来,但仍不死心,隔三差五地会寄一些信来。居民将之当做骚扰,曹作家犹豫再三,最后拆了那封信,里面说宝贝小孙子就要上小学,需一笔择校费,并在结尾诅咒,如再不出现,那必定是要天打雷劈的。
曹作家不迷信,他将信重新装好,去楼下的公共电话亭给负责租房给他的中介打了个电话,说自己租约即日到期,这就要准备离开了。
第五场
曹作家搬离那日,有个小青年开着车来帮忙,他个子也挺高,古铜色的皮肤,穿着很时髦的皮夹克。伊物什不多,统共一个旅行箱,并一个老式的牛皮箱。两人坐到车里,小青年阿武递上一个文件夹,里面夹着三份文件。
曹作家默不作声接过来看,第一份是下关市某公安局的验尸报告,死者叫连卫国,死因是酗酒后跌倒,颈部被铜梳贯穿,其亲属栏里填写:妻 娄晓芳,女 连红,子 连勇。第二份是滇南某社区医院的员工档案,其中记录张春燕曾于1986年至1991年间,在妇产科任护士。第三份是一张医院病历的复印件,连红罹患子宫癌,已于3个月前去世。
阿武问:“都搞清楚了没?”
“大致已经比较清晰。”曹作家说,“张春燕本身并没有生育,她带回来的那个小女孩,其实是连红的孩子。这两个女人恐怕一直保持着联系,张春燕用来杀人又藏起来的那把梳子,很可能就是连红交给她的。张春燕带着孩子先来了上海,连红可能晚了几年。以她的学历,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很可能是在幼儿园做保育员或者清洁阿姨。小女孩说的‘林老师’压根不是个男人,其他人听错了,她叫的可能是,连老师。”
阿武发动了车:“这样看,连卫国的死也有可疑。张春燕为什么会选择这栋楼?”
曹作家说:“老梁是孩子的父亲,连红当然应该有他在沪的地址。可惜张春燕找过来的时候,老梁已经不大正常,并且已经搬离了。但他有时候会回来,所以居然还见过女儿一次——只是他估计也不知道这是自己的女儿。”
阿武笑了笑:“你这个委托,我觉得实在是不大划算。”
曹作家没说话。
几个月前,一个叫连勇的男人找到他,付了一笔委托费,要求他帮忙调查一个密码。90年代,银行基本都还在用存折,他说他妹妹留下一笔赔偿金,现在他妹妹的存折、身份证和户口本都在他手上,只要有一个取款密码,他就可以自由动用这笔钱。
这天下午他们开车来到银行,曹作家报出银行账号与密码,出示了早就准备好的一份“委托书”,要求查询账户余额。密码是890319,张小茜的生日,余额是27.9元。阿武在旁边摸鼻子,曹作家却很不意外,他要了一张汇款单,自己拿出四千九百多块,凑了一个5000,汇到某一个账户上。
阿武颇为意外,问:“你汇给谁?”
曹作家:“张春燕的父母,他们退休工资不高,还要养那个孩子。”
阿武问:“你打算怎么和连勇交代?”
“把密码给他。”曹作家满不在乎地说,“他委托的内容是:调查一个密码,这其中并不包括帮助他得到一笔钱。”
阿武笑了。
回到花园坊的途中,曹作家坐在副驾驶上,细心地将他找到的那把铜梳用纸巾擦拭干净,阳光下,它每一处小齿都闪烁着动人的光芒。其前后两个主人并未有机会亲自叙述各自的心路历程,但有的抗争本就是静默的,不必发出什么声响,也不存在对错。
就像这世上其他大多数的故事一样,都是既不过于悲惨,也不过于幸运的。
— 全文完 —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 人间工作室 小程序
快来关注追更吧~
作者:谢十三
以前是个小学校长,现在预备躺平收租。
责编:方悄悄
更多内容请关注公众号:onstage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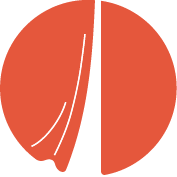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