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网易戏局栏目出品。
红日08:患有间歇性失语的女人,发出了婴儿的啼哭
前言
俞晓红和祝离的恩怨刚刚和解,“红日铁三角”的另一人孙海华却忽然发病。患有间歇性失语症的她,却在发病期间出声了——不,确切地说是啼哭,两长一短,婴儿的啼哭。
这特殊的哭声,祝离听到过,从一个真正的婴孩那里。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故事要重新说过。
第一场
祝离是在第五天回到红日的,所有人都很激动。她没有解释这五天为什么没来,大家也没去深究,唯恐给她压力,又把人赶跑了。人回来就好,红日的不安消散了大半,摇摇欲坠的团体又有了稳固的倾向。
所有人都围着祝离关心时,只有一个人没上前。
俞晓红如今的腿上已经不盖毯子了,单薄的裤子,单薄的腿。没了色彩浓郁又厚重的毯子加持,人也显得单薄了许多,似乎风一吹就能从轮椅上飘走。
但她的眼神是有重量的,千钧之重,看着会让人怀疑这具身体承载不了她的眼神。她用目光牢牢锁定着那位归来的,面容憔悴的红日元老,铁三角中的一角,她的挚友。
祝离推开包围圈,走到俞晓红的面前,每一步都走得艰难,她的手仍在震颤,腿也依旧跛着。几步路,她好像走了一辈子。到俞晓红面前站定,她嘴唇都是抖的,然后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扑通”一声,跪在俞晓红面前。
“对不起。”
俞晓红没反应,头微仰着,目光向下睨着她,面上尽显凉薄。
祝离的情绪绷不住了,她本就是个撒癔症的人,重复念着对不起,魔怔似的。迟迟得不到反馈,她开始磕头,往俞晓红的轮椅上磕,频率之快,下手之重,让人不禁怀疑这是不是她新诞生的躯体形式障碍。
俞晓红的轮椅被她磕得往后退,她便去抓稳轮椅,继续磕,磕得满头血。
围观的患者一个个惊叫着上前把人拉开,祝离却挣扎着去抱轮椅,要继续磕。场面一阵混乱,众人拉扯间,祝离不小心抱住了俞晓红的腿,那条仅剩的左腿。
所有人顿时安静了,没有人敢碰俞晓红的左腿,都怕刺激她。
祝离也呆了一下,迅速把那条腿放开,张皇不已,胃里突然一阵翻滚,她想呕吐。她不可遏制地想起了六年前在手术台上碰过的,俞晓红那条截肢的右小腿。
俞晓红没什么反应,淡然地收回左腿,冷脸看着她:“你这样有什么意义,你现在再痛,能有我截肢痛么,有我丧子痛么。”
祝离哭出了声:“晓红,我真的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俞晓红:“你是什么时候认出我的?”
祝离不说话,泪流成了一个水娃,她因为雌激素不调脸上一直有高原红,此刻因疲惫和过激的情绪更红了,泪痕崎岖地嵌在失去色差的黄褐斑上,让她显得苍老又可怜。
“……第一天,你来红日的第一天。”
俞晓红深吸口气,语气也有些颤抖:“那你为什么要和我做朋友?为什么要献殷勤?为了赎罪么?”
祝离似乎被这话刺激了,干脆坐到了地上,抹了把脸:“那你呢,你不也早就知道是我了么,为什么不揭穿我,还让我靠近?我给过你多少次机会,我把剪刀递给你,针筒递给你,把背给你!你为什么不捅我?我多少次就站在楼梯口,告诉你这里没摄像头,你为什么不推我?!”
俞晓红一时无言,她确实很早就猜到,祝离就是那张纸条上要她找的害她的人。祝离从没在她面前隐瞒过,在那个三甲医院做过护士,离职时间和俞晓红事故时间又吻合,她几乎把真相拍到她脸上了,要猜到并不难,没揭穿只是为了获取更多信息和证据,她要知道这个人到底对她做了些什么。
这半年来,她们都各自心怀鬼胎,隔着一层没捅破的窗户纸在做好友。
周围的人都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怎么就吵了起来,这两个不是关系最好的闺蜜么,孙海华今天没来,这铁三角的另两角就先自己内讧了。想介入又根本不知从哪入手,都面面相觑着叹气,有人已经跑上去找徐奔了。
俞晓红久未回应,祝离的气焰又瘪了下去:“我当时要是不帮他删除监控,我也会死的,他不会放过我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她用震颤的手把袖子推上去,推了几次才成功,露出臂弯处几道浅色的疤,看着像是一个个孔扎成的。经年过去,疤痕还这么深,看着十分瘆人,都是她前夫留下的。
俞晓红恍惚了很久,几度抬手,又放了下去,她突然感到汹涌的疲惫,她到底在斗什么,和谁斗,意义在哪?就算抓住了真凶,她还能怎么样,噩梦就会停息么?不过是从一张脸理所当然地换成另一张脸,她还是要这样残疾地活一生,她已经被毁掉了。
为了活下去,她适应了六年,可痛苦是无法适应的,她还要制造更多痛苦么?
为什么世上可怜人这么多,为什么可怜人还要被逼着迫害可怜人?
腕上的小玻璃瓶不知何时在炎热的天气里捂热了,贴着皮肤,像幼儿的体温。俞晓红沉默良久,开口时嗓子都哑了,像是把一口埋了六年的浊气吐了出来:“你还有别的事瞒着我么?”
祝离的哭泣一僵,她想到了那个孩子,胃部又一阵蠕动,面色变得苍白了几分。她看了看俞晓红的表情,却怎么都说不出口,只能摇头道:“没了,我只帮他删除了监控,我没想害你,真的,我跟你一样恨不得他死。”
俞晓红的眼眶红了,她把祝离从地上扶起来,祝离不肯起,抱着俞晓红的膝盖说胡话。两人最终都哭了,把周围不明所以的患者也传染了,似是这几天压抑久了,顿时哭声一片。小空呆滞地夹在这群大女人之间,在眼泪中闻到了孙海华的气味。
徐奔下来,看到的就是这幅场景,叹了口气上前安抚。祝离看到徐奔,爆发得更厉害了,醉酒的人似的,哭声间又出现了往日的嬉笑怒骂,红日在这一刻好像又完整了,不去看身后的悬崖,不去管脚下的累卵。
“她原谅她了?”站在远处看了全程的顾问骞道。
“早就原谅了。”司罕打了个哈欠,又站没站相了,“俞晓红为什么自残?她的腿在安乐住了五年多不见好,来到红日短短半年就不痛了,她在这半年内消解掉了整整六年都无法消解的心理症结,这段友情提供了多大的帮助。她其实知道,也正因为知道,才会对乐乐产生愧疚和背叛感,抗拒这种来源的治愈,用自残恢复疼痛是为了提醒自己记住仇恨。”
“她潜意识里其实早就在放下了,人的关系就是这么神奇,能麻痹一些东西,能让痛苦和仇恨变得懒惰。”
顾问骞不置可否,他知道俞晓红是什么时候报的警。
司罕观察着身边人的表情,莞尔道:“即使一开始动机不纯,相处就全是假的么?人最天真的,不正是以为一切都会按计划进行么。”
“是吧顾警官,我们经过这阵子的相处,你是不是也不像一开始那么讨厌我了。”
顾问骞侧目看向他,迎上一对带笑的眼睛,看起来狡黠又真诚,这双他曾极度反感的,好像藏了千万个捣蛋的诡计,眨一下眼就能倒出一堆,弄得鸡飞狗跳让他措手不及的笑面虎眼。
“我没有讨厌过你。”
司罕一愣,还来不及扩大笑意,就听这人硬邦邦道:“我是看不顺眼你。”
“……有什么区别?”
“我会看不顺眼一条乱闯红灯的狗,但不会讨厌它。”顾警官如是说。
司罕无言了好一会:“那你还是讨厌我吧。”
顾问骞偏过头,眼角浮上了微不可见的笑意。
大家的情绪到后面有些收不住,徐奔干脆决定下午聚餐,在红日室内烧烤,化解连日来的紧绷。所有人都操办起来,买伙食的买伙食,布置的布置,连那三个不被待见的外人也参与其中。顾问骞贡献了一箱可乐,司罕贡献了一箱娃哈哈,周焦贡献了一个节目。
对,小孩要表演节目,周焦和小空一起。
小空欢乐地拉着他转圈圈,食指向上戳他的脸教他“smile”。周焦耷拉着嘴,目光越发阴恻恻,那两个大人根本不管他,乐得他被折磨,司罕还语重心长地支持了一句:“爱笑的小孩运气不会差,你运气太差了,正好去学学。”
周焦沉默了很久,学着小空,用食指戳起自己的脸,对着司罕离开的背影smile。
下午孙海华也过来了,她听说祝离回来了,特地请了假过来的,跑得气喘吁吁,生怕祝离又不见了。铁三角一见面,刚休息会儿的眼眶又红了,聚在一起絮叨了很久。
樊秋水被患者们遍地召唤,处理食材,搬运器材,还要在场地上挂个联欢会的横幅,让他来题字。樊秋水的字写得很漂亮,是能挂出去展览的水平,大家让他自己想写什么字,应景点的,他题了五个字——最后的晚餐。
等横幅挂上去了,大家才看到这五个字,都觉得不好,太晦气了,但又没时间改了,火都烧起来了,该吃了。
徐奔搬酒进来时,看到那五个字,生气了,这还是患者们第一次看到徐奔生气,都手忙脚乱地把那横幅撤掉,丢在了墙角,隐约露出了“最后”两个字,没人去看,又都留在印象中,像是房间里的大象。
酒是最便宜的罐装酒,是开十分钟的车程,去最近的小商店买的,刺啦一声,开酒的声音很好听,许多人一起开时,像某种恢弘的奏乐。
即使是从不喝酒的患者,在今天也喝了一口,人或许冥冥中都有预感,在最快乐的氛围会想象最可怕的陨落。大抵精神病患者都会认同《欢乐颂》是首悲怆的乐曲。
她们举杯许愿。
“我们的病都会好吗?”
“坦白局能一直开下去么?”
“一直活在彼此的秘密中吧。”
“敬红日。”
喝得最上头时,不知谁带头,大家又群魔乱舞地唱跳起了红日的活动操。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
顾问骞站在黑色门前,记得上一次这扇门打开,那个叫红日的女孩就直挺挺地站在门后,她此刻会不会也在呢?
这扇加了双重锁的黑门,已经无法从里面自己打开了,五天来,她都没出来过的,地下室有食物?她为什么在可以自由活动时都宁愿选择待在地下,那里有什么?
此刻所有人都在聚餐,这里空无一人。
顾问骞的手轻轻搭上腰间,似乎要抽出什么。
突然,一阵令人耳朵发麻的哭声响彻红日,是婴儿的哭声,有着极为奇特的规律,两长一短,凄厉地重复着。
顾问骞目光一凝,警觉地四下查看,哪来的婴儿?红日有婴儿?!
这阵啼哭诡异而不自然,人在哭泣时呼吸的进出是不规律的,没有孩子的哭声会这么刻板地重复两长一短,一成不变,仿佛照着第一节均匀复制出了所有声段。
当找到声音来源时,发现是音箱,这阵奇特的婴儿哭声是从音箱里传来的,挂在走廊顶部的几个小音箱同时作用,让这哭声形成了响亮的环绕音,直往人脑子里沁。
顾问骞蹙眉:“录音室?”
他即刻往红日里唯一能播音的房间狂奔而去。
第二场
十分钟前。
司罕靠在墙边,嘬着娃哈哈乐呵呵地看患者们闹,顾问骞不知道又跑去哪了,周焦和小空被夹在她们中间,脸都绿了。
樊秋水心不在焉地四下张望着,有焦灼之色,司罕问他:“怎么了?”
“孙海华不见了。”
司罕一顿,这才发现铁三角还真的缺了一角,但大家都玩疯了,也没在意,可能上厕所去了。
樊秋水蹙眉道:“徐奔也不见了。”
司罕看了一圈,还真是,这个人群中心也不知何时退位了。
“你在担心什么?”
樊秋水的面色愈加难看:“徐奔最近的状态不正常,孙海华又难得才来一次,我怕他做出什么事来。他一直最喜欢孙海华,但孙海华拒绝得很明确,都在避着他,他尤其喜欢这种过程,把不听话的人一点点拖下去沉沦,同化成他那样的怪物,和他一起留在地狱里,这才是他最大的高潮。”
司罕思索片刻:“我和你一起找,他平时喜欢去哪里做这种事?”
“哪里都有可能,红日每个曲折的房间都是庇护所。”樊秋水露出不加掩饰的厌恶,所以他鲜少逛红日,怕一个转角就看到恶心的东西。从第一次“狗拿耗子”把人救下来反而被那患者埋怨后,他就不再乱晃了,但那些画面还在层出不穷地闯入他的视线,他甚至怀疑徐奔是故意的,他需要观众来见证他畸形的高潮。
两人朝外走去,司罕问:“孙海华不常来红日,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樊秋水:“肯定有,我都不明白她为什么非要来红日,住得远,工作又忙,要带孩子,还要避开徐奔这个禽兽,她就近找家医院看病不好么。”
司罕沉默,他也曾经思索过,孙海华的症状很严重,间歇性失语最大的问题是极其损害社会功能,影响她的职业,影响人际关系,是个对生活破坏性很大的症状。她又是个要拼命工作养孩子的人,为什么不选择更高效专业的医院治疗,而要来红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中心。
申城的总院和分院都没有她的病史记录,说明她从未去诊治过,他甚至怀疑她说去普通医院挂过神经外科都不一定是真的。间歇性失语很可能跟神经系统损害有关,去做体检是必要的,她有比红日所有人更迫切的康复动机,又有比红日所有人更困难的互助条件,她来这里图什么?只是讳疾忌医?
两人刚找了几个房间,突然听到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婴儿啼哭声从头顶落下,劣质的音箱把这哭声演绎得扭曲而瘆人。
樊秋水稍愣了一下,立刻面色难看地转身朝着录音室跑,司罕都来不及叫住他问,只得也跟着他跑。
两人抵达录音室时,门是锁着的,被樊秋水直接暴力地踹开了。
里面的场景让人愕然,徐奔半倚着台子,皮带半解,满是惊恐地瞪着孙海华。而孙海华面色惨白,衣衫不整地半坐在地上,嘴大张着,在凄厉地喊叫。
她的嘴张得那样大,喊得那样用力,那样撕心裂肺,可没人听到她真实的叫声。
因为从孙海华的嘴里发出来的,是婴儿的哭声,就是那串奇特的两长一短的婴儿哭声,通过录音台上误开的设备,传到了整个红日。
樊秋水先是愣了片刻,回过神立刻冲进去把吓到了的徐奔一脚踹开。
司罕快步上前,脱下外衣披在孙海华的身上,然后退开了些。她现在对异性的靠近是排斥的,而且那婴儿哭声持续不停,最好不要打断。他只站到她面前,让她能看到自己安全了,同时用设备通知祝离上来。
看着这样的孙海华,司罕隐约明白了,她的嗓子能发声,她的躯体症状根本不是间歇性失语,而是间歇性爆发婴儿啼哭。因此她在症状期间不得不闭口不言,伪装成失语。
她没去治疗,是为了隐瞒真实症状?为什么要隐瞒?
被踹到墙角的徐奔,尽管浑身都痛,精神也还处在惊恐中,但他甚至来不及调整姿势,就将目光紧紧地锁住还在诡异哭叫的孙海华。他的目光逐渐赤红,最后竟毫无顾忌地将手伸进了裤子里。
樊秋水泛起了强烈的恶心,这是怎样一幅变态的画面,孙海华在崩溃异叫,徐奔在她诡异瘆人的叫声中手淫,面目都兴奋得扭曲了,无比专注地凝视着她,孙海华崭新的诡异症状完全取悦了徐奔。
第三场
十几分前,徐奔以换音乐为由把孙海华骗到了录音室。她发病之前是商场播音员,熟悉设备,孙海华有点警惕,但他说是为了安抚俞晓红和祝离,给她们准备惊喜。孙海华还是进来了,所有人都喝了不少,只有她滴酒未沾,谨慎得仿佛生怕酒后会暴露出什么。
进去后徐奔就落锁了,孙海华惊讶不已,对于徐奔突然毫无伪装的状态。但她连惊讶都很安静,小嘴张圆,里面是让人想一探究竟的黝黑隧道。
徐奔没有立刻做什么,他对孙海华一直是喜爱的,像他自作的木雕里最满意的一个,正因为喜爱,他迟迟没下手完成最后一步,烫蜡。用上等的蜂蜡擦涂,提升木头的光泽亮度和湿度交换能力,让木质的天然纹理得以保存,成为经久不衰的工艺品。
但在成型的那一刻,它也作为一根真正的木头死去了。
他尤其喜欢烫蜡的过程,一点一点,将活物变成一颗琥珀。越是喜欢的木雕,越怕烫蜡不够隆重,死亡的过程不够享受,便心痒难耐地看着,等一个时机。
此刻,喝了酒的徐奔眼前有色彩在飞,孙海华变成了一只可爱的古印加木雕,就是现在了,他的心脏鼓鼓跳动,时机到了,他要给他最爱的木雕,烫蜡。
“小华,你现在就很好,不需要改变什么,不需要会说话,人类的话语本来就是不幸的源头,不会说话,是上天给的天赋啊。”
“放轻松,这里没人会指责你,外面剥夺你的还不够多吗,不要再惩罚自己,以你最真实的样子感受快乐不好吗?”
“我只是向你索要一个小小的契约,我给了你新家园,你该给我什么?我们是依偎在一起的难民啊,没人比我更懂你的痛苦了。”
他把他可爱的小木雕逼退到了桌旁,无路可退,他露出满意的笑容:“你为重回人间做的每一丝努力,对人间都一文不值,留在这吧,只有我是疼你的,连你的疮疤一起疼。”
孙海华挣扎得很厉害,但她无法开口,这份无声的挣扎对徐奔构不成任何威胁,甚至很合他意,这才更符合死亡过程的审美。
他真是喜欢她啊,这种无声的绝望让他激动到颤栗。正要将她剥开,头顶突然落下一阵让人耳鸣的婴儿啼哭声,徐奔瞬间跳了起来,心脏都要吓骤停了。他看到是孙海华在叫,本来小巧可爱的嘴,此刻成了幽深的小黑洞,狰狞地发出了令人胆颤的诡异声音。
怎么回事?孙海华不是失语么?还在反应,门就被踢开了,人和光一起涌了进来,徐奔被一脚踹到了墙角。
这脚很用力,他浑身骨头都在痛,可他却顾不上这些,直勾勾地盯着孙海华,这瘆人的声音是她的新症状吗?看她痛苦崩溃的模样,那幽暗的张得巨大的嘴,仿佛圣母玛利亚在吟唱。那婴儿的啼哭声有多可怕,症状有多诡异,在徐奔的眼里就有多迷人,他的脑中竟奏起了安魂曲,神怒之日的篇章,徐奔起反应了,他恨极了自己这种为痛苦高潮的特质,但他控制不了,他把手伸进裤子里,握住了那只短小、残缺、丑陋的,需要用痛苦灌溉的东西。
神啊,赐予他安宁吧。
第四场
顾问骞赶到录音室,眼前的场景让他只顿了一瞬,瞥了眼墙角狼狈纵欲的人,他快步走到司罕身旁:“怎么回事。”
司罕把猜测的大致讲了一下,顾问骞看着因为力竭,婴儿哭声渐弱的孙海华,蹙眉道:“她在伪装失语?”
司罕:“应该是不得已的,症状期间不想发出这种动静,只能闭嘴当哑巴了。”
顾问骞思索片刻,忽然问:“孙海华之前是在哪家商场做播音员?”
樊秋水走过来:“滨海西路的泰乐商场,她发病之后就调去仓库了。”
顾问骞沉默片刻,道:“那她的症状我可能是知道的。”
滨海西路的这间商场,有一阵子在商场播音时,总会突然爆发出诡异的婴儿哭声,那个声音非常奇特规律,一开始顾客以为是走失婴儿播报,但又没有具体信息,随着次数增多,这声音又过分规律诡异,顾客们都放弃了这个想法,觉得是灵异事件,还报了警。
那家商场被人扒出历史,原址在旧时代是个育婴堂,接收各地在乱世中被父母遗弃流离失所的孩子,二战后这里成了童尸乱葬岗。大部分都是传言,说建造的商场夜里会出现孩童的身影,无人的儿童乐园总会莫名一片狼藉,十年前那个商场在申城是很有名的都市传说,每晚结束营业后,都会循环播放一首歌《宝贝对不起》,说是借此安抚死者,但它很快倒闭了。新建的商场就是孙海华工作的泰乐,那时传说已经远去,直到三年前新商场被人报警说播音时有婴儿哭声,传言才又被人提起。
顾问骞没参与事件,这种民事事件都是基层民警从中调和,但因为传言多,他也听了几耳,其实什么事都没有,是商场播音员有疾病,播音时不自觉发出来的声音,后来怎么处理的他不知道,可能把那播音员开除了。但他现在知道,是转岗了,转去仓库了,那个播音员应该就是孙海华。
司罕和樊秋水听完,一时没说话,孙海华的叫声越来越轻了,她没力气叫了,这种声嘶力竭是极其耗费体力和精力的,可能会导致脑缺氧,她的嘴还是顽固地张着,让那道规律的两长一短的啼哭即使再微弱也还在发出着。
门口进来了一个人,是祝离。她似乎是跑上来的,气喘吁吁,面色惨白,浑身的症状和呼吸一起剧烈颤动,那条跛着的腿似乎更跛了,震颤的手似乎更震颤了。
她一进来,哪里都没看,目光如鹰般锁住了发出诡异声音的人,孙海华。
祝离的表情裂开了,她走了过来,短短几步,走得无比艰难,司罕立马给她让路,现在孙海华极需要信任的女性来安抚。
他还没迈开步子,身旁突然闪过一阵凌厉的风,祝离居然冲了过来,用她那副孱弱不堪的身体,一把揪住了孙海华,目光里爆发出了从未见过的怒意和震撼:“你,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哭声?”
婴儿啼哭声骤然止住了,像它毫无预警地爆发一般,毫无预警地熄灭了,孙海华弥散的眼神聚焦,落在祝离的脸上,目光逐渐清澈,恐惧缓缓填满瞳孔。这种恐惧,甚至比徐奔要侵犯她时还要剧烈,她想逃跑,却不知祝离哪来的力气,死死抓着她,一步都动不了,像只待宰羔羊般稳稳落在屠夫手里。
祝离从孙海华的眼神中确认了什么,几乎是凶狠地瞪着她,声嘶力竭道:“是你,是你!那个孩子在哪里?你把他藏在哪里?!”
故事要重新说过。
未完待续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人间工作室】小程序~
作者:穆戈
海怪投胎,自由写作
责编:赛梨
更多内容请关注公众号:onstage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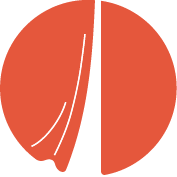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