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踏入社会那年,每天过得像奴隶一样,活着那么辛苦,那时候,我甚至想死了算了。但我并没有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我觉得,这是由于我最早期的记忆......
我的养父是农民工,因为家里穷,养父的第一任老婆在领养我之前就和他离婚了。
小时候是爷爷带着我。
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三四岁吧,爷爷带着我回家,从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走回去,这条小路连接着热闹的集市和闭塞的村落。记忆里小路似乎总是十分漫长,爷爷带着我走过了很多遍,很多时候,都是他抱着我走的。我知道的,他总会抱着我的。
那天,太阳很大,走到一半,我又累又渴,央求爷爷抱我,爷爷不同意。他扁担上挑着赶集买回来的货物。
我开始又哭又闹,赖在原地,不肯走,要求爷爷必须抱着我走,不然宝宝累死啦。
爷爷始终不同意,他认为我长大了,可以自己走了。
在耐心哄劝未果后,爷爷开始威胁:“你不走,那我先走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哦。”
面对威胁,我也始终一副“我不管我不管,我就是要你抱着我走”的固执宝宝样。
他没打我,也没骂我,自己默默挑着货物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满心以为他会回来接我。
没想到等了一会儿又一会儿,不对啊,咋还没来接本宝宝?我从期待,到茫然,再到愤怒着急,最后一边委屈害怕,一边迈着小短腿哭唧唧地去追爷爷了。
走了不到一百米,拐个小弯,我一眼看见爷爷就坐在前面的小溪边歇息,其实离我很近。因为周围都是甘蔗林,我看不到他,以为自己真的被抛弃了。
他看到追上来的我,微笑着为我擦掉眼泪,然后用强健有力的臂弯把我抱到小溪对面。
后面的事情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心里依然残留着些愤怒和委屈,觉得爷爷不爱自己了,但又因为被抛弃的恐慌,我似乎初次拥有了小小的独立意识,自己走完了回家的路程。
我从被抱着走的宝宝,变成自己走很长很长一段路的宝宝,累了,爷爷就会带着我在小溪边一起歇息。现在重温记忆,我明白,他依然爱我。
在落后贫瘠的地方,人的心灵也一样贫瘠,大人们的普遍共识是,面对任性哭闹的孩童,打骂是最直接高效的手段,更何况我这捡来的娃,更不能惯着了。
但爷爷并没有因为我的撒泼胡闹而生气、骂我或打我。他肩上有着负担,顶着炎炎烈日,却依然耐心陪着我哭泣,帮助我成长,没有真的离我而去。
这在缺失父母陪伴的孩童世界里,是可贵的。
爷爷在我五岁时过世了。
初中毕业后,我背井离乡出来打工,独立探索这个复杂的世界,有过挫折和迷茫,有过痛苦和挣扎。
那时刚出来,懵懵懂懂,啥也不会。姑姑拜托老乡把我介绍到一个黑厂上班,那是我最抑郁的一段时期。
工资只有10块钱一小时,加班12块钱一小时。工资还要压三个月,我刚出来一分钱也没有,吃饭的钱是从姑姑那里借的。
每天至少上12个小时,从早上八点上班,到晚上十点下班,忙的时候甚至加班到晚上十一、十二点。
一个月难得一天的休息,睡觉的时间都不够。没有自由的时间追求其他的爱好,没有时间社交,啥也不能做,连最基本的精神需求也被剥夺。总有干不完的活,总有加不完的班,活着就如同行尸走肉,或者一头干活的牲口。
最难过的是,因为新来,啥都不会,犯错了,还要遭受工头的粗暴辱骂,同事的冷漠无视甚至排挤。在这种不把人当人的环境里,人的心理也会跟着扭曲。
刚出来,缺少社会经验,我也十分害怕他们因为我干得不好把我开除,工头就是这么威胁我们的。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压榨人的苦力活,招人都难招,怎么会舍得把人开除?连童工、无赖、懒汉、骗子他们都会要!
总之,我完全就是一个干活机器,为了不挨骂,为了获得身边工友亲朋的认同,为了挣那一点吃饭的钱,每天麻木重复、从早到晚地埋头苦干。
我的手要不停地修割从机器里生产出来的磨具,速度不能慢下来,慢下来就要被工头呵斥,机器一分钟生产一个,我就要一分钟修割好一个。最开始因为不熟练经常划到手指,每天上班都要带着创可贴。
脚从疼痛站到麻木,手掌从磨破皮,到起水泡,最后变成了厚厚的一层茧。
每天早上起来,手又肿又痛。吃饭的时候,拿着筷子,手无法控制地颤抖。太痛了,那种痛不是手指划伤的尖锐的疼,是从骨骼肌肉里蔓延出来的持久的痛感和麻意,就好像被人用锤子每天把整个手都砸遍一样。
在厂里,上厕所和吃饭的时间都要争分夺秒,每天要忍受机器巨大的轰鸣声,空气中还有一股刺激的、极可能含毒的塑胶味,加上得不到足够的休息,头痛的毛病越来越严重,我都不知道有哪天上班时,头是不痛的。
因此,我的身体越来越差,面色蜡黄,消化不良,也变得很瘦,瘦到只有78斤,就像一个难民。
又是冬天,身体变差就容易感冒咳嗽,我去请假,可因为厂里活多赶着出货,工头并没有批准,让我自己忍忍。
伴随着身体垮掉的,还有精神的崩溃。
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告诉组长,晚上不想加班,太累了。组长让我去找厂长。
我找了厂长,厂长盯着我冷漠地问:“你有什么事?大家都加班,你为什么不加班?”
我告诉他我很累,需要休息。他坐在办公椅上,身体舒舒服服靠向椅背,轻哼一声,说:“你累?谁不累啊?哪有不累的活?你要明白,你是来挣钱的不是来玩的,不要总想着偷懒!要是不想干,可以走人,我们这不要不加班的人。”
他还说,现在那么忙,就算走人,他也是不会给我结工资的。
我每天依然这样加班,压抑麻木地干活。我想着,只要再扛两个月,他们说再过两个月忙季就过去了,刚好到时我发了第一笔工资,经济压力会减轻。谈离职的话,拿回全部工资也容易一些。
之后有天晚上,十一点下班,走在回出租屋的路上,经过一片河,周围空无一人,望着那一片黑暗寂静的河,我突然有股跳河淹死的冲动。我知道,我扛不住了。我低估了恶劣的生产环境和过长的工作时间,对人身体和心理的伤害。
手脚的疼痛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越来越严重的头痛折磨着我,有时走在路上,甚至听到脑袋里有水声在响,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幻觉。因为头痛,我也难以入眠,精神状态很差。
我崩溃了,打电话给姑姑,倾诉我的难过,告诉她,我想换一份工作。
她认为,我这点苦都吃不了,不行。并且,我就这样走了,让她在老乡面前也不好做人。她开始滔滔不绝地告诉我,她幼时的饥饿贫穷,早年打工有多辛酸、工资有多低;教育我好好干活,不要想太多。然后问我工资什么时候发,存了多少钱,这个月花销多少,有没有省着点;养父这个赌鬼最近又问她要钱了,让我有钱的话打点回去给他......
我把她的电话挂了,我受够了她喋喋不休的说教和唠叨。
眼泪从我的眼里流出,我捂住眼睛,蹲下身失声痛哭,忍不住想:“为什么她一直看不到我的绝望和痛苦?为什么她不能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给予我哪怕一丝安慰?为什么她总是和我说钱,让我感受到自己只是一个挣钱机器?”
内心的高楼已在崩塌的边缘,有个声音不断地呐喊着:“为什么我生长于这样的家庭?为什么我是最底层的那种人?为什么我要过这样的生活?”
我感到自己一文不值。那个声音疯狂地说:“你只是一个畜生,唯一的价值就是让工厂剥削,死了也不足惜。”
痛不欲生。
这一刻,我彻底否定了自己的人生。
那晚,我想了很多事情,包括自己要怎么死,死了会怎么样。
最后我想起爷爷,那时候我总想起他,想起他的支持和鼓励,在这些压抑痛苦的日子里,唯有想念过往的爱和温暖才能支撑着人走下去。
眼泪流得更凶了,回忆过往,我的冷漠和恨意慢慢被击溃。
终于,在热泪汹涌中,我开始试着自己安慰自己,我在心中大声告诉自己:“我很好,我值得过更好的生活。”
“我是人,活生生的人,我不是奴隶,不是畜生,我也可以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期望。”
“我愿意走完全程,不放弃我的生命、我的未来。”
“我保证,我会让自己过得更好。”
我经历了心灵的毁灭坍塌,又挺过来了。
我想像自己承诺的那样,去做一个人,而不是干活机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是,我从那家工厂自离了。在这个黑厂,只有两种离开方式,要么自离扣掉一半工资,要么做到年底工资全部结清。
离职那天,我在大街上闲逛,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有多久我没好好看着这一切,享受着这难得的自由了?脱离了昏天暗地的厂里生活,只是简简单单地望着路上行人,都能觉得很满足,那种感觉,太像刚从牢里被释放出来了,简直就是重获了新生。
后来,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改善自己的心理健康状态,利用了我能利用的资源,比如在网上接受一位心理咨询师的公益咨询;比如去找一些心理自助类图书观看,学习;花时间提高自信和社交技巧,交往善良可靠的朋友;改善和亲人的关系......
离开了有毒的工作环境,摆脱了高强度作业,我的身体也恢复健康。
现在,我依然在外地打工,努力试着让自己过有尊严和有人权的生活。
回忆这一切,是什么使我在感觉人生已经毫无意义的情况下,没有选择放弃生命?
我觉得是爱本身。正是因为爷爷早年在我身上种下爱的种子,这个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在我看到了自己压抑的痛苦和绝望的时候,种子趁机长成了大树,填补了心灵破碎空缺的那一部分,支撑着我,让我去接受自我疗愈的可能。由此产生的那些自我安慰的话语,毫无疑问,力量是强大的,它们在最后关键的时刻,把我从死亡的深渊里拉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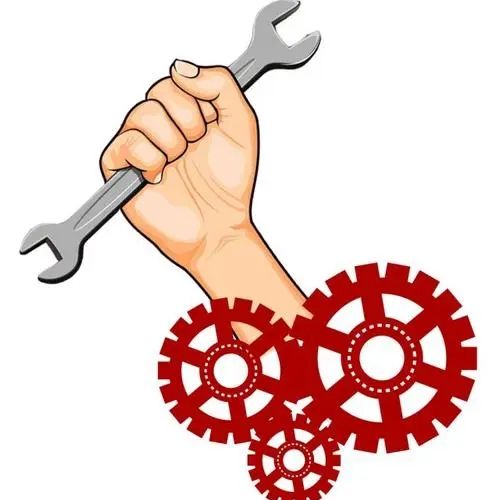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