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笑骂他们脸皮厚,他们只是嘻嘻一笑,和我说脸皮厚才能走天下。
01
我是在工地上认识他们的,这个他们,是一伙年轻人。而我已经在工地上待了十几年了,肩膀被挑沙灰的板子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嘴唇常年抽烟,变得发紫。大拇指的指甲盖被锤子敲过,多年来有些变形。
我很少在工地上见到年轻人,多半是师傅带来帮工的。其余的都是零零散散的,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唯独这伙年轻人,一共五个,互相都认识,很显然是好的。
他们脸上都是青涩和稚嫩,十几二十岁,都没有上过高中,有的连初中都没上完,很难让人放心他们能做好工地上的苦活。一开始没打算招,但人数没够,打地基的速度就得下降,影响后期工程。我和监工们一拍板,多招些人,大不了平时多盯着点,出不了什么大事。
于是,他们五个来到了工地。
也许是年轻人的原因,干活很认真,没有老油条的想法。力气也大,干活劲头很足,人也虚心,好学,什么都要凑一脚,试图学到点什么的。
我时常笑骂他们脸皮厚,他们只是嘻嘻一笑,和我说脸皮厚才能走天下。
我看着他们,心头被这股子年轻的气血感染,总是忍不住要照顾着点他们,他们的人生路还很长,长到还有更多选择,更多可能。
02
小李是五个人中年纪最大的,也才二十一岁。当初是他带着其余四个人一起出来打工的。
他们的老家在寨子里,少数民族地区,说着自己的语言,过着自己习俗的生活。但交通闭塞,大家都很早出门打工,家里都是留守老人和孩子,村子老旧,田也荒了。
“我出来找工做,他们知道了要跟我来,说也想找点活干,但是怕被骗,就一起来了。”小李操着口音,和我说道。
我问他们住哪,小李说五个人合租了一间房子,两个房间,挤着睡。沙发轮流着睡,两个人一个床。伙食费平摊,一星期吃一次肉,从老家拿来的腌咸菜就着吃。晚上七点以后再去超市买菜,会打折半价卖。
“明天去我家吃饭,我叫媳妇儿弄点好的,你们来就行。”我挥舞着手,要请他们吃饭。我实在是喜欢这几个孩子,难有的真诚。
他们先是愣了愣,摆摆手要拒绝我。“别不给谭哥面子,平时谭哥喊得起劲,请吃饭就要和我扯远关系咯?”我佯装叹气,他们顿时急了,点头答应。
我站起身说:“我先说好咯,不准买什么东西来,买了我可跟你们翻脸。”他们互相对视,和我说好。
短暂的聊天结束,工程还得继续。太阳实在是太大了,大家不情不愿地走出避暑区,继续操起手中的活计,工地上又响起乒乒乓乓的声音。
有工人大喊一声:“躲开!”随后尘板从空中抛下,掉在地上轰隆一声,震得地都在颤。一阵灰浮起,大家咳嗽几声,见怪不怪,因为这就是每天要面对的生活。
灰头土脸的回去,又朴素的来工地干活。每天都是这样,好像穿梭在城市里,却又好像不在。他们做着最苦的活,却又被城市排除在外。
我耳边突然浮现起小李和我说的话:“就为了拿点钱,苦也没有办法,不苦的话,也没人要我来做。”有些人仿佛就是为了吃苦而生,于是社会要分出很多阶层。
有的人天生接受了最好的教育,拥有最好的家境,所以成为了“上等人”。而太多太多人,都依旧挣扎在社会底层,一旦不用力,就会溺水。包括我也是,我心里一阵有心无力感,跺跺脚,把粘在鞋底的纸巾搓掉,石子被我搓得咔滋响,我朝里走去,我还要面对辛苦的一天。
3
晚上我回家喊媳妇做点好的,思量了一会儿,转给她三百块钱说:“都是大小伙子,能吃。你去多买点肉,什么肉都行,再称点大虾啥的,做好一点。其它的你自己看着办,别寒碜了。”
“弄得跟过年一样,你也是大方。”媳妇白我一眼,有些不满我太大手大脚。
“五个人呢!加上你,我,还有孩子,也有八个人了。家里还有点腊肉也弄来吃,饭多煮点。都是工地上的朋友,你也别那么多小心思了。”我说着,点了根烟,电视机放着新闻,窗外一片漆黑。
“是了是了,谭老板,明天我一定做妥当咯。”媳妇回房先歇息了,我知道她肯定还在网购软件逛逛选选的,但从来不买,都存购物车,过一段时间又看着它们下架,如此反复,就这么过去了十几年。
我垂着头,一口烟雾从我嘴里吐出,稍微平复了心情,起身也回了房。
04
第二天晚上,结束了工地上的活,我本想顺路把他们五个拉去家里,准备准备就开饭了。他们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泥灰,和我摆摆手,说要回去换身衣服。
“讲究有那么多干什么?哎哟,直接下去就开饭了嘛!”我劝道。
他们对视一眼还是拒绝了,说等会会赶快换好衣服就去:“谭哥,我们还是去换个衣服,毕竟是要去做客的嘛!嫂子见了也不好,我们自己心里头也不舒服。”我看没得劝,叮嘱他们弄好赶紧过来就开车走了。
回到家媳妇已经摆好一部分菜了,我说我先去洗个澡。“怎么就你一个人哦?”媳妇探着头,也没见其他人。“他们要回去换衣服,我也劝不住,说是要做客。”我回答她,一边说一边找衣服。
“诶,也是,谁都想体面点。”媳妇随口一说,就转身去了厨房。我听此一愣,摇摇头没说什么。
我擦着头发,门铃响了。打开门把他们拉进来,桌上的饭菜冒着热气。
我数落他们:“哎呀,来就来嘛,我不是喊你们不要提东西吗?”小李摇摇头说:“这是我们家乡的腌菜,还有一点水果,没怎么花钱。”我接过东西,没再说什么。
媳妇热情地叫他们加菜吃饭,想吃多少都有:“今天不吃了扶着墙出去,就是瞧不起我的手艺。”大家笑作一团,五个人把媳妇夸得合不拢嘴。
饭局到结尾,小肖灌着酒,哇一下就哭出来了:“谭哥,我这辈子都没吃得这么满足,家里太穷了,我出来就是想找点钱赚。可是我没读过的什么书,人家也瞧不起我,我就跟着来工地做点力气活。”他眼眶发红,和我说着,又灌了一口酒,趴在桌子上直不起身。
小李安慰他,叫他少喝点。“没事,给他喝吧,人也得发泄一下。”我说着,和其他人聊起来。
小李是唯一一个结婚的,这个结婚指的是办了婚礼娶了媳妇,年龄不够证还没领。现在有了个女儿,才三岁。媳妇带着孩子在家里种地,照顾老人,小李一个人出来打工。
“我有时候都感觉对不起她,她跟着我太苦了。”小李叹了口气,眼里都是无奈与苦楚。我感同身受,偷偷瞥了一眼跑去看电视的媳妇,心里决定过久带她买一身好点的衣服。
小农面相看着最楞,说好听点老实,说难听点就是最憨的一个。性子最犟,一看就是容易起冲突的类型。
“我出来是因为上初中的时候和班上一个女生处对象,结果她家里人知道了,让她辍学了,现在她去杭州打工了。当时他们话说得很难听,我也知道自己条件不好,但我还是心里烦,就跟着出来了。”小农呵呵一笑,说得很轻松。
“啧,现在怎么恋爱还不自由啊?”我替他打抱不平。“都过去了,现在我只想好好挣钱,别的不想。”小农扯着一根筋,他是真的被那件事伤到了,我估计再来一点刺激,就得无情无欲了。
剩下的两个人,是亲兄弟,都姓王,大家为了区分他俩,叫哥哥大王,弟弟小王,二人就差两岁。这对王炸兄弟平日里话最少,只是闷着头干活。
大王看了弟弟一眼说:“爷爷把我们带大的,她生病了,没钱治,走之前死了,都没和我们俩说。那晚我和弟弟才决定出去做工挣钱给他治病,他嘴上还答应我们要好好活着,等我们带他去大城市的医院看看。”说着大王忍不住哭了,他想起来爷爷走的前一天晚上和他说的话。
“爷爷跟我说,我们两个从小命苦没有爸妈,要团结一些才行。所以我们俩兄弟从不吵架,什么都想着退让。爷爷要我们出去外头要多做事,少占便宜,少计较,我们也照办了,只闷着头做事情,我们想着,只要做得越多,做得越好,生活会好起来的。”他扯着嘴笑了笑,一脸悲戚。
小王张了张口,还是没说什么,他给哥哥倒了一杯酒,坐在一旁没吭声。
“会好的,会好的,一天会好过一天,一年又会好过一年。”我举着酒杯,要他们和我碰杯。酒杯撞在一起的声音清脆,我和五个人,都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大概就是要一群有相同境遇的人聚在一起,聊一聊怎样去生活。生活中会有独自摸索,也会有互相扶持,他们感激遇到我,我又何尝不会感激他们。
喝到了天黑,直到他们离开,我看着桌上的狼藉,起身和媳妇收拾了起来。
“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嘛!谭老板做家务咯。”媳妇打趣我,我嘿嘿一笑,帮她把碗收进去。
空了的酒瓶在桌上堆起来。
“真能喝啊。”媳妇感叹一句。
“是啊。”故事那么多,苦也积压得太多,只能多喝一些了。
活着也许会很痛,但人生不能只有快意。我们得保持清醒,永远站在生活的前沿,我们背后有家庭,有朋友。我们肩上有责任,也有承诺。况且,谁又说过,痛苦不是人生的必修课。
我们不在乎那些阶级的歧视,我们随高楼而起,我们随公路而前行,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建设。我不是伟大的人,但我心里,一定有一个平凡的梦——终有一日,我建起的房会有一家三口的欢笑,会有朗朗的读书声,会有炊烟升起,也会有,我的期许。
太阳又升起,我又奔忙城市各地,我是工人,一个普通又平凡的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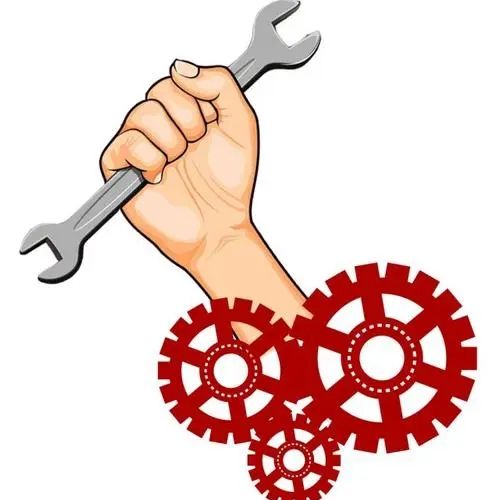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