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网易戏局栏目出品。
忒修斯之船02:她是他的病人,还是他的恋人?
前言
上回讲到,张语彤成为了杀害记者黄珊珊的嫌疑人,她说,证明她无罪的证据,在她的师兄陈明升那里。
直到她的老熟人——云上信息管理协会的官员李兰上场,温情的纱布刷地揭开,犯罪者方才露出了潜藏在底的狰狞面目。
在戏局作者陆鸣构造的“云端世界”里,比AI变成人更可怕的,是什么?
第一场
黄珊珊真想不到,会在这里碰见陈明升。
首先,这里是市立精神病院,不算什么通常意义上的体面地方。来这儿的人多半有病,还病得不轻,只是表面上不一定看得出来。其次,有钱有人脉的,谁也不会来公立医院看病:候诊一个半小时,花五十块钱,领一盒吃了就会感到快乐的药丸,不如躺在知名咨询师的诊疗椅上,转账五千,然后为一处略显可疑的童年阴影嚎啕大哭。最后的最后,她特意在工作日请假,坐城际轻轨来邻市挂号,为的就是避人耳目——是的,病耻感,世纪初就被人嚼烂了的词儿。站在干地上,指责和规劝都是容易的,但她现在泡在这人生的大江大河里,泥沙俱下,水都快要上到脖子根了。
陈明升显然也没料到她会在这里,往后退一大步,脸上立刻现出防备。黄珊珊想起张语彤为这人说过的好话,主动解释:“真不是来堵你的,你上次拒掉我,选题早就黄了。”
“那你怎么在这里?”
总不能说,同事有意无意划了她的包,还说是假的,她也心虚,没有强硬地要对方赔。好不容易挺到家里,哭得换气过度旧疾复发,又不敢给人知道了,只好跨市来看病。“我是精神病人,”她效仿他简洁的口吻,“来拿点药。”然后反问,堵住对方的话头:“你呢?你什么情况啊?”
陈明升说:“我是他们请来坐诊的。”
“那你白大褂呢?”
“这里是挂号大厅,我还没来得及上楼去换。”
一个是专家门诊的医生,一个是遮遮掩掩的病人。地位差距已经明明白白,再无转圜之地。黄珊珊感到一阵心慌,知道惊恐发作随时可能再来一次,刚想找个借口让他赶紧走。陈明升说:“你现在只能挂到普通号了吧?要不稍等会儿,我去打个招呼。下午开诊前,你来我这儿看。”
“这怎么好意思……”
“你是语彤朋友。帮点小忙应该的。”
说完这话,他就上楼了,背影颇为潇洒。只留下黄珊珊站在原地,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过了好一会儿,躯体症状消退了,她深吸一口气,脑内飞速上到云端,查了陈明升的价格——甚至不是专家号,是国际门诊——要价五百,每周一天,每次只放十个号,每个号面诊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她往后翻了翻,毫不意外,下周、下下周的,也早就被抢完了。
黄珊珊叹了口气,决定还是不走了。谁能跟天上掉下来的五百块钱过不去呢?而且张语彤说的一点儿没错,陈明升,确实是个好人。
中午一点,她如约上到主楼顶层,进了国际门诊。一出电梯,就被眼前的阵仗吓了一跳:护士站看起来像星级酒店的前台,由胡桃木嵌板、白色大理石和暖光内嵌灯带组成,坐落在这个空旷的门诊大厅中间,背靠着一整面落地窗,好像一座突然出现在海平线上的孤岛。黄珊珊四处张望。从建筑结构和装潢布置上隐约能看出,这里曾经是两层楼。为了让就诊环境配得上这五百块钱的挂号费,院方打通了一部分楼层,在护士站上方构造出了一个约八米的挑高空间。诊室、生化平台、休息区……则以门诊大厅为中心环绕分布。走廊上甚至有组合式光屏,供来访者接入云端打发时间。不过,和所有的医院一样,这里依然有一股闻起来十分洁净的消毒水气味。只有这个气味是黄珊珊熟悉的——嗅觉不依赖于眼睛,而疾病是一种隐喻。
护士站的人说,往左边走,第一诊室。还问她吃饭了没有,没有的话医院有配餐,可以送进去。黄珊珊不确定这是门诊福利还是陈明升安排的,但到底没好意思要,只说自己吃过了。
向左走,推开门。毫不意外,这儿的诊室看起来也像酒店套间。有棕色真皮沙发,大理石岛台,黄铜茶几。地上铺的原色实木地板。靠窗能晒到太阳的位置,放了一把看起来就很舒服的人体工学诊疗椅。陈明升从窗边回过头来,几步走到门边。黄珊珊还在找自己知道的那种就诊桌:“我坐哪儿呢?”
陈明升说:“随便。都行。”又说:“要不就沙发吧。”
黄珊珊捡了个靠扶手的角落,歪着半个身子,陷进去。
陈明升那边,已经开始看她的病历了——双相情感障碍合并重度焦虑,对他来说应该不算什么疑难杂症,没准都见多了。光线织就的档案界面,在他手掌下方悬停着,脚边的黄铜茶几原来兼有全息投影的功能。从这里看过去,由于角度问题,方形的浏览窗变形为一道几乎接近于白色粗实线的平行四边形,完全分辨不出那上面都写了什么。她正漫无目的地回忆着自己的病史,陈明升突然说了一句:“黄珊珊,对吗?”
黄珊珊心头一跳,装作刚回神的样子:“说我名字?”
“对。”
“那没错的。怎么突然问这个?”
“习惯了,三查七对。”
“我又不做手术,你也不在住院区呀。”
“所以说习惯了。和语彤不一样,我的研究方向和神经病学关系更密切,在医院里待的时间可能比在学校还久。像这种坐诊,也是平时工作的一部分。”
话题逐渐往其他地方偏了,这是好事。黄珊珊决定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可语彤现在也开医院了。你俩一个师门出来的,研究方向再怎么样也不会差太远吧。”
“不能这么说。你的理解方式就不对。”陈明升皱着眉头瞥了她一眼,较真的劲儿跟张语彤一模一样。黄珊珊不由腹诽:难道这是某种学术训练的痕迹?这会儿滔滔不绝的,倒是和拒绝采访时判若两人。“这是神经科学研究思路的区别。一方面,异常大脑为神经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最早的切口;一方面,对正常人的大脑活动进行研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对既往经验进行爬梳和对照。”
“听不懂。”
“听不懂你怎么跑研会?”
“陈老师,陈教授。我不跑研会的,我是商业报道的记者……那天也是去采访厂商……”
陈明升瞪着她,似乎才想起来黄珊珊不是自己的学生,是来看病的。
“好吧,”他挂着脸,不高不兴地哼了一声,“但既然我们讲到这里,还是应该把概念厘清楚。不管怎么说,脑机的商业应用和学界的前沿突破是密切相关的。你应该有这个意识,不能满足于目前职业限制的知识领域。特别文化传媒,一个具有公共宣教义务的行业……”
黄珊珊急忙打断他:“知道了知道了我错了我真错了!你要不直接开始讲吧。讲完记得给我开个药就行。”
她哪想得到,陈明升一鼓作气,干脆给她上了快四十分钟的课。剩下二十分钟简单过了一遍病史,聊了聊这回的发作症状,然后根据既往用药开了处方。五百块挂号费的国际门诊,别人只能给看半个小时,她倒好,还搭上了一节科普教育,也不知道是值还是不值。临走的时候,陈明升一脸神清气爽,连连夸她理解到位、态度认真。黄珊珊把哈欠扼杀在喉咙里,乖巧地表示都是陈老师教得好。正准备拍屁股走人,陈明升向她飞出一张虚拟名片,还附上了一句留言:“有需要,可以来学校找我开药,不必特地跑这么远。”待到她回头去捕捉他脸上的表情,却只看到一个淡淡的微笑。还来不及想这笑容背后的情绪,一个大叔擦肩而过,走进诊室,在她面前砰地关上了门——下午的开诊时间到了。
黄珊珊站在原地,心跳如鼓。可能是重度焦虑导致的躯体症状,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神经递质是一种化学信使。分子层面,答案总是清晰明了;映射在人的意识中,却随情境的变化而衍生出不同的解释。总而言之,她不知道——对于这种既令人兴奋又带来些许不安的情感,在一个真正重要的时刻,那些被命运推上台前的人,好像从来都没能准备好。
第二场
药很快就吃完了,效果却不好。因为陈明升说,她停药已经两三年了,应激性事件导致的单次发作,不一定要吃回之前的处方,只给她开了些安定和营养剂。“还是尽量自己调整,毕竟心境本来就会波动,你这次也是事出有因。”在云端上,他重复那天的结论:“一旦要开始吃拉莫三嗪、坦度螺酮、阿普唑仑这些东西,肯定得长期服药稳定情况,再视情况慢慢减量。考虑到药物副作用,我个人是觉得慎重,最好能通过心理治疗来改善。”
黄珊珊破罐子破摔地说,吃药好歹医疗保险能报销一部分,心理治疗肯定是没钱看的。
陈明升又建议,那就请个长病假,先好好休息休息,远离应激环境对她也有积极作用。“我可以给你开病假条。按照现行劳动法的规定,你至少能拿着半薪歇满一个月。到时候我们再来结合生化结果进一步做治疗评估。”
他听起来很高兴,仿佛她的困难并不具体,而是纸面上一道条件苛刻但稍加琢磨即可解开的证明题。黄珊珊轻声地说:“如果拿你的单子去请病假,一个月后回公司,我就会丢掉现在这份工作。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话,选择也不会很多,恐怕只能去一些后台产业。”
比如,贡献生物脑的解析能力,把自己的审美、经历以及情感模式喂给AI,加速它们取代人类工作的速度。比如,去科技公司的外包团队里当个专属客服,接待难哄的VIP客户——这可是活生生的人才能胜任的情绪沙包。比如,审核意识流信息,人脑擅长解读机器看不出来的隐喻和讽刺,云端世界总还是需要这样便宜高效的“肉开关”。
既不体面,也不产生任何价值感。她哪个都不想做。当然,要是知道了自己正带病生存,也可能是这些企业根本就看不上她。
陈明升说:“我们学校很多老师也请过这种病假,没什么问题呀?”
“学校是学校,社会是社会。”
“那按照劳动法,你可以告他们。”
“按照劳动法,最好的情况,我可以得到一笔赔偿。然而,劳动法不能帮我找到一份新的工作。”黄珊珊开始感到疲倦了:明明不得已的人是她,对方却好像成了那个被为难的人。“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也有专业上的考虑。我先自己控制看看。”
妥协的结果,是另一次更严重的发作。
最先降临的是失眠。星期天晚上,照例走了一遍睡前流程:热水澡,助眠香薰,甜牛奶,拍松的枕头。躺下去直到凌晨四点钟,毫无睡意。这个租来的卧室里潜伏着一头看不见的怪兽,只在她闭上眼睛的时候出现。她能感觉到它阴郁的注视,像钟乳石笋上一滴将落未落的水珠。由于恐惧着那冰凉的溅落,她不由自主地绷紧了神经,任凭意识在失控的电化学之海中上下起伏。
第二天,星期一,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糟了:她整夜没睡。星期三,吃了药,可能睡着了两三个小时,也可能没有,她的自我感知已经出了问题。星期四,在办公室毫无必要地加班到晚上十二点,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害怕回家,害怕面对失眠。星期五,她不得不找借口又请了一天假,因为最轻微的不快,现在都会激怒她——手上端着刚倒好的热水,心里却下意识地想着该怎么找个机会泼到同事手上。她恨极了。如果不是被划了包,如果不是这帮人老是给她找气受,如果不是这个该死的主编又无能又自负,如果不是生在这种把人当消耗品即抛即用的时代……
她本来已经好了。她已经死而复生过一次了啊。
再一次,从公司硬挺到家。没敢开车,咬牙叫了一辆的士。五十块钱的车费,想着要是能在后座上睡一会儿,也算值了,可惜还是做不到。休息如今是一项过于艰难的义务,几乎等同于自我折磨。健康则成了一个遥远的国度,她已经离岸太远,或许不会再有机会回头。回到住处,打开卧室门。那一瞬间,一切仿佛都在旋转。黄珊珊知道,这就是极限了,必须想办法求救——可是,要通过什么渠道,又能向谁求救呢?还来不及细想,随着一阵剧烈的痉挛,如同一只时令时不灵的灯泡,世界向她放射的种种映像,在这仿佛将成为永恒的旋转中,突兀地熄灭了。
醒来的时候,黄珊珊觉得很渴。
视野还是有些昏暗,但不再旋转了。一切几乎都是白色的,除了帘子是淡淡的婴儿蓝。一个人影迅速地向边上退去。“护士,她醒了。”是陈明升。
黄珊珊问:“你怎么在这儿?”
陈明升往边上让了让,意思是一会儿再说。一名护士从他身后挤进来,开始询问情况、检查体征。黄珊珊任由她摆布,眼睛依旧死死地盯着陈明升。她很想知道,等自己从这个病房里出去,是得在同事们幸灾乐祸的八卦声中主动辞职,还是干脆找个湖跳下去一了百了。说来讽刺,昏倒的这段时间,她倒是得到了充足的休息,现在神采奕奕,甚至开始后悔星期五不是真的泼了那杯热水,而是选择了请假。
护士走了。陈明升上前来,坐到她床边。“我确实应该给你开药的,”他承认错误,“很明显,你现在到躁期了。”
“昏过去之前,我还非常想死呢。”
“一天之内,抑郁态到躁狂态。快速交替的环形心境障碍。”
黄珊珊立刻捕捉到了重点:“也就是说我昏过去还不到一天。”
“对。反应很快。”
他在暗示吗?因为她处于躁狂模式,所以思维才能如此敏捷。黄珊珊想笑。在她看来,自己一直都非常聪明,特别敏锐,并且拥有普通人不具备的洞察力和分析头脑。要不是求学经历坎坷了些,选的专业坑了点,超越张语彤也不是什么问题。区区陈明升,竟然敢对她评头论足。
“你到底想说什么?”她冲着他高傲地扬起下巴。
陈明升把隔帘放下来。“我们先来谈谈发生的事情,你想知道过去这八个小时里都发生了什么吗?”他好脾气地说。而她立刻识别出,这是精神病院里那帮医生最爱用的语气。
也就是说,自己现在并不“正常”。这种无所不能、飘飘欲仙的状态,并不“正常”。
她竭力抑制住膨胀的自我感受:“我昏倒了。你送我来的?”
“对。详细一点是这样:你昏倒了,因为过度疲劳,大概率伴随了一次惊恐发作,因为我到你住处的时候,地上有呕吐物——万一呛到了,还是挺危险的。”
黄珊珊不吭声了。自尊心像硫酸一样灼烧她的脸颊。陈明升见她没有反应,继续往下说:“明天,也就是星期六,本来约好你来我这里复诊,但我临时接到通知要开会,因此中午想联系你改个时间。没想到从一点多等到三点多,你都没回复,我就担心是不是出事了。刚好在附近,直接去了你公司,然后,你领导给了我你的地址。”
“原来如此,”黄珊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都听到了什么,只能尽力装作若无其事,“那你怎么和他们说的?你没有提我的病吧?”
“我说中午本来想约个饭,发现联系不上。你最近总说工作很累,既然请假了,我想过去探望下。”
黄珊珊哑口无言。这借口编得非常合理,简直不像是陈明升这样的象牙塔木头能想出来的,就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容易引人误会——真不知道同事们现在都是怎么编排她的。不等她消化完其中的信息量,陈明升特别真挚地补上一句:“而且这也不能算假话。咱们现在是朋友,我确实想去探望你,还买了点心。”
病床旁可没见着那种东西。“我怎么没看见?”
“当时太着急,好像放你家里了。”
躁狂发作时,人会陷入一种高涨而振奋的心境中,精力充沛,骄傲自大,幻想自己魅力非凡,天纵奇才。黄珊珊再次提醒自己,这是疾病透镜扭曲后的错觉,不是真的,嘴里却不由自主地吐出一句:“陈明升,你该不会是有点儿喜欢我吧?”
陈明升笑了,矜持而略带保留,像是人们被说中心事后会浮现的那种表情,也像是那天在国际门诊外她没能看清的那个笑容。
“可能吧,我也不知道。”想了两分钟,他诚实说。
第三场
黄珊珊开始跟陈明升约会。
能不能说是约会呢?这她也不确定。他们没有正儿八经地做过假期计划,也没有特地去什么网红餐厅打卡。一般就是黄珊珊外出采访,顺路到大学里见面。或者陈明升碰巧到她公司附近,请黄珊珊下楼吃顿饭。但不管是哪一种,最后总得开个房。他们很默契地达成了共识:现阶段,两个人都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节奏,那么干脆一切从简,尽量不在双方家里过夜。
比较正面的迹象是,陈明升既不避开自己的学生,也没要求黄珊珊对同事保密。虽然这段关系开始得不清不楚,欠缺一个正式的告白,但在外人看来,他们经常出双入对,完全就是在谈恋爱的样子。黄珊珊不知道应不应该要求他做出些明确的表示——她才二十四岁,之前只有过两段恋爱经历,担心自己太矫情,显得孩子气。陈明升倒是三十六了,整整比她大一轮。可据他说,他之前只想搞科研,心思很单纯,再加上没人向他告白,所以从来也没谈过。
这能是真的吗?你家里没给你介绍过吗?张语彤不是还给你留了一封信吗?黄珊珊很想就这么反问过去,但怎么也说不出口。一方面,万一陈明升真的因为什么巧合没看过那封信,她是把事情复杂化了;另一方面,自从陈明升频频出现在公司楼下,不但同事们态度好了一些,连主编对她都比之前客气了许多。
可能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他,黄珊珊想,只是喜欢他带来的这些好处。现在,她相当于有了一个专属的医生,周末能去高档一点的地方散心,甚至还买了新包——这次是真货——陈明升云端户头里的购物卡多得用不完。黄珊珊把包拿在手里掂量:虽说看不出细节差在哪儿,但确实跟上一个的质感不太一样。她把包背到单位,随意甩在角落里。午饭聊天的时候有意无意漏出一句,这是陈明升主动给她买的。
“这次可别再给我划了,”黄珊珊笑嘻嘻地说,“要不生气的该是他了。”
至于张语彤那边,她到现在都没有勇气去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谁对谁错,毕竟张语彤自己都几乎放下了。唯一不妥的是,没在刚有苗头的时候就告诉对方,错过了最自然最正当的时机。黄珊珊在心里演绎和张语彤摊牌时的情景,无论她如何调整话术,总感觉双方会落入到无话可说的境地。在那假想中花岗岩一般的沉默里,张语彤的疑问不言自明——“为什么他喜欢的人不是我,而是你?”
这个问题折磨她想象中的张语彤,也折磨她自己。然而,除开这些忸怩作态的自我告解,它其实也通向一种隐晦的胜利。自少女时代,她就时常幻想这样的未来:从茫茫人海里,自庸常中一跃而出,夺取某个大人物的垂青,只为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确实与众不同。
虽说是通过恋爱的方式,但她也算是部分成功了。
陈明升倒是不常提起张语彤。只有一次,黄珊珊试探性地说,上次学会年会上遇见,语彤好像在查什么东西,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说。陈明升本来在批改学生的论文,听见这话,眼神微微地侧过来,像一把推出后斜放着的美工刀。“她和你提过?”他问,很严肃。黄珊珊立刻解释说,其实也只是一笔带过,她只是突然想起来,好奇。陈明升松了一口气,摇摇头:“那这个事儿,你最好别碰。”
这种时候,她又会觉得自己被轻视了。被当成了一个可爱的、不设防的、需要呵护的女友。真正重要的事情,就像那些酒会上她进不去的房间,关上门,他选择和其他人共谋。甚至连治疗方案,陈明升也不信任她的判断——她一直暗示,按照以前吃惯的处方来就可以,毕竟按照这个路径,自己已经康复过一次了。可陈明升说,既然复发了,就应该换一换诊疗思路,上一个医生的方案太保守了。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和我说。如果你感觉不好,我们就换药。不过,要做好思想准备:一开始肯定会比较艰难。哪怕你吃回之前的处方,一样会有药物反应。慢慢适应、慢慢克服,要接受这是个比较长的过程。”
又是那种哄骗的、劝诱的语调,带着精神病院里消毒水的余韵,披挂着权威的白袍。
黄珊珊抿着嘴,一声不吭。她心里清楚:在他面前,自己首先是个女人,其次是个病人。无端拒绝会被当作感情用事。极力争辩则有可能滑向躁狂。越是如此,越是要表现得平和、理智、心态开放。
“那就先按你开的处方来吃吧。我有耐心。”
陈明升很满意:“非常好。耐心是康复的第一步。”
于是,她要吃的药变多了。每天两顿:早上两片拉莫三嗪、一片阿立哌唑、一片碳酸锂、一片坦度螺酮;晚上两片碳酸锂、一片喹硫平、两片坦度螺酮。大部分药都是白色的。椭圆形。圆形。圆角矩形。拉莫三嗪具黑醋栗香味,坦度螺酮是薄膜涂层片。只有晚上的喹硫平是粉红色的——准确来讲是西柚粉——像把痘痘里的脓挤干净后渗出的那点表皮组织液。陈明升不允许她喝酒、喝咖啡、喝可乐,每次吃完药都得给他发信息确认。为了避开同事们的刺探,她不得不在公司的卫生间里偷偷摸摸地吞咽药物。
她被困住了。她不自由。
第四场
张语彤醒了。
睡得肯定不算久。最多一个小时。她精神紧张。大脑只稍稍啜饮过睡眠的泉水,就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复苏。在逐渐稳定下来的视野中心,还是一样的景象:办公桌、圆头台灯、黑色制服、光滑如镜的单向玻璃。而她也依旧坐在这张窄小的铁椅子上,体会着尾骨处传来的阵阵酸疼。有那么一瞬间,张语彤想要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她是受害者。她已经被迫经历了这一切。她需要真正的休息和心理干预。但在证明自己的清白之前,谁也不会放她离开这里。
“哦,你醒了。不再多睡一会儿?”那个年轻的警官问。很和气。
“睡得比较难受,”张语彤说,“还是赶紧问完,我去拘留所里躺着吧。”
“还要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陈明升脱离危险了,不过还没醒。”
“那真挺好的。”张语彤费力地说,感觉这声音在她舌尖上留下了一种奇怪的涩味。“我睡过去之前提供给你们的线索,现在有在查吗?”
老警官哼了一声:“你不用这么积极。你从进来到现在讲过的所有信息,我们都会一一核实。”
张语彤半垂着眼,用余光去捕捉另一位警官的动作。只见他挂着脸,幅度很小地点了点头,似乎只是在赞同搭档的发言。张语彤希望自己接收到的信息没有错:他在暗示,已经有人去查她要的那个东西了。
“云上信息管理协会的官员已经进驻我们的专案组。你应该很熟悉,叫李兰。”
“认识。安全监管司的司长,曾经来我们医院临检过。”
“据说她之前就比较关注你,一直要求对云梦疗养院这一类的脑机医疗机构实施更严格的资格审查。这次也是主动要求过来参与我们的工作。”
张语彤心里一紧,有些拿不准对方的立场,不由得抬头瞥了他一眼。他没看她,还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李司长会从脑机应用的专业角度,对目前所有的证据再做一遍梳理。包括现场监控,你提供的供词、记忆棒、视觉捕捉、意识流记录……还有黄珊珊的尸检报告。”
“好的。”张语彤稍稍放下心来:李兰虽然看不惯自己,但在脑机应用领域绝对是专业的。只要有她在,黄珊珊脑部留存的证据就不会被湮灭;补上这一环,在专业论证层面,既定事实也能极大洗清自己目前的嫌疑。除非,她的对手连这一步都算到了……但这真的可能吗?翻转棋盘,如果是她,站在“老钱”的位置上,又会怎么做?
冷汗像蚯蚓,爬了满背。张语彤猛然意识到,自己忽略了最重要的信息。
“我能不能问一下,安安是怎么……死的?”
对面眉头一皱,刚要反问。张语彤连忙往下说:“警察同志,您想啊,如果我真的害了她,我肯定知道她的死因,你和我说了也不会改变什么。但如果我是清白的,您告诉我,我说不定还能想到一些线索。这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你真不知道她怎么死的?当时你就在现场。”
“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我确实是收到她的信息要见面,但进楼以后没找到她。出事以后,我是被你们警察带走的,也没人和我说过现场的情况。”
他们不说话了。表面的、物理性的沉默。难道这也是什么必须打申请才能透露的信息吗?张语彤盯着那面单向玻璃,等待着,暗自祈祷这群人的同理心能够稍稍往自己这里倾斜一下。终于,那位年轻的警官发出了一声类似咳嗽的声音。
“她是坠楼。”
玻璃弹珠一般,这四个字依次落地。细节就像面团里的酵母。黄珊珊的死——这个事实其本身——因为增添了具体的描述而膨胀起来,压迫着她的心脏。张语彤咬紧了牙关,在愤怒和悲恸的灼烧中无法自控地颤抖。她强迫自己追问:“还有别的吗?”
“十一层的高度,头部着地,当场死亡。”他显然知道张语彤需要的是什么,有意着重透露:“事发的时候下暴雨,视线不好。等周围有人发现的时候,现场的脑组织保护得就是……也比较差。鉴证人员尽了最大能力去搜集。考虑到冲刷和蛋白水解的影响,很难说脑部原有的纳米机械还保留了多少。”
张语彤眨掉视野里逐渐浮起来的泪水。眼下,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黄珊珊,她最需要的就是审慎和冷静。“这不对,”张语彤深吸一口气,“你们抓我的时候,说的不是这样。当时是说,安安死前浮现的最后一个意念,是我。”
“对。我们据此怀疑,她死前最后看到的人是你。”
“据我所知,意识流脉冲只能从脑机里提取。您刚刚也说,她的脑部组织保护得不好,纳米机械搜集不全——请问这是怎么做到的?”
办公桌后的两人俱是一愣。年轻些的那位目光闪烁,已经开始动摇了;年长的这位把眼皮子往下一放,语气不善:“张语彤,我警告你,不要得寸进尺。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刑侦工作,已经超出了你能要求知情的范围。”多半是怕被她控制了谈话的节奏,故意杀杀气势。张语彤立刻摆明态度:“这么大的疑点,涉及到个人的清白,我为什么不能要求知情?如果不在这里解释清楚,我宁愿保持沉默。”
她挑衅地看着他们,却猝不及防地在单向玻璃上瞥见了自己。很难说到底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十分钟前,她还非常想从这里出去。想随便找个地方大哭一场,然后坐朋友的车回家。这会儿,镜子里的这个女人却显示出一种静止的神态,仿佛被固定在油画里的蒙娜丽莎,已经接受了终有一死的命运,因此要在这里天长地久地耗下去,不再寄托无谓的希望。就在这时,有人推门进来。走廊射入的暖光,破坏了这幅画阴沉的色调。张语彤还来不及转动眼珠,就听到来人说:“用不着。我来给你解释清楚。”
是李兰。还是那样一张石刻般的脸,每一道沟壑都暗藏着中年人的倦怠和技术官僚的自视甚高。“赵贝思替你整理提交了一份资料,我们刚刚看过。”她开门见山地说,顺便找了把折叠椅坐下。“汇总云管协内部的一些线报,也找到了一些疑点。这会儿应该开出搜查令了。”
张语彤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但猜想赵贝思应该不会做无用功。“有结果吗?”她问。
“没那么快,要等。”
“那你完全可以先去检查证据。”
“我带了人过来,他们已经接手了。我对你怎么自圆其说比较好奇,尤其考虑到这边的同事也需要一些专业上的说明。”李兰向办公桌的方向侧身,点了点头,就算是打过招呼了。
张语彤盯着单向玻璃,一动不动。镜子里,李兰位于她的右手边,呈九十度夹角,侧对——极其讽刺地复刻了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的落座方式,仿佛这不是一场加码的审讯,而是一次妥帖的谈心。但很快,她反应过来了:要是真的确信自己有嫌疑,云管协的人,特别是这个李兰,不太可能如此客气。
李兰说:“讲讲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陈明升就是‘老钱’的?”
这是险境,也是转机。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人间工作室】小程序~
作者:陆鸣
故事会因为落在纸上而成为某种程度的真实。
责编:方悄悄
更多内容请关注公众号:onstage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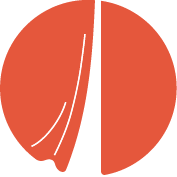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