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十多年中介,主营上海老洋房,经手上百套房产,我终于实现了“卖房自由”——只做5000万以上的单子。
成交后,我经常会受邀去房主家做客。这日,陶老板请我去他家品酒。他那套法租界里的老洋房,是我经手交易,并且委托人重新设计的。
经过改造的老洋房,整体是时下富人喜欢的侘寂风,千金难买的老壁炉成为装饰,落地窗能俯瞰凡尔赛宫同款花园全貌,沙发私人订制,意大利纯手工,我一坐下,就感觉人融化在沙发里。
这十多年间,陶老板已经换手了五六套。他有老上海情结,从新式里弄到老公寓,终于住上花园洋房,二婚娶了个年轻貌美的上海小囡,从一个“沪漂”,摇身一变,过上“上只角”的生活。
我和陶老板还是同一个慈善基金会会员。当然,他是为了拓展社交圈,而我,是为了卖房。
陶老板举杯,感谢我为他打造了这样一个完美的房子,同时抛出一根橄榄枝:“我有个在美国的朋友Andy,也看中一套上海的老洋房,你帮他留意下。”
“他看中哪一套?预算多少?“我在脑海里迅速搜索——我踏遍上海每一套老洋房,有信心立即匹配成功。
“价格好商量,不过,他只想要X公馆。”陶老板说。
“那一套……恐怕有些难办。”这一次,轮到我犯了难。
“凶宅”
市面流通的上海老洋房,存量只有百余套,更像是仅此一件的顶级奢侈品。但因为历史遗留原因,很多产权都盘根错节,这成为老洋房交易的最大障碍之一。
X公馆的产权倒不复杂。这栋老洋房的主人,父亲曾经是沪上知名的资本家,楼里一度住着三代人。
五年前,就有客户看中X公馆。我先走访了几位邻居,侧面了解X公馆的情况:主人已去世,目前的继承人是他的长子忠伯。除了忠伯的独子长期在美国,其他的老洋房第三代,都带着家人住在这栋楼里。
说起这栋楼,附近弄堂里的邻居们讳莫如深:三楼有间房一直没人住,到了夜深人静时,不时会传来老人的哭声,“老房子嘛,风水都不好。“邻居有点幸灾乐祸,接着又添油加醋地告诉我,“不过呢,也有人说那个老头子,藏了一屋子的金银财宝呢。”
即便如此,由于品相良好,地处市中心,从2003年之后,来询价的人就不少。有人曾开出过1200万的价格,这在当时,可以购置几套地段不错的商品房,但房子始终没有出售。
看上去,X公馆待价而沽,高不可攀。但我知道,不愿出售房产的主人们,并非都活得如鱼得水。老一辈早已退出舞台,第三代们之所以蜗居老宅,多是败光了祖荫,工作又不如意,买不起附近的商品房,所以一直将就和等待。兴许是身处“上只角”的优越感作祟,这一等,这些人就错过了一波又一波“下只角”的楼市风潮,这大概就是老洋房“风水不好“的根源。
所谓“上只角”,是指上海早期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区域,主要是指湖南路、余庆路、愚园路、淮海路、南京路等一带,闹中取静。老上海眼中,即使蜗居弄堂,身处“上只角”都是一种身份象征,那里多为洋人和社会名流、商贾的居住地,区别于“七十二家房客”的聒噪和复杂。
辗转经人介绍,我结识了X公馆的第三代居住者——忠伯的一位侄子,提出有人想购买他们的宅子。
“如果有条件,谁愿意住在那样的房子里?水电煤的管道都是老式的,窗户很小,外立面看着雅致,里面隔热隔音都不行。”忠伯的侄子对在老宅苟活的生活十分不满,他们悻悻然地提出,“要不是大伯父子俩不答应卖房,我们都已经过上了好日子。”
我意识到,忠伯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五年前,见面那天,下着大雨,我准备了精美的金华火腿和鲜花,约好上门拜访忠伯。
老宅有老宅的气派,层高差不多五米,罗马柱在屋中矗立。只是年久失修,木质楼梯踩着吱吱嘎嘎,阴雨天里,原配的彩色玻璃更显诡异。
忠伯风湿严重,膝盖的疼痛比天气预报还准。但尽管腿脚不便,他还坚持住在三楼,和那间“鬼屋”为伴,平日里,深居简出。
我以慈善基金会的名义才联系上忠伯,尽管没啥收入,但他这些年来,一直用积蓄坚持做公益。我先跟他聊捐助和生活,他和颜悦色,时不时拿出一方丝质手帕掩饰咳嗽。
末了,我忍不住“夹带私货”,“忠伯,您住在这样的老房子实在不方便,有没有考虑置换,改善下居住条件?现在老房子行情不错,很容易出手。”
忠伯一下子明白了,板起脸孔,“又是楼下那几个小家伙让你来游说我的?我不会卖的,多少钱都不卖!”
“您有什么顾虑呢?他们也是为你好……”我不知该如何缓解僵局。
“为我好的话,就让我清静清静……”忠伯拿起雕花精致的红木手杖,起身送客。
新贵
虽然五年前被拒,我仍然不愿错失潜在客户,央求陶老板介绍Andy给我认识。
一来,几年过去了,说不定X公馆主人咬定的东西也松动了;二来,只要意向客户手握资金,即使买不了这套,也可以推荐类似的,实在不行,还可以鼓励他们先租赁体验。
我对自己的业务能力有信心。客户只言片语地描述一些阳台或者外壁的形态,我就能在脑海中勾勒出房子的画面,然后检索匹配——典型的西班牙风格,墙面通常为弧线形水泥拉毛粉刷,住宅房间窗框处会并列螺旋形双柱,屋顶会铺设筒瓦;而法式的建筑,则遵循古希腊、罗马建筑的整齐对称,通常会有镶嵌着手工烧制彩色玻璃的窗户,阳光一照,煞是好看。地中海式建筑,则以形式多样、色彩明快著称。还有些上海老洋房,会博采众长,中西混搭。
从业之初,我花了四个月逛遍上海的老洋房,并且阅读大量书籍,熟悉它们的历史。如今,闲暇时间,除了社交、进修、健身,我依然到处去看房子。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一群真正的“高净值人群“,要想打动他们,除了精准的匹配,还要对老房子的文化和故事说得头头是道。
Andy是华裔法国人,中文出奇地好,我练就的一口流利的社交法语没能派上用场。他今年42岁,独身,在美国纽约工作。我与他的第一次通话,安排在纽约时间晚上九点,寒暄一阵后,我直入主题。
“听陶总说,您看中了X公馆,不瞒您说,有点难办。您有其他选择吗?”
“陶总说您很可靠,其他的房子我不考虑,请帮我多留意X公馆。”
“您为什么那么执著?我手头有更多增值空间更好的老洋房,绝不会让您的资产缩水。”
“有些私人原因,我不便说。”
挂了电话,我反复咀嚼Andy的“私人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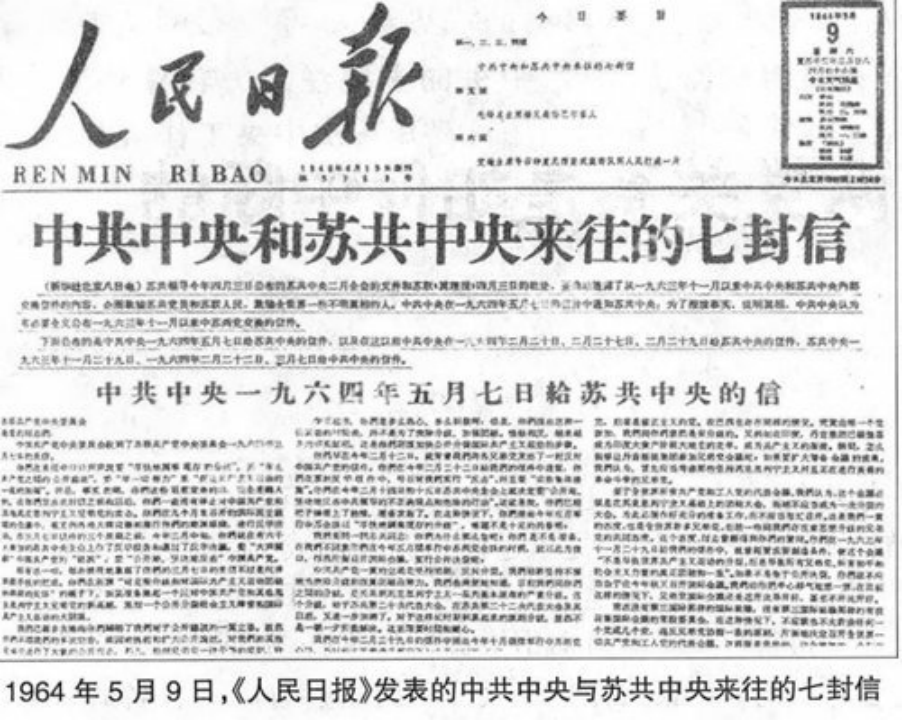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