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地说,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前,慈禧是一个深谙权谋之道的愤青,不是投降派。
掌控权力的前三十多年里,慈禧一直秉承的是大清第一、中国第二、洋人第三,而她自己,则是大清的第一人,皇帝都不能与她相提并论。
慈禧讲究吃、讲究穿、排场大、修园子、过生日,生活极其奢侈。这些奢侈生活除了是其本性之外,慈禧还给它叠加了一层政治含义。
在慈禧看来,自己是九州万方第一人,自己的面子代表大清的面子,大清的面子代表中国的面子,自己要是没面子,大清就会被洋人看不起,中国就会被洋人欺负。
此种观点虽然荒谬,但确实是慈禧本人的逻辑,她身边宫女的回忆录经常提到这一点。
与很多人想象中不同,在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慈禧对洋人是非常痛恨的,她的执政风格,在一群只知道对洋人妥协退让的爱新觉罗家族男人面前,显得非常激进。
请注意,这是和爱新觉罗家族的男人相比,慈禧显得激进,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火烧圆明园时,慈禧在政治上并没有发言权,但据说,私底下她是反对咸丰皇帝听从肃顺等人的建议逃去承德避暑山庄的,她主张就在北京城和洋人干。这也是慈禧与肃顺等人水火不容的主要原因之一。
辛酉政变之后,实际把控满清行政中枢的是恭亲王奕䜣,以及围绕在奕䜣周围的洋务派群体。
这派群体的执政风格用一个字就能总结:让。
他们对洋人是百般退让,只要洋大人提出要求,他们就会想尽办法予以满足,生怕惹得洋大人不高兴。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新疆问题上他们主张放弃,在中法战争问题上他们主张趁胜求和。
慈禧对这种行政风格是非常不满的。
作为深宫妇人,慈禧并没有实际接触过洋人,她也一直因为丈夫咸丰的郁郁而终,对洋人没有好感。
在新疆问题上,慈禧力排众议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在中法战争问题上,慈禧又委派左宗棠前往福建坐镇指挥。
发展到最后,慈禧与小叔子恭亲王奕䜣的关系逐渐变得水火不容。
作为一个权谋老道的阴谋家,慈禧采取了两手来搞倒奕䜣。
1,她放任言官的权力增长,用言官来牵制实际执政的奕䜣追随者。
言官们多是饱读诗书却没有实际执政经验的清流,论引经据典搞道德文章,奕䜣追随者不是他们的对手。
2,培养醇亲王奕譞以替代恭亲王奕䜣。
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慈禧的小叔子兼亲妹夫。
奕譞比哥哥奕䜣小七岁,打小也是个愤青,对奕䜣在外交处理中一味的妥协退让也非常不满,经常高喊“整军备战,恢复祖宗荣光。”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公元1884年(光绪十年)4月8日,慈禧突然发布懿旨,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一个不留。
新的军机处大臣,“遇有重大事件,先与醇亲王商办”。因这一年是农历甲申年,也称“甲申易枢”。
“甲申易枢”之后,慈禧彻底掌控了满清朝廷的最高权力,再无掣肘。
清廷也一改之前只知道软弱退让的执政风格,转而开始整军备战,谋求强硬。
1885年,深受中法战争中法国舰队横行无忌的刺激,清廷下谕“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
10月,清廷采纳李鸿章专设衙门以统辖画一之权的建议,决定设立海军衙门。
1886年5月,醇亲王奕譞奉旨巡阅北洋海防。
8月,清廷为防俄谋占朝之永兴湾,命丁汝昌与琅威理率定远、镇远 、济远、威远、超勇、扬威六舰舰队赴朝鲜釜山、元山一带巡游。
8月9日,北洋海军抵达长崎,日本认为北洋舰队的来访是其炫耀武力,向自己施加压力 。
就在十多年前的1874年,日本人还主动打过台湾的主意,现在大清的水师反而兵临日本本土。
所有人都认为,时移世易,攻守易势。
1889年,18岁的光绪皇帝亲政,正式走上政治前台。
光绪的师傅翁同龢是清流派的主力,耳濡目染之下,光绪也养成了凡事对外强硬的施政理念,极其瞧不起日本,经常叫嚷“对日一战不可避免”。
在对日问题上,慈禧与光绪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就是极力主张对日强硬,希望通过击败日本来重振大清国威。
所谓的“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这种传闻,其主要原因是大清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与慈禧的对日强硬态度无关。
真正反对向日本开战的,反而是李鸿章这种洋务派遗留,他们是强烈主张凡事都对外妥协的。
可以说,如果不是光绪皇帝凭借慈禧的支持,强力压制了李鸿章的意见,甲午战争的规模根本不可能打那么大。
如果听从李鸿章的建议不打,清廷就是给北洋水师再多的军费,也没有用。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看起来光绪皇帝好像是大义凛然发愤图强,可真实历史中,甲午战争却对清廷的权威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连蕞尔小邦的日本都搞不定,也就难怪人心思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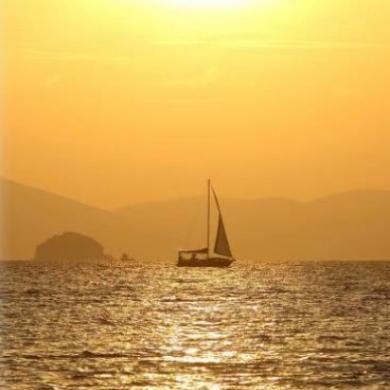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