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每个陕北人心中都装着一碗小米粥,陕北人几乎每天都要喝小米粥的,一天不喝小米粥就好像没有吃饱一样,没有了精气神。即使参加了宴席,吃了那所谓的山珍海味,回到家还要喝一碗小米粥,不喝一碗小米粥好像没有吃饱一样。在陕北人眼里,没有什么比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来的实在、舒坦。
小米粥是根植在陕北人骨子里的一碗粥。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陕北人,对小米粥的喜爱在我小时候母亲就在我心里种下了种子。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每天早上永远是我们家起的最早的那一个人,村子里的鸡叫三遍过后,当窗户纸上麻麻亮的时候母亲就起床了。
母亲起床不久,院子里就传来鸡的咯咯声,牛的哞哞声,猪的哼哼声……母亲首先忙着喂家里的那些牲畜,忙完以后就开始做饭了。陕北农家的早餐很简单,可以蒸几个馒头或者连带蒸几个红薯,有时候甚至不用炒菜,在缸里捞几根酸豆角或者一根酸萝卜切成丝就是一个菜,但绝对少不了熬一锅小米粥。
一锅清水里抓一把小米下去,把锅坐在灶膛上。灶膛里的柴禾燃烧的正旺,火苗一下一下欢快地舔着锅底,渐渐地锅中响起滋滋的声音,锅中的清水蹿起一连串的细碎的水泡儿,那先前还在锅底沉默的小米随着水泡儿的蹿起在锅中沉沉浮浮跳跃起来。
《食林广记》所言:疾徐不同,文武不同的火势可以决定食物的口感。煮小米粥讲究一个“熬”字,所谓的“熬”就是要掌握好火候,也是煮小米粥最重要的一环。从大火依次为中火、小火之煨火。让水与小米相互渗透、相互糅合,以至于最后变成一锅软软糯糯,一层米油儿浮在上面的色泽金黄、清香四溢的小米粥。
熬一锅好的小米粥远远不止加水那么简单,米与水的比例、熬的时间与火候,都要拿捏的恰到好处。袁枚《随园食单》中写:“见水不见米,非粥也;见米不见水,非粥也。必使米水融合,柔腻如一,而后谓之粥。”
每天早上叫起一个赖床孩子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厨房里散发出的香味,我也一样。小时候叫我起床的是母亲熬的那小米粥,迷迷糊糊中厨房中小米粥的清香一股一股传来,肚子也咕噜噜叫起来。起床后简单洗漱一下,母亲早已把一碗晾的温热适宜的小米粥放在我面前,当然少不了一碟酸菜,那酸菜可以是几根酸豆角,也可以是一根已经被切成丝的酸萝卜丝。
急不可待的捧起碗,稀溜溜喝一大口,满嘴谷物的清香,再吃一口酸菜,酸菜在嘴里脆脆的响,那叫个舒坦。
《板桥家书》中说》: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一捧一咽,一缩一啜,道出了一碗粥温贫暖老的至深情味,更是普通百姓居家过日子的真实写照。
陕北小米粥还有一经典做法是熬小米粥时加入豆钱钱。豆钱钱是黑豆在清水中浸泡一晚上,沥干水,然后到石碾上碾压。记住不可过分碾压,把黑豆碾压成片状即可。熬豆钱钱小米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豆钱钱不容易熟,所以首先要把豆钱钱加入清水中熬,豆钱钱饱含油分,熬时容易起沫和溢锅。
水开后捊去浮沫,切记,此时不能盖上锅盖,不然容易导致溢锅。等锅中没有了浮沫再加入小米盖上锅盖慢火一起熬。让小米在水的作用下与豆钱钱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助力、相互补充、相互合作。小米粥由于豆钱钱的加入,小米粥中的谷物的清香中有了豆油的香味,变成了油汪汪的清香四溢的豆钱钱小米粥。小米还和南瓜一切熬粥,叫南瓜稀饭,甜而清香;小米和绿豆一切熬粥叫绿豆稀饭,清热解毒。不同材料的加入有不同的口感,不同的风味,不同的营养。
陕北谷子,一年生草本植物,古代称稷、粟,亦称梁。一种粮食作物,有的书说稷为黍属。古代以稷为百谷之长,因此帝王奉祀为谷神,也有江山社稷之说。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有文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可见谷的种植历史悠久。在北方一般称为糜子、谷子,盛产于黄土高原。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农作物。
由于陕北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干旱少雨,反而适宜谷子耐贫瘠、耐干旱的特性,得以在陕北大面积种植。谷子脱壳以后,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米、小米。对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它们并不多见,尤其在南方更是稀罕之物。
小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以及人们所需的赖氨酸和蛋氨酸,并且色泽金黄,颗粒浑圆,粘糯芳香,油脂丰富,深得陕北人的厚爱。现在由于物流的发达和快捷,陕北小米也走向了五湖四海,收获了不少地方的粉丝。
人生百味,素食清欢。即便一碗小米粥一碟小菜,也熬煮出了陕北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希翼。在穷苦的日子,一碗清粥喝进去的往往是生活的无奈与苦楚。如今习惯了大鱼大肉,偶尔简简单单的吃食,才发现最是这极简的家常、毫不起眼的味道,经得起岁月的考验,越能抚平生活的焦灼,勾起一个人与家的思念。
一碗小米粥,陕北人一生的执念与挚爱!
喝一碗小米粥,吼一声信天游,是陕北人的本色出演:
生在土窑洞
长在黄土坡
妈妈熬的小米粥
滋润我心窝
作者:刘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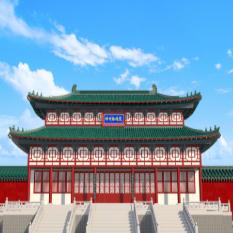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