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它同“反冒进”针锋相对,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从此揭开了瞎指挥、浮夸风、弄虚作假的序幕。
1958年夏季,全国各地农村的小麦、早稻、花生等作物的高产“卫星”竞相“上天”,令人眼花缭乱。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的影响和支配下,放高产“卫星”运动席卷全国,有些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也被迫卷入这一场神话般的竞赛中。
1958年7月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院第二届党代会上讲话,谈到全国已经出现很多亩产一万斤的小麦试验田。

这时,坐在台下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代表聂春荣递上纸条,上面写道:
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小麦高产能手,准备向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和其他有关单位挑战。
张劲夫当场号召中国科学院组织各方面专家,连夜开会提出办试验田的研究计划,向农民生产能手应战。
第二天,科学家们商定了向农民丰产能手应战的1959年丰产试验田单季亩产指标:
第一本账:小麦1.5万斤,水稻2万斤,籽棉3千斤,甘薯15万斤;
第二本账:小麦2万斤,水稻3万斤,籽棉4千斤,甘薯20万斤;第三本账:小麦3万斤,水稻4万斤,籽棉6千斤,甘薯26万斤。
7月5日和6日听取农民丰产能手的报告后,大家觉得原定的应战指标已经远远落后了。
7月7日,借农民丰产能手参观有关研究机构,丰产座谈会暂时休会之机,生物学部召开了会议,把亩产指标调整为:

小麦2万斤,争取3万斤;水稻2万斤,争取3万斤;甘薯30万斤,争取40万斤;籽棉6千斤,争取1万斤。
7月8日,分组座谈。原定是交流经验,但是会议一开始就展开了指标大战。
在小麦组的会议上,湖北省谷城县新气象五社主任王家炳首先发难,提出1959年小麦亩产3万斤的指标。
紧接着出现了拍卖行里经常见到的那种竞相抬价的景象,亩产从3万2千斤、3万5千斤,迅速提升到4万斤,话音未落,那边又冒出了4万2千斤……
竞争主要在农民丰产能手之间展开。
在紧张的第一回合较量中,生物学部彻底打输了,不仅不敢向农民挑战应战,就连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出的挑战(小麦亩产指标4万5千斤),还犹豫了好久才应战。
就在生物学部仓皇应战时,河北省邢台县丰产能手一下子把小麦亩产指标提到5万5千斤。
7月8日晚,生物学部紧急会议,连夜讨论新的高产指标和保证措施。
9日上午是丰产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生物学部向中国农业科学院贴出了挑战书,亩产指标是:

小麦5万斤,争取6万斤;水稻6万斤,争取6万5千斤;籽棉1万5千斤,争取2万斤;甘薯40万斤,争取50万斤。
到9日会议召开时,这些指标又迅速退居下游了。河南、陕西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小麦亩产指标10万斤;
江苏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多数科学家和农民都心知肚明,亩产万斤是绝无其事,但只能假戏“真做”。
1958年7月中旬,全国科联组织中科院负责人和各相关学部科学家,召开丰产座谈会,中科院负责人和部分科学家应邀参加,由一名国务院副总理主持。
在会上,这名国务院副总理宣读了中央一位领导的批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
宣读完毕后,这名副总理当众号召:“中科院也要办试验田,亩产必须达20万斤!这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科学的重大成就”
在这种压力下,根本不容许讨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被迫仓促上阵应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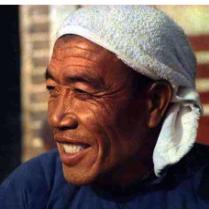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