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扬州耆宿林苏门于兴起之间写竹枝词名曰《青石板天井》:“来往原无井,当阶石板填。画时宫称亩,凿处地规天。大块平皆合,空青断总连。何人常露坐?风月两悠然”以赞天井,并作小引“天井用青石板铺之,较胜于用砖之生苔聚蚊矣”点名题目。
何谓天井?
“天井”一词最早出现在孙子兵法《行军篇》“凡地有绝涧天井、天陷、天隙,必然远之勿近也”,原指四面陡峭、中间低平的作战地形。后因中国古代宅院中房与房或与围墙之间所围成的露天空地——从上往下看,由屋顶四周坡屋面围合而成一个敞顶式空间形似漏斗式的井口,从下往上看,则四面高墙围堵,亦如身处深井井底只能窥见方寸的天地,故而“天井”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建筑形式。在明清时期,南方地区几乎到了有堂皆井的程度,其中,又以徽州民居的“四水归堂——晴雨两宜,四时皆景”为精髓。
海德格尔在《筑·思·居》一文中写:要把建筑看作是一种思想的任务。虽然中国古代没有系统性的建筑理论,但中国古典建筑设计的出发点——同时满足居住者在精神上和功能上的需求却与海德格尔对建筑的定义不谋而合。因此,毫无疑问,天井和其他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相同,可以抽象而为一个包含“表层”和“深层”双重结构的文化符号。
在表面上,参观中国江西、徽州等地的传统民居,进门先见“天井”,抬头,一隅蓝天、高墙、底部略显逼仄的正方形或长方形的空间、在上海的弄堂北京的胡同从不会出现的静谧而透明的光晕,站定,感受从石块和砖头的表面所透出的微微冷气,在因窗上木雕的拦截而摇曳的亮而冷的光段里,在与外界几乎隔绝的寂静中,一个似乎将某种中国文化紧密封存于其中的厚重空间在不动声色地消解着空间外的激烈变动。
这一被封存的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天井作为文化符号的深层结构和属性,“以天为主,以人为客,上下其地,通于天地”,我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人的财富主要依赖于风调雨顺、寒暑时至,因此观察天象成为了人们的一项重要日常,天井作为室内开敞空间,则为此提供了“直达通道”,合乎荀子《天论》掌握天时,利用万物之道,又及天井之景观往往延续室外的风景到院落空间,以作为外部环境私有化的表达,天井,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古人对“天人合一”抽象化的内心诉求到现实的人居环境的转化。
现在,让我们回归到日常生活,回归到摆放在天井里的餐桌、竹椅、陈酿、花生米、儿童、妇女、老人慢腾腾的起身、嬉闹、闲聊、唠不完的陈芝麻烂谷子,回到放鞭炮、迎财神、祈团圆、祭月亮……天井作为内聚性的空间,在将不同性质的空间连接而为一体以外,还作为一种纽带把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聚集而为一个大的家族、一个鲜活亮丽的共同体,相对于人的渺小而显得有些过于高、大、威严肃穆的老宅也因天井而充满了盎然生机。
咫尺之间,别有洞天。
小小的天井虽然只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一隅,但它所“化形”的古代中国人长期适应自然、追求精神世界、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立体画卷,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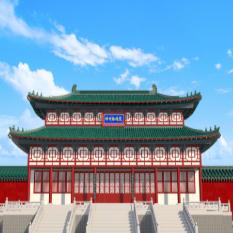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