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老少爷们儿们!在下张大少。
蒙特城堡位于阿普利亚北部,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建造1。城堡矗立在被称为穆尔日(Murge)的平原上的一座圆锥形小山上,缓缓地向大海倾倒。其独特的八边形外形,每个角落都有八角形塔楼,被阴影清晰地勾勒出来。鲜明的城墙突出了其立体感。蒙特城堡的几何关系无需创造或猜测。它们只是存在于这座建筑中,它需要数学分析来帮助将其作为建筑对象进行评估,就像历史分析、年代分析、艺术史分析和建筑史分析一样。
图29.1蒙特城堡。
当然,我们必须忽略城堡的实际尺寸与明显的设计目标之间的微小偏差。建筑师在这里建造了一些小的偏差,例如,为了突出建筑的东翼。这并没有贬低基本概念,恰恰相反。这些偏差显然是基于一个明确的总体规划。
几何分析和定义
蒙特城堡的二维布局可以被确定为一个具有 16 个元素的对称群:8 个反射平面和 8 个旋转平面。这是一个自同构群。这些对称关系在所有游览塔中都有体现(图 29.2)。对称的多重性通过同构关系(即主楼的大八角形、内庭院的八角形和置于同一轴线系统中的八个八角形塔楼之间的 "相似性")得到了扩展。
图29.2蒙特城堡的对称群。
三个八边形彼此“相似”的尺寸比由4/h (I):2h(II):2(2√2-1)h(III)给出,其中h是基本网格的网格尺寸(图29.3)。三个八角形的边长比为2a:a:c(√2-1),其中a为庭院八角形的边长。这里涉及的对称群是D16型平面群,用J. M. Montesinos-Amilibia (1987)的符号表示。
图29.3基本网格。
简单的反射对称在自然界中经常出现,长期以来在建筑中发挥着重要的美学功能。还有其他一些数学关系同样具有很强的美学效果,它们也出现在自然界中--例如,与五边形有关的 "黄金比例"。蒙特城堡的建筑师清楚地意识到对称在美学上的重要性。他利用这些对称性实现了城堡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观,至今仍影响着我们。
平面航拍照片(图 29.4)显示,构成内院的八角形的切线在八角形角楼的中心相交:它们形成一个八角星,星尖位于角楼的中心。这就提供了内院和角楼之间的几何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上文讨论的相似性关系建立起来的。
图 29.4 蒙特城堡鸟瞰图及几何图形。
《蒙特城堡》(Gotze,1984 年)一书中首次讨论了这一关系,并给出了该布局的几何结构(图 29.5、29.6 和 29.7)。马克斯·科赫首先想到了几何平面中的多重对称所带来的强烈美学效果,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具有自身内在美的几何构型(科赫,1991 年:221-233)。他将其描述为由正多边形概括而成的八面体构型,并根据以下原则进行构建:
1. 该配置包括一个中心八边形 O 的中心点和顶点,以及中心八边形的八个较小的平移副本 OV 的中心点和顶点,所有副本的大小相等。
2. OV 的中心 MV 位于通过 O 的中心 M 和 O 的顶点的射线上。
3. 所有 MV 与 M 的距离相同。
4. 尽可能多的 O 和 OV 的顶点和中心是共线的;也就是说,它们位于共同的直线上。最后一个条件对美学构造至关重要。科赫随后讨论了许多不同的可能共线排列。
图29.5蒙特城堡几何构造中的第一步。
图29.6蒙特城堡几何构造中的第二步。
图29.7蒙特城堡几何构造中的第三步。
在图 29.8 中,标出了两个这样的 "交点"(即基本八边形结构中位于一条直线上的点):连接八边形中心 MaMv 的直线(或相当于通过 c 和 b 的直线),以及两个外部八边形的切线。
图29.8两个共线排列。
除了图 29.5、图 29.6 和图 29.7 所示的布局(需要罗盘和直尺)之外,汉诺威工业大学的马塞尔-埃尔内(Marcel Erne´)提出了另一种不需要罗盘的布局(图 29.9)。
图29.9布局的替代结构。
在画出一个直角后(如第一种构造),我们将一个大正方形分成边长为 h 的 16 个子正方形(如上图 29.3)。h 可以看作是一个模量,其大小可以根据城堡的测量结果计算出来。下一步是创建第二个同样大的正方形,并将其旋转 45°,使新正方形的顶点位于原正方形主轴的延长线上。这就是通过旋转正方形来构建八边形的经典方法。第二种构造的优点之一是可以轻松计算所有线段的长度。
关系
构成城堡外侧内墙的八边形边长由相交网格决定,是构成内部庭院的八边形边长的两倍。八个外塔的宽度等于一个庭院边长 a。
我们也可以使用网格尺寸 h 作为基本单位来代替 a。可以通过测量塔楼的宽度或内部庭院的边长,从实际建筑中找到 a 的数量。虽然 h 作为构建矩形网格的基本单位非常重要,但如何测量 h 却不是很清楚。网格在布局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估计在将图纸转化为建筑的实际建造过程中也起着关键作用。对于这种复杂的几何构型,如果不在施工现场进行全尺寸标注,是不可能建造出来的。显然,这也不可能是"手工"完成的,而必须使用现成的机械测量工具。以 h 为基本单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果(参见图 29.3):
1. 院墙外侧与外墙内侧之间的距离为 h。
2. 从一面墙的中心到另一面墙的中心,内部庭院的直径是 2h。
3. 塔楼中心之间的距离也是 2h。
4. 塔楼的边长为 b=a^2×h/2 ,外墙的厚度为 c=a^2/((2√2)h) 。
5. 城堡的总宽度为 (4√2)h。这个数学公式与几何构造相对应。
值得注意的是√2的出现,尽管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正在处理正方形和八边形的构造。
俄罗斯建筑历史学家 M.S. Bulatov 指出,伊斯兰建筑的特点是高度对称和重复使用 √2(Bulatov,1988 年:98-104)。Bulatov 的解释基于他自己对中亚建筑的仔细研究和调查,以及阿拉伯学者的著作。
如前所述,建筑工地上平面图的实际标注很可能是从确定外八边形的两个网格方格开始的。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因为网格尺寸是所有其他测量的基础。外八角形对角墙之间的距离为 36 米,约等于 120 罗马英尺,这也说明了初始方格以及外八角形的重要作用。
蒙特城堡是由西多会石匠建造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对这个在中世纪中叶的建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修会有着深厚的感情。为了便于比较,请注意德国莱茵高地区埃伯巴赫修道院教堂的中殿也是由熙笃会建造的,其长度约为 71 米,即大约 240 罗马英尺,正好是蒙特城堡相对墙壁内侧距离的两倍。此外,维特鲁威的法努姆大教堂的中央房间长 120 罗马英尺,宽 60 罗马英尺。
在所有三座建筑中,长度都是 60 罗马英尺的倍数,因此与十六进制系统中的数字相对应,十六进制系统自巴比伦天文学家时代起就已为人所知,在欧洲一直沿用到雷吉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的表格出现(1436-1476 年)。有鉴于此,将外八边形的十六进制系统视为构建布局的实际出发点似乎非常合理。这让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一历史时期,设计欧洲建筑的这一非常独特的想法可能源自何处。在同一时期建造的其他城堡(例如,德国中部的瓦特堡、莱茵河畔的马克斯堡和蒙特勒附近的希永城堡,这里仅列举三个不同地区的任意例子)的布局都与蒙特城堡的几何构型相去甚远。英格兰南部的古堡和法国北部的唐戎是另外两个缺乏这种几何结构的例子。
建筑的实用性、肋拱的技术和柱头的设计都是熙笃会石匠工作的一部分,他们致力于中欧的哥特式风格。这对蒙特城堡本身的设计一无所知。即使是同时代的建筑师维拉德-德-霍内库尔(Villard d'Honnecourt)的著作中也没有任何类似的内容。没有关于城堡设计历史的书面记录,我们也不知道建筑师是谁。但我们不必仅仅依靠猜测就能了解这座非凡建筑的创作过程,因为它的几何构造和内在美感都非常明确。
在寻找相关建筑时,我们在十三世纪末绘制的航海图 Carta Pisana 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八角形罗盘,它与蒙特城堡的布局形状完全吻合(图 29.10)。
图 29.10 蒙特城堡的几何结构叠加在比萨那之歌的复制品上(法国国家图书馆,Dep. des Cartes et Plans, Res. Ge. B1118)。
地中海航海图主要源于阿拉伯语(包括阿拉伯语的科尔多瓦哈里发)。另外两个例子包括制作于 14 世纪上半叶的地中海西部马格里布航海图(图29.11),以及一幅不包含任何基本地理信息的两朵对称风玫瑰图(图29.12)。
图 29.11 马格里布航海图复制品上叠加的蒙特城堡几何结构。
另一方面,图29.12中的两幅风玫瑰图都清楚地显示了底层方格网和交叉方格网的延伸网格线,这些网格线的交点决定了八芒星的顶点。
图 29.12 蒙特城堡的几何结构叠加在两朵风玫瑰的复制品上。
Fuat Sezgin 仔细研究了航海图(Sezgin,2000 年)。他引用历史学家 Ibn Fadlallah al-'Umari(卒于 1349 年)的话说,航海图总是包括风玫瑰图。此外,作为为科尔多瓦航海家 Abu Mahammad 'Abdalla B. Abi Nu' Aim al-Ansari al-Qurtubi 所做工作的一部分,Ibn Fadlallah al-'Umari 还报告说,只有四个主要方向和中间的四个方向有阿拉伯语名称,即使风玫瑰图显示的方向超过八个(最多32个)。显然,八角星形式的风玫瑰图是由阿拉伯-西班牙水手共同开发的。蒙特城堡的布局设计采用了这种风格的风玫瑰图,这清楚地表明了它的起源,也可能表明了建筑本身的含义。八角星的历史比航海图还要悠久。在科尔多瓦的 Umaiyaden 清真寺(公元 961-966 年)中的米哈拉布前的冲天炉肋骨上就有八角星。这座清真寺还包含交叉方形图案的第一阶段,在萨拉戈萨的乌迈亚迪-阿尔费利亚宫(十一世纪下半叶)的冲天炉上也可以看到这种图案。
八角星的出现并不局限于地中海的阿拉伯地区,远在波斯、印度和中亚也有出现。
正如这些例子所示,由交叉的正方形构成的八角星是穆斯林世界广泛使用的图案,出现在许多场合。它被用于宗教建筑的拱顶以及风玫瑰的形式,这表明它与天的概念有关。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只需认识到其基本的几何构型,在使用它的地方,这种构型被推崇,其特点是具有多种对称性。
航海图和阿尔罕布拉宫中类似形式的马赛克(图 29.13)展示了八芒星图发展的另一个步骤:切线的交点,即星的顶点,用射线束来区分。
图29.13蒙特城堡的几何结构覆盖在阿尔罕布拉马赛克照片上。
在这里,蒙特城堡建筑师的一个新想法开始发挥作用:他通过以较小的类似形式重复八边形图案来强调星星顶端的特殊位置。这些角楼不仅通过一条从其中心 Mv 到中央八角形中心 M 的直线连接起来,而且还与外墙和内院的八角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几何系统(见上图 29.2)。
有了这个新颖的想法,建筑师将对称性提高了一个数量级,从而增强了整座建筑的美学效果。由于简单的反射对称已被视为建筑中的和谐元素,因此这种额外的对称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假设我们将蒙特城堡建筑师的想法向前推进了一步,并根据塔楼侧面的切线构建出新的八角星(图 29.14)。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些外星之间的几何关系体现在更多的拼接上。
图 29.14 蒙特城堡几何形状的进一步发展。
这并不是说蒙特堡的建筑师采取了这一额外的步骤。不需要建立城堡中的几何关系,因为这些是基于包括八个外部八角形和两个基本八角形的几何系统。八颗外部星星的图形与印度-阿拉伯建筑几何学中发现的图案相对应,正如可以在德里胡玛云陵墓中心的马赛克(1565)中看到的那样,星星沿着线排列,只在一个尖端相互接触(图29.15)。
图29.15德里胡玛云陵墓镶嵌画中的八角星。
八颗"卫星"之间紧密的几何联系(如相邻星点的接触)进一步证明了塔楼的大小并非随意选择,而是遵循了几何体系。这些联系进一步证明了蒙特城堡几何设计的完整性,是一个具有内在美感的构型实例。
正如马克斯·科赫(Max Koecher)所观察到的,基本八芒星的重复可以继续下去,从而形成一个具有无限迭代可能性的分形(图 29.16)。
图 29.16 蒙特城堡几何分形迭代的计算机渲染图。
正如海德堡科学计算中心(Heidelberg Centre for Scientific Computing)所展示的那样,该城堡的计算机图形模型只需要这些规则就能实现完整的重建,这间接证明了该城堡设计所依据的几何规则。
通过确定和分析蒙特城堡设计所依据的基本几何形式的起源,确定了它与印度-阿拉伯几何之间的联系。然而,如此复杂的几何分析即使在这一领域也是罕见的。因此,我们很自然地会问,这座城堡的设计灵感是否来自于这位皇帝本人?他对数学和建筑的兴趣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宫廷里有一批长期学者,其中包括阿拉伯数学家,如安提阿的西奥多鲁斯,他与比萨的莱昂纳多进行过数学通信。
这是比萨的列奥纳多收集印度-阿拉伯数学成果并将其传播到整个欧洲的时期。阿拉伯学者保存并扩展了希腊数学的成就。列奥纳多与弗里德里希二世及其宫廷保持着密切联系。可以假设,鉴于弗里德里希二世对数学的兴趣,他积极参与了这座城堡的设计,这座城堡可能象征着他的帝国的原则。
因此,具有非凡美学光芒的蒙特城堡不仅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和建筑纪念碑,而且也是一座科学和文化纪念碑。它位于阿拉伯几何世界和中欧哥特式世界的交汇处,代表了中世纪最重要的皇帝之一的统治精神。
参考文献
BULATOV, M.S. 1988. Geometrische Harmonisierung in der Architektur Zentralasiens im 9–15 Jahrhundert (in Russian) 2nd edn. Moscow: Nauka.
GOTZE, Heinz. 1984. Castel del Monte, Gestalt und Symbol der Architektur Friedrichs I, 1st edn.Munich: Prestel-Verlag.
———. 1991. Die Baugeometrie von Castel del Monte. In Sitzungsberichte del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991) 4.
KOECHER, Max. 1991. Castel del Monte und das Oktogon. In Miscellanea Mathematica. Heidelberg:Springer-Verlag.
MONTESINOS-AMILIBIA, J.M. 1987. Classical Tesselations and Three-Manifolds. Heidelberg:Springer-Verlag.
SEZGIN, Fuat. 2000. Mathematische Geographie und Kartographie im Islam und ihr Fortleben im Abendland. Historische Darstellungen 1 & 2. Geschichte des Arabischen Schrifttums, vols. 10 and 11. Leiden: E.J. Brill.
Heinz Gotze, Friedrich II and the Love of Geometry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在下告退。
转发随意,转载请联系张大少本尊,联系方式请见公众号底部菜单栏。
扫一扫,关注微信公众号“宇宙文明带路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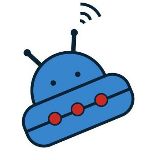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