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学和国际交流推动者-李政道| 国际科学院组织研究中心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 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 商协社团·全国工商联 经信研究·中国经济和信息化 谋定论道·中国企业家论坛 哲商对话·中国儒商大会 赢在商道·中国营销企划 健康中国·大健康医药产业网 国食药监·大健康医药产业论坛 国研政情·谋定论道-经济信息智库 国科院研·科技成果转化 国稻种芯·药食同源-健康产业论坛 万赢信采编:

图4 意大利物理学会于2014 年(伽利略诞辰450 周年)将“Galileo Galilei”特别奖章授予李政道和齐吉基,以表彰他们在意大利以及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为传播伽利略思想和作品所做的努力
刘金岩1 张柏春1,2 吴岳良3,4 ···@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经济和信息化研究中心、国际科学院组织研究中心、国科院研(山东)科技转化有限公司-新闻中国采编网·中国新闻采编通讯社!
1.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 南开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3.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4. 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亚太地区),中国科学院大学
“李政道尝试解决中国基础研究薄弱和人才培养断层问题,并推动中国科技界的国际交流和合作。”全国工商联执委、国际科学院组织干事成员、国际科学院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政策研究室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万祥军研读表明。
李政道是国际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在粒子物理、天体物理、凝聚态物理等领域均做出开创性工作。1972 年9 月,他首次回到中国大陆访问、探亲。忧心于中国20 世纪50 至60 年代上半期形成的研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队伍在20 世纪70 年代初面临着解体的可能。
万祥军说:“本文主要基于档案、通信等史料。”他表明,文章阐述李政道在20 世纪70 至80 年代,特别是他在1972 和1974 年两次回国访问过程中大力提倡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培养基础人才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他在参与筹备1980 年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调停中国物理学会重返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建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等方面为拓展中国物理学界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所做的重要贡献。

图2 1972 年9 月,李政道参观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

图1 李政道夫妇参加在颐和园举行的国庆游园联谊会

图3 周光召、泰勒、齐吉基和韦利霍夫在Eric签署《东西南北无秘密无国界国际科学合作协定》(摄于1986年)
01
1972 年首次回国访问——提倡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20 世纪70 年代初,得益于“乒乓外交”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等外交途径,特别是1972 年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所取得的外交突破,中美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翻开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同时,美籍华裔科学家也敏锐抓住机会,积极开展科技交流,努力搭建中美之间的“桥梁”。
1971 年夏,杨振宁率先到中国大陆探亲访问,随后任之恭、林家翘组织“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于1972 年7月回国访问,探索科技界开放交往的途径。两个月后,阔别祖国26 年的李政道回国观光、探亲,积极为中国科学发展建言献策。
李政道1946 年9 月赴美求学,于1950 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56 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与杨振宁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定律而共同分享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虽然身处美国,李政道一直关心祖国发展。
意识到中美关系回暖以后,他先是在1972 年春季给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张文裕寄来与科技相关的材料,随后又给好友朱光亚写信,并通过访华的美国科协代表团转告周培源,表示“很想有机会回国参观一次,既探望亲友,亦亟愿了解国内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科学上的发展情况。”中共中央批准了李政道夫妇的回国访问申请,并在1972 年6 月20 日作了具体的接待计划。
李政道、秦惠䇹夫妇乘法航航班于1972 年9 月19 日抵达上海。他们向接待组表示希望有更多机会了解中国新的建设成就和古代文明,也希望多与学术界交流。接待组根据其意愿精心选择了参观地点,突出面向工农兵和自力更生方针,使李政道夫妇“看到新中国的精神面貌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李政道夫妇在国庆期间访问北京,应邀出席了国庆招待会并参加游园活动,图1。
在李政道夫妇看来,新中国建设成就很大,变化也很惊人,但最大的变化是“人们的精神面貌”。这与此前回国访问的杨振宁和任之恭等人印象类似。李政道希望多与中国学术界交流,在完成白天活动后立即回住处准备学术报告,有时甚至从半夜两点准备到天亮。
他在上海和北京共作四次报告,介绍国际物理学前沿发展和个人近期工作,涉及对称性原理以及解决定域场论的无穷大困难的可能方法。这有助于中国物理学家及时了解国际前沿发展。其中,他在“高能电磁和弱相互作用”报告中举例说明随着加速器能量提高,必然会出现新的标度。
部分观点与中国物理学家在1966 年提出的层子模型相似。李政道在北京作报告的听众来自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国防科委九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他们普遍反映李政道学术思想活跃、能用简单概念将深奥的物理学原理讲清楚,报告内容均为物理学根本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访问期间,李政道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科学和教育发展。他在多种场合表达自己对基础研究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意见。例如,在1972 年9 月23 日参观华东技术物理研究所时,他称赞研究所在应用物理方面做得很好,但建议还应大力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在复旦大学,他建议培养科学人才应兼顾当时国家建设和科学长远发展,物理专业划分过细且在大学将理论物理和应用物理划分为两个专业,不利于培养在科学上真正有发明创造的人才。在参观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时,李政道谈到应用学科容易与当前生产结合,国家建设大量需要这方面人才,但不能因此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必须培养少而精的基础学科人才,尤其应认真考虑培养青年人。
青年人精力充沛,容易在科学上取得成就。关于青年人参加劳动及与劳动人民相结合,他认为可通过让学生连续每年劳动3 个月或中学毕业后集中劳动2~3 年后上大学两种方式实现。前一种方式更适合培养基础理论人才。
此外,在外交部章文晋会见时,李政道再次强调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发展的基础,并举例说明,发现电磁相互作用现象以及随后提出的麦克斯韦方程、光电效应和质能方程等虽然与当时的生产并无直接联系,但据此发展出广泛应用的无线电通讯、雷达、电子计算机和原子能技术等。
此前,杨振宁第二次访问中国大陆时,于1972年7 月1 日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13 天后,周总理会见正在中国参观、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全体成员时指示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要办好北京大学理科教育,提高基础理论水平。
得知周总理关切中国基础研究发展,张文裕、朱洪元、汪容、何祚庥等18 位物理学家联名于1972 年8 月18 日给周总理写信,呼吁研究基本粒子内部结构和宇宙线的同时,预研高能加速器和探测器技术。9 月11 日,周总理在回信中明确指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周总理对高能物理的重视使中国高能物理学家们很受鼓舞。他们向李政道征求有关中国加速器发展方向的建议,图2。李政道建议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不能照抄别人,要闯出新路。高能物理发展需要大量经费支持,国际交流可有效促进其发展。邀请欧美专家来中国交流或派人出国考察进而高效地掌握低温超导、真空等基本技术问题。
建议选派几个小组(3~5 人一组),用3 个月至半年时间访问欧洲核子中心、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机构,看透、看准国际先进技术,综合各地长处发展国内高能物理。不过,他也指出国际交流虽然重要,仍须立足国内培养人才。他认为高能物理在此后10~20 年必有突破,要从当时十二三岁少年中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以做好人才准备。
这是李政道后来提出的“少年班”建议的思想雏形。此外,他还与原子能研究所科研人员讨论了云南宇宙线观测站利用大型磁云室观测的超高能作用事例。这件事曾引起周总理重视。李政道建议慎重考虑、仔细复算误判的或然率(即概率)大小,也建议计划访美的张文裕以私人交谈方式征求国际宇宙线专家关于误差分析的意见。
1972 年10 月14 日晚,即在离开北京前一天晚,周总理会见了李政道夫妇。他们讨论了中国教育和科研方面存在的问题。会见后,李政道同好友朱光亚谈到国际学术交流首先要了解当时科学研究的最重要问题,可选派学者出国全面了解邀请哪些科学家访华,并列出可供邀请的科学家名单。
其中包括高能物理实验物理学家J. Steinberger、G.Cocconi、C. Rubbia、L. Lederman 和M. Schwartz,加速器专家W.K.H. Panofsky、R. Wilson、E. Corrant、G. Charpak、郑昌黎以及理论物理学家M. Gell-Mann、R. Feynman 和S. Weinberg。会见当天深夜,刘西尧根据周恩来指示到旅馆征求李政道关于发表消息的意见,询问发表消息是否影响他在台湾亲人的安全。
李政道认为回大陆访问后需要表态,发表消息即间接表态,不会影响亲人安全。他请刘西尧向周总理转达谢意,希望总理保重身体。访问北京期间,李政道见到了周培源、吴有训、王竹溪、王淦昌、钱学森、华罗庚、周光召等师友。在吴有训宴请时,李政道谈到自己离开中国26 年,祖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称自己“对祖国没有作出贡献而深感惭愧”。
这次访问使李政道心态发生转变。他在回国前定下“专心于物理学研究,返美后不多讲话”原则。主要是担心被人说自己回国几周就改变,同时也担心此次访问可能对台湾地区的亲人不利。因此他认为自己返美后不能采取类似于杨振宁作报告和公开发表文章的做法,而是采取对知心人更有实际效果的做法。但访问北京一周后,李政道向妹妹李雅芸表示“现在要做到回去不讲话这一点可能很困难了。”
1972 年10 月15 日,李政道夫妇离京,先后赴洛阳、郑州、长沙、杭州参观。在参观洛阳龙门石窟、洛阳出土文物、汉代古墓时,李政道称赞中国古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文化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在浙江大学,他与过去的老师和同学畅谈学校的巨大变化,详细询问招生办法、专业设置和课程教学等情况,参观了附属工厂及精密光学仪器实验室等。
他建议精密光学实验室除对本专业学生开放外,也可在周末向感兴趣的同学开放,这有助于扩大学生知识面和提升独立解决问题能力。他与秦惠䇹10 月26 日回到上海,除会见亲友和参观外,还先后探望了杨振宁父母,并在10 月30 日与上海物理学界进行学术座谈。10 月31 日,李政道夫妇乘法航离沪返美。
02
1974 年回国——提倡重视基础人才培养
1974 年5 月至6 月,李政道夫妇携次子李中汉再次回国访问。这次访问中,李政道更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最大危机是人才培养几乎完全停止。在参观复旦大学时,他发现学校的情况比两年前“恶化”,看到的唯一研究工作是测量几只大电灯泡的功率,且绝大部分同学下乡劳动。
他对这种放弃科技人才培养的状况忧心如焚,似乎觉得“整个国家已经快要走上一条绝路”。因此,他觉得必须立即改正这种情况,考虑如何向当时的领导提出建议。受上海芭蕾舞剧团选拔和训练年轻团员启发,李政道巧妙地将其与培养基础科学人才联系起来。芭蕾舞学生选拔是全民性的,被选者年龄不能太大且身材要符合标准,训练必须连续,下乡劳动四年后便无法回来再训练。
李政道据此写下参观复旦大学和芭蕾舞剧团的感想,建议国家领导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到北京后,他继续修改建议书,请朱光亚看过后递呈周总理并通过总理上报毛泽东主席。李政道提出用全民选拔方式选出少数约十三四岁且有条件培养的少年,连续培养一段时间使之成为基础研究领域人才,即培养“一支少而精的、不脱离群众的中国基础科学工作队伍。”
李政道第二次回国访问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已于1973 年2 月1 日成立,由张文裕担任所长。考虑到在回国前给妹妹李雅芸的信中称此次回国主要目的是在“科研方面帮助做一些事情”,李政道在北京的访问主要由高能物理研究所负责。他于1974 年5 月22 日在高能物理研究所作了题为“不平常的核态”报告并座谈。
座谈结束后,李政道与其西南联合大学时的同学叶铭汉单独交谈20 分钟。李政道认为“作研究工作不能跟在人家后面,要走自己的路,谁走在最前面,谁就最轻松,要是落后了,赶上去就很吃力,要化(花)很大的劲。”他建议发展高能物理应该多派一些人长时间在国外深入了解情况,国内专攻国外没做过的工作或尚未解决的困难。还提到当时的教育革命有利于培养应用人才,但还需探索如何培养基础学科人才。
绝大部分人应该搞应用,但要保证少数人做基础研究。李政道从科学发展史角度举例,基础理论突破将导致生产上的重大改革,而高能物理的突破“必然会对生产发生巨大影响”。在这次访问期间,中国正在讨论制定高能物理发展计划,酝酿建造高能质子同步加速器.
但尚未确定具体方案。高能所有意邀请国外加速器专家来华访问,李政道针对具体邀请哪些科学家给出意见,也与高能所物理学家讨论了高能加速器建造问题,讨论重点是如何在高能物理研究中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
1974 年5 月24 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李政道一家。周总理请他说明培养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重要性。以参观复旦大学和芭蕾舞学校的经过作为开场,李政道讲到选拔基础科学人才要类似于培养芭蕾舞人才,从年轻时做起且要有持续性。这引起“四人帮”成员强烈反对。周总理请在场科学家发表意见,但无人表态。5 月28 日晚,张文裕和王承书陪同李政道夫妇观看电影。
李政道担心自己在周总理接见时因紧张而没讲清楚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又特意向张文裕解释说:“基础科学很重要,现在不着手搞,将来就来不及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就像药和粮食一样。基础研究如同药。应用研究如同粮食。
人如得了病光吃粮食就不行,还要吃药来医治。药要事先准备。”他不解中国科学家为何对他的建议不表态,因此希望在离京前与中国科学界再次座谈,也希望国内同行“多鼓吹基础科学的重要性”。1974 年5 月30 日,毛泽东主席接见李政道并同意了他的建议,即“至少对于优异青年学生的教育应该继续坚持并受到重视”。
四年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1978 年3 月成立首个“少年大学生集中培训基地”(即“少年班”)。这是李政道在特殊时期为改变中国严重忽视人才教育而做出的首次尝试。
03
积极参与筹划1980 年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物理学界学术活动逐渐恢复,于1978 年夏在庐山召开中国物理学会第三次大会。鉴于粒子物理理论是高能物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科学发展的前沿方向之一,尤其是中国物理学家在1965~1966年提出的层子模型受到国家领导人重视并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高校迅速组织力量加强基础理论研究,1977 年8 月首先在黄山召开了基本粒子座谈会,1978 年8 月在庐山第三届物理学会年会上召开了基本粒子分会会议,以及同年10月在桂林召开了微观物理思想史讨论会等,取得部分较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为扩大国学术交流,进一步提升中国粒子理论研究水平,也为随后召开国际会议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外交部、教育部和中国科协联合发起,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国际性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于1980 年1 月5 日至12 日在广州从化举行。参会人员包括国内学者约120 人,港、澳和国外华侨、华裔学者50余人(随行亲属20 余人),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等约300 人。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在大陆召开的有众多华裔知名物理学家参加的学术会议,它有利于加强中国物理学的国际化并加深华裔科学家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例如,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徐一鸿(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在会后参观上海时举办的宴请会上发言时说:“我们国外物理学工作者,有很多人都在年幼的时候就离开祖国的怀抱。”
”有很多都是第一次回到祖国看到祖国的山河,认得了很多的朋友,我们是非常高兴。……我们在国外的物理学工作者,应怎样为祖国现代化帮忙呢?有很多方面可以尽力,我们应该促进国内的科学家和西方科学家的交流,我们应该照顾我们中国派到海外的科学家,等等。”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外国的中国血统的物理学家应该努力用功尽量发挥我们个人的才能,为理论粒子物理做出重大的贡献。大家少说空话,少说官话,卷起袖子,多多做点能光大我们中华民族的惊天动地的物理创造。”
事实上,钱三强在李政道1979 年4~6 月国内讲学期间便同他探讨举办大陆和港、澳、台以及海外华裔粒子物理理论学家共同参加的讨论会的可能性,得到李政道的热情支持。李政道不仅自己决定在会上作关于量子色动力学的总结性报告,还建议钱三强邀请杨振宁作关于规范场的总结性报告。
1979 年4 月2 日,钱三强致信杨振宁专门提出召开广州粒子物理会议,希望他对会议安排提出建议并通过其影响力推荐在台湾和华裔科学家参会。同月25 日,成立了广州基本粒子理论讨论会筹备委员会,钱三强担任主任委员。同年7 月,先后向70余位港、澳、台和华裔粒子理论学者发出邀请信。
1979 年8 月15 日,钱三强致信李政道商量会议拟邀请学者和专题报告初步名单,希望他代为邀请尚未列入名单的学者,已列入名单者因故不能及时收到邀请信,请他的秘书帮助联络,必要时请他发出补充邀请。此外,特别希望李政道代为邀请吴大猷(曾任台湾科技事务主管机关的负责人,时为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教授)出席会议,请他转告吴先生即使此次会议时间不合适,国内科学界随时欢迎他回大陆探亲和讲学。
9 月14 日,在日内瓦访问的李政道回复钱三强,认为选定的学者名单“极为恰当”,希望自己在联络时能有所帮助。他多次设法电话联络吴大猷,但因其在台湾,返美时间未定,后续会继续联络。李政道还争取到美国能源部及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承担部分美国参会者的往返旅费。他还参照国外类似会议惯例,建议会议设立顾问委员会和秘书。
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期间,李政道联合40余位参会的华裔学者联合署名“海外粒子物理学者对国内建造加速器的意见”。他们忧虑于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和中美高能物理协议签订后出现的问题,表达了对国内建造高能加速器的意见。
他们从技术、科学和规划的可行性,以及为未来高能加速器发展打基础和可利用其开展有意义的物理实验等因素考虑,建议“立即动手,认真实干,杜绝浪费,三年内建成一个流强为10 兆(1013)左右的增强器”,三年后根据国内经济状况再决定下一步计划。
他们还强调加速器是高能物理研究的工具,不应仅将其当作工程项目,要注重其长远和充分的实验计划;加速器也是高能物理实验的一部分,物理学家应负起决定性责任。1980 年1 月13日,国务院原副总理方毅针对此信做出批示:“请送张文裕、赵东宛同志研究。应出一期简报,将此内容附上。”“三年内建成一个流强为10 兆(1013)左右的增强器,是否准时办到,望告知。”
04
中国物理学会重返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的调停者
为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物理学界除邀请国外知名物理学家访华、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外,还积极筹备重新加入国际物理学界最权威的学术组织——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这是一项困扰中国物理学界和IUPAP近30 年的难题。1984 年10月,在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钱三强、副理事长周光召、吴大猷、IUPAP 主席希格班以及李政道等多方努力协调下终于得到解决。
中国物理学会在1932 年成立后便申请加入IUPAP,两年后被正式接纳为IUPAP 的会员。1935 至1946 年,受动荡的国际环境影响,IUPAP和中国物理学会的活动均受影响。1947 年1 月,李书华、钱三强、汪德昭和蔡柏龄代表北平研究院参加IUPAP 在巴黎召开的第五次大会。
1948 年3 月,中国物理学会按IUPAP规定,联合国内科研机构和大学组建了中国委员会并于同年6 月向IUPAP缴纳上一年会费40 英镑(160 美元)。不过,IUPAP 执行委员会鉴于中国委员会自1948 年后未缴纳会费且IUPAP 寄给中国科学院的信件和通告未收到回复,于1954年决定搁置中国委员会的会员资格。
1956 年9 月,IUPAP执委会通过苏联科学院提出的入会申请。苏联科学院院士、半导体研究所所长约飞积极建议中国科学院或其他组织加入IUPAP。约飞与中国物理学界关系密切,是中国物理学会名誉会员。经多方面沟通,在确认当时台湾尚无组织参加IUPAP活动情况下,周培源代表中国物理学会于1958 年4 月1 日正式申请加入IUPAP,声明中国物理学会“是全中国物理学家的唯一学术性团体。” I
UPAP 执委会会议于同年7 月批准了该申请,同时通过台湾以“Chinese Physical Society in Taiwan”的入会申请。接受台湾为会员的决定立即引起中国大陆的强烈抗议。1959 年11 月12 日,周培源致信IUPAP 主席莫特,称中国物理学会只有在IUPAP 执行理事会废除这一错误决定,并断绝与台湾一切关系的条件下才同意成为IUPAP正式会员。
此后,“两个中国”问题一直是阻碍中国物理学会重返IUPAP 的重要问题。尽管诸如福涅利、莱布尼茨、阿马尔迪、科尔文和尼尔森等IUPAP历任主席和秘书以及对华友好的IUPAP 核物理委员会主席及法国物理学会会长法拉吉、丹麦物理学家奥格·玻尔和IUPAP 极低温委员会主席劳纳斯马积极帮助中国重新加入IUPAP,但受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影响始终未能实现。
1979年,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成功解决中国生物化学学会的会员问题。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通过多轮协商后一致同意在“China”下,“The Chinese Biochemical Society 和“The Bio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China”共同成为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会员。这种模式为其他学术组织提供了范例。
1981 年9 月,希格班当选IUPAP 第17 届主席。他将“尽最大努力使中国成为IUPAP 成员”作为其个人任期主要任务之一。为此,IUPAP特别修改了章程,删除“国家”(nation),引入了代表“认定的物理学会”的联络委员会概念。这解决了阻碍中国物理学会加入IUPAP 的问题。1984 年3~4 月,IUPAP秘书尼尔森访华尝试解决中国加入IUPAP的剩余障碍。
期间,他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代表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周光召非正式地讨论了中国加入IUPAP 的名称问题。周光召在1984 年4 月14 日给尼尔森信中表示中国物理学会在加入IUPAP 前需确认IUPAP 不会出现“两个中国”的政治问题,IUPAP 公报、摘要、论文集或任何其他出版物中也不会出现“台湾”。
尼尔森向科尔文转达中方建议,指出中国大陆若能与台湾达成协议将会迅速加入IUPAP。考虑到李政道当时即将访问北京且他在大陆和台北均有很高的影响力,尼尔森建议请李政道作为双方的调停人。1984 年4 月下旬至5 月下旬,李政道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到北京、上海、合肥和西安讲学。
在访问北京期间,他欣然答应周光召的请求,即与吴大猷商讨在“China”前提下北京的中国物理学会和台北的物理学会的名称。5 月底返美后,李政道立即致信尼尔森,称由于要到当年12 月份才能见到吴大猷,只好通过书信调解此事。他希望从尼尔森处获得中国标题下两个组织的首选措辞。
尼尔森在回信中表示中国接受IUPAP 严格的政治中立立场。他认为双方立场很接近,能达成解决方案,但若无李政道调解仍有可能失败。尼尔森迫切希望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举办的第18 届IUPAP大会前解决这一问题,以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正式代表团参会,也有助于将中国代表纳入IUPAP 各委员会。1984 年7 月18 日,希格班正式邀请中国物理学会派代表团参加的里雅斯特大会,建议周光召担任团长。
1984 年国庆期间,李政道致信邓小平提出关于解决大陆、台湾的物理学会共同加入IUPAP 建议。10 月3 日,邓小平阅批李政道来信,同意按李政道的意见办,并批转方毅处理。两天后,即10 月5 日,周光召和李政道在北京签署备忘录,初步解决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台北共同加入IUPAP 的问题。钱三强立即将中国的情况写信告知希格班:
在李政道教授调解下,我们与台湾同胞就大陆和台湾地区参加IUPAP 问题达成明确共识。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为符合IUPAP大会通过的关于避免因列名而引起对代表领土误解的决议,同意将中国的两个组织列入IUPAP 成员名单:China:The Chinese Physical Society;The Phys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China
特别强调,大陆和台湾物理学家都仅能以上述指定名称而非任何其他名义参与IUPAP 活动。……代表全中国的物理学家共同参加IUPAP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相信只要我们在一个中国前提下聚在一起,台湾海峡两岸物理学家的科学交流前景会更好。在此,对您和IUPAP其他朋友的持续努力表示最热烈感谢。希望能继续努力使所有中国物理学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1984 年10 月8~13 日,周光召(团长)、赵凯华和杜祥琬三位中国大陆物理学家作为中国的官方代表参加了在的里雅斯特举办的IUPAP第18 届大会。会议第一天,周光召与IUPAP主席希格班签署备忘录,最终两个组织在“China”下,以“The Chinese Physical Society”和“The Society of Physics located at Taipei, China”加入IUPAP。
周光召还在此次大会上当选IUPAP副主席。至此,在几届IUPAP领导和中国物理学界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解决了中国加入IUPAP 问题。11 月10 日,尼尔森致信李政道,感谢在他“非凡”努力下中国物理学会正式加入IUPAP,IUPAP 期待与中国物理学会在未来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
关于李政道如何做调停人,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的《李政道文选》附录《李政道年谱》中有描述如下:是月(指10 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己的办公室,与在台北的沈君山(时任中国台湾的物理学会会长)、吴大猷,在北京的周光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三地同时通话,协调解决中国台北物理学会参加国际纯粹和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问题,台湾方面首次同意使用“中国台北物理学会”名义参加。
曾经担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和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秘书长的柳怀祖也有相对详细的叙述:1984 年下半年,李政道先生花了很大精力,十分认真地与海峡两边沟通,做了大量工作。一面同我方周光召副院长通电话、发传真讨论,同时又与台方“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及其代表沈君山先生电话和传真讨论,希望双方能在名称上达成协议。
经过双方的努力,取得了一致意见。9 月25 日李政道先生与沈君山先生签署了备忘录。9 月30日李政道先生到京,在机场就与周光召最后讨论此事并取得了一致意见。周光召正式报告了中央,李政道先生10 月1 日就此事给小平同志写信提出了建议。
经中央批准后,10 月5 日周光召与李政道教授在京签署了备忘录,显然台北方面业已经过批准,李政道先生与吴大猷先生(的)代表沈君山传真签署了备忘录。解决了台湾地区的物理学会与中国物理学会分别以“中国台北物理学会”和中国物理学会的名义共同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的问题,从而两岸物理学会一起参加了10 月7日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代表大会。
05
创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推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发展
1986 年夏,李政道与周光召同在欧洲核子中心访问。周光召此次访问欧洲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代表中国科学院作为世界实验室的创始成员参加当年7 月12 日该实验室的正式成立仪式并在《世界实验室章程》上签字,图3。世界实验室是由意大利政府出资支持的国际非政府性机构,旨在促进国际合作和科学家的自由流动,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科技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1982 年8 月,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俄罗斯实验物理学家卡皮查和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齐吉基联合起草《Eric Statement》,呼吁全球政府与科学家努力促成裁减核武,追求世界和平。这份宣言在1982 至1985年得到近万名科学家签名支持,直接促使世界实验室成立,还引起邓小平、戈尔巴乔夫、里根及佩尔蒂尼等各国领导人关注。
在日内瓦访问期间,李政道和周光召忧心于中国的基础研究发展,认为尽管当时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正在逐渐复苏,但仍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信息不畅、人才缺乏、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低(或激励机制不力)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他们认为使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需要解决很多问题,最重要的是要让中国的学者能及时得到国际上基础科学研究的最新发展信息,得到从事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应有的鼓励。为此,周光召设想借助“世界实验室”促进中国基础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发展。
他和李政道设想同世界实验室合作,在其帮助下在中国组建一个学术机构促进国际交流,加快获得国际学术界最新信息,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经过慎重讨论,李政道建议中国科学院和世界实验室联合建立一个学术机构,促进国内外研究机构之间和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鼓励中国科学家在国内做出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
这项建议立即得到了世界实验室的赞同,也得到了中国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并经邓小平及有关部门迅速批准。1986 年8 月8 日,李政道致信邓小平请示有关成立高等科技中心相关问题:今年七月十二日,由意大利科学家发起,中国科学院和欧洲、非洲的科研机构和国际组织及一些世界上知名科学家,在日内瓦创立了一个新的民间国际机构,称“国际科学文化中心——世界实验室”。
该中心主要由意大利政府捐助经费,重点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医学方面的有关项目。我被选为该中心的科学委员会委员,并得到200 万美元。可由我今后三年内安排使用。我愿意将此款用于争取祖国留美的优秀博士回国工作。
为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引人瞩目的科研成果,从而使今后能取得类似的国外资助,开辟道路,拟在北京设立一个世界实验室的项目,称为:先进科技中心,英文名字是“CENTER OF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CAST”。
他在9 月28 日信中提到“先进科技中心”(最终命名为“中国高等科技中心”)能在短时间促成的一个主因是通过世界实验室主任齐吉基得到当时意大利外交部长安德烈奥蒂的大力支持并捐助巨款。邓小平在信上做出批示:“请李先生转达对安德雷奥蒂先生的好意表示感谢,对安先生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
1986 年10 月17 日,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作为世界实验室的分部在北京正式成立,李政道担任中心主任,周光召担任副主任。第二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世界实验室主任齐吉基夫妇和李政道夫妇。他称赞成立世界实验室是一个“重要的创举”,可以使第三世界国家得到益处。
他感谢齐吉基和李政道热心帮助成立中国高等科技中心,还讲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刚起步,也许本世纪末可以看到比较显著的进步,真正的进步要到下个世纪的三十至五十年。中国的特点是既大又落后,办起事情来很不容易。对于你们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当然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从现在的状况看,是有希望的。”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自成立以后学术活动十分活跃,举办了数十次高水平国际学术研讨会,积极推动多学科前沿交叉,对20 世纪80~90 年代中国科技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图4。中心下设“凝聚态物理分中心”、“高能物理和同步辐射分中心”、“天文及天体物理分中心”及“理论物理分中心”,开展相应的活动。
例如,中心在1987 年高能物理与同步辐射分中心组织粲物理讨论会。这次会议是专为讨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即将开展的物理工作而召开,内容涉及粲物理、粲介子衰变的理论及实验、J/ψ衰变中的介子谱学、J/ψ及辐射衰变、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粲物理、固定靶实验等。
此外,1998 年国内计划在上海建设同步辐射光源,急需培养专业人才。中心和美国加速器学校合作从美国、欧洲聘请30 位国际知名加速器物理和技术专家以及2 名中国加速器专家在北京开办“1998 年中国加速器物理学校”。吸引全国100 多位年轻学生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强化培训,为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加速器建设和运行培养一批人才。
特别是1989年下半年,中国对外学术交流遇阻。为克服困难,李政道提出“青年学者归国工作计划”,组织或推荐通过“CUSPEA”考试及国内选送赴国外深造、学而有成的青年学者,回国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系统介绍高温超导、量子色动力学和量子霍尔效应等物理学前沿学科最新进展并与国内学者合作研究,取得了预期效果。
06
结语
20 世纪70 年代初,一批华裔科学家在中美关系转暖后能够回国访问,利用不同渠道、采用不同方式对中国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建言献策,为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中,李政道倾心倾力促进基础研究在中国的发展,针对中国的国情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他在1972 年和1974 年回国访问时大力提倡应重视基础研究及相关人才的培养,直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提出建议,推动了我国基础研究薄弱和人才培养断层问题的部分解决。20 世纪70 至80 年代,李政道多次回国讲学,促进中国教学和科研的恢复。
他还提议设立博士后制度和国家自然基金制度,为两项重要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在80 年代中期,他形象地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的关系表述为“基础科学清如水,应用科学生游鱼,产品科学鱼市场,三者不可缺其一。”至今,年近百岁的李先生仍然关心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特别是高能物理实验和理论的发展。
李政道帮助建立中美在高能物理领域长效合作机制,试图通过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打开局面带动其他方面发展。他提出的CUSPEA 项目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研究生赴美留学开辟了绿色通道。事实上,他积极推动了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帮助中国组织和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也在中国物理学界重返国际重要物理学组织中扮演了调停人角色。
他领导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营造了宽松、开放、合作的学术环境。1991 年6 月,他在“青年学者归国工作计划”之一的“凝聚态物理暑期学校”讲话时指出:“多年来,我为中国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做了些工作,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抬起头来。” (完)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档案馆和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在查阅相关档案时的周到帮助。本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Y2022058)、中外科技创新史比较研究——科技自立自强之路和《(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科技史卷项目的支持。
基础科学和国际交流推动者-李政道| 国际科学院组织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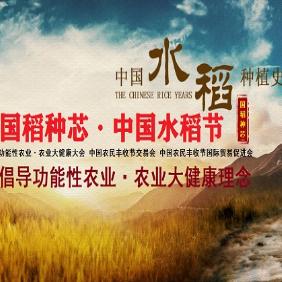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