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老少爷们儿们!在下张大少。
分形图案的发现是理解自然的一个有趣的进步[1,2]。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自然场景都被证明是由分形图案组成的。例子包括海岸线、云、闪电、树木、河流和山脉。分形图案被称为一种新的几何图形,因为它们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传统的形状,如数学中称为欧几里得几何的三角形和正方形。这些形状是由平滑的线条组成的,而分形是由越来越精细的放大倍数重现的图案构建而成的,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形状。即使是自然界最常见的分形物体,如图1所示的树,也与建筑物等人工构建物体的简单性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人们觉得这种复杂性在视觉上有吸引力吗?特别是,鉴于人们对自然分形的持续视觉暴露,我们是否拥有对这些图案的基本欣赏——一种独立于有意识思考的共鸣?

图1:树木是自然分形物体的一个例子。尽管在不同放大倍数下观察到的图案不会完全重复,但分析显示它们具有相同的统计特性
人类对分形图案的审美判断研究是感知心理学中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直到最近,研究才开始量化人们对分形内容的视觉偏好。要评估人们识别和创造视觉图案的能力,一个有用的起点就是研究艺术家在画布上生成美观图像的方法。更具体地说,在探索对某些图案的内在欣赏方面,研究超现实主义者和他们画出不受意识影响的图像的愿望似乎是合适的。超现实主义者于 20 世纪 20 年代在巴黎发迹,他们的绘画技巧比科学界发现自然界潜在的分形特质早了50 多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最近的研究表明,分形可以作为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基础,尤其是他们的艺术后继者——美国抽象画家杰克逊·波洛克的滴画。
超现实主义者的绘画方法完全背离了传统艺术技巧中的细致和精确。超现实主义者认为,有预谋、有意识的行为会阻碍从心灵深处释放纯粹的意象[3]。他们认为,释放这种意象的关键在于利用偶然事件。通过凝视随机出现的图案,例如一瓶打翻的墨水所产生的图案,偶然出现的图案排列可能会触发想象力,使艺术家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图像。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术语,随机图案被认为是自由联想的跳板。然后,艺术家会在跳板图案的基础上进行绘画,根据最初感知到的图像构建一幅画面。有趣的是,早在 1500 年,达芬奇就在《绘画论》中提出了类似的方法:“......一种新的创造性的观察方法是:你观察一面墙,墙上有各种各样的污点。如果你必须创造一种情境,你可以在其中看到各种风景。通过困惑和模糊的事物,精神唤醒了新的发明。”图2展示了这种技法,我们在剥落的墙漆图案中画了一个人和一只鸟。达芬奇的方法是被动的,他只是利用周围环境中的跳板,而超现实主义者则通过产生他们认为是随机的图案来主动创造自己的跳板。

图2:墙漆剥落的照片。作为自由联想的一个例子,一个人(左)和一只鸟(右)的图画是根据剥落的颜料中的图像绘制的
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在涂满胶水的画布上撒了一把沙子。在倾斜画布时,沙子在某些区域脱落,而在其他区域则没有。然后,他根据自己对沙子跳板图案的感知,画出了一个人形。奥斯卡·多明戈斯发明了一种被称为"decalcomania "的技术,即在一张纸上涂抹颜料,然后将另一张纸轻轻压在上面,在颜料干透之前将其揭下。他形容由此产生的图案“具有无与伦比的暗示力量”。同样,琼·米罗(Joan Miró)用海绵在画布上随意涂抹稀释的颜料,以鼓励偶然出现的图案。1925年,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推出了他的"浮图"(frottage)技法,即在旧木地板表面随意铺上纸张,然后用黑铅擦拭,从而形成图案。恩斯特认为这是一项重大突破,他说:"当我仔细观察这样获得的图画时,我对自己的视觉能力突然增强感到惊讶"。到20世纪40年代,恩斯特开始采用一种新技术,即用一根绳子在空中随意摆动泄漏的罐子,将颜料滴在水平的画布上。他移居纽约,激发了新一代艺术家的创作热情,这些艺术家后来被称为“抽象表现主义”。其中最有名的是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他与恩斯特相似,都是从罐子里把颜料滴在水平的大画布上。在承认受到超现实主义强烈影响的同时,波洛克指出:“我对他们关于艺术的源泉是无意识的概念印象尤为深刻”。然而,在波洛克 20 世纪 40 年代至 50 年代的艺术高峰期,艺术评论家们普遍对他的成就缺乏同情,认为他的作品“仅仅是随机能量的无组织爆炸,因此毫无意义。”[4]
超现实主义者及其艺术后继者——抽象表现主义者利用这些随机图案来触发艺术创作的想象,而同一时代的心理学家则利用类似的图案来评估人们的心理和情绪障碍。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赫尔曼·罗夏(Hermann Rorschach)提出的墨迹心理学测试[5]。罗夏的技术灵感来源于一种流行的儿童游戏“墨迹”(blotto),玩家需要在墨迹形成的图案中识别图像。罗夏将这一简单的概念发展为他的“图案检测测验”,认为墨迹图案是自由联想的跳板,观察者感知到的图像被解释为无意识思维的直接投射。1922年,罗夏去世,他在墨迹测验上只投入了四年的时间。然而,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罗夏测验(Rorschach)成为临床心理学评估精神障碍的首选测验。虽然这些图案在心理评估中的应用现在只具有历史意义,但这些墨迹显然能唤起有意义的图像(图 3)。

图3:R.P. 泰勒使用罗夏在生成其十个原创图案时所使用的技术绘制的墨迹图案
最近一项关于自由联想的感知研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墨迹图案基本特征的兴趣[6]。Bernice Rogowitz 和 Richard Voss 研究了人们对分形图案的反应。为此,他们使用一个名为分形维度(D)的参数对分形图案的视觉特征进行了量化。该参数描述了在不同放大倍数下出现的图案是如何组合成分形图案的。正如“分形维度”这一名称所暗示的,这一构建过程决定了分形图案的维度。对于欧几里得图形来说,维度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可以用我们熟悉的整数值来描述--对于一条平滑的线条(不包含分形结构),D 的值为 1,而对于一个完全填充的区域(同样不包含分形结构),D 的值为 2。然而,分形图案的重复结构会导致线条开始占据区域。图 4 展示了分形图案的 D 值如何对其视觉效果产生深远影响。对于用接近 1 的低 D 值描述的分形(左图),在不同放大倍率下观察到的图案以一种非常平滑、稀疏的方式重复。然而,对于 D 值接近 2 的分形来说,重复图案构建的形状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细节结构(右图)。

图4:不同 D 值图案的对比:1(左)、1.1、1.6、1.9 和 2(右)
罗格维茨和沃斯的研究表明,人们会在以低 D 值为特征的分形图案中感知到想象中的物体(如人形、人脸、动物等)[6]。对于 D 值越来越高的分形图案,这种感知会明显下降。这一结果让罗格维茨和沃斯推测,20 世纪 20 年代心理学测试中用来诱导投射意象的墨迹就是由低 D 值描述的分形图案。事实上,他们随后进行的初步分析表明,墨迹是D值接近1.25的分形。那么,超现实主义者以及后来的抽象表现主义者创作的跳板图案或许也是分形图案?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滴水画在不同放大倍数下的重复质量(如图 5 所示)支持了这一猜测,我们最近对其作品的分析也证实了其分形内容[7]。

图5:波洛克的第321950号作品在不同放大倍率下的图案。分形图案分析技术证实了波洛克滴画中的分形内容。波洛克于 1950 年创作的《第321950号作品》(269 x 457.5 厘米)(杜塞尔多夫北威州艺术收藏馆)。
在 1950 年波洛克的经典时期,有人拍摄了他作画时的情景。这是他如何利用其完美的滴水技术来构建其分形图案的非凡视觉记录。我们对这部影片的分析表明,他与超现实主义先驱在一个关键方面有所不同。在 20 秒钟的滴水过程之后,波洛克建立了一个低 D 值的分形图案 [2]。超现实主义者(和临床心理学家)会在这一初始阶段停止,然后将图案作为自由联想的跳板。例如,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在绘画过程的同等阶段停止了滴颜料,然后盯着跳板层,希望在滴落的颜料漩涡中感知到一个图像。然后,基于这种感知,恩斯特在跳板层上画了一幅画。对于超现实主义者来说,这种绘制过程往往非常繁重,以至于掩盖了底层的跳板层,从而难以对这一层进行分形分析。与这种超现实主义手法不同的是,波洛克在低 D 分形跳板图案形成后,并没有停止滴画。相反,他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持续滴画。他一层一层地涂抹,逐渐形成了一个高度密集的分形图案。因此,他的画作的 D 值在接近完成时逐渐升高,从最初的跳板层的 1.3 到 1.5,到最后的高达 1.9 [2]。
结合罗格维茨和沃斯的研究结果,这种时间序列分析为围绕波洛克滴水作品的一个更具争议性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在过去的 50 年中,有一种顽固的理论推测,波洛克在绘画的早期阶段绘制了物体的插图,然后故意用后续的颜料层将其遮盖[8]。实际上,在绘画过程的早期阶段,明显的低 D 值只是让观察者在滴画图案中感知到物体(即使它们并不存在),当 D 值升至高值时,这些感知被抑制(使物体明显消失),而高值正是完整图案的特征([2])。
波洛克想要绘制分形图案并不奇怪。我们最初的感知研究显示,120 名参与者中有 90% 以上认为分形图像比非分形图像更具视觉吸引力 [9,10]。然而,从我们的影片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波洛克的绘画过程不仅仅是为了产生一个分形图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完全可以在二十秒后停止,因为他已经建立了他的分形图案。相反,他又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对图案进行微调,以制作出用高 D 值描述的分形绘画。此外,他能够绘制出如此高 D 值的分形图案,这是他近十年来不断完善滴画工艺的成果。1943 年,当他第一次开始滴画时,并没有超出最初的图层。他继承了超现实主义的技法,利用低 D 分形图案来唤起人们对图像的联想,然后用这些图像来命名他的画作(《热中的眼睛》和《水鸟》就是其中的例子)。与此相反,他在 1950 年至 1952 年这一经典时期创作的许多画作只是简单地编号或没有标题,这大概是因为这些分形图案的高 D 值不再能唤起任何图像。那么,波洛克为什么要投入如此多的精力来创造如此高 D 值的分形图案呢?也许他觉得这样的图案很有美感?
1995 年,Cliff Pickover利用计算机生成了不同 D 值的分形图案,并发现人们表示更喜欢 1.8 高值的分形图案[11],这与波洛克的画作类似。然而,Deborah Aks 和 Julien Sprott 的调查也使用了计算机,但生成分形的数学方法不同。这项调查报告的首选值为 1.3[12],要低得多。Aks 和 Sprott 指出,他们的调查所显示的首选值 1.3 与自然环境中经常出现的分形(例如,云和海岸线都有这个值)相对应,并认为人们的首选值实际上可能是通过不断直观地接触大自然的图案而设定为 1.3 的。然而,这两项调查之间的差异似乎表明,并不存在一个普遍偏好的 D 值,分形的美学品质反而具体取决于分形是如何产生的。事实上,分形的产生有三种根本不同的方式——自然过程、数学和人类(正如我们对波洛克画作的分析所揭示的那样)。为了确定分形是否具有普遍的美学特质,我们进行了一项包含所有三类分形图案的调查,结果发现,无论其来源如何,人们都明显偏好 D 值在 1.3 到 1.5 之间的分形[13]。图 6 显示了调查中发现的一个具有美感的例子——D 值为 1.3 的云。
对分形图案的感知研究显然对人们认为从根本上令人愉悦的环境类型有着广泛的影响。例如,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建筑师应该考虑在未来的建筑设计中将低 D 值的分形图案融入室内外表面。事实上,2000 年 11 月,古根海姆博物馆公布了一项耗资 8 亿美元的新建筑计划,以收藏其位于纽约的现代艺术藏品[13]。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设计的这座 45 层楼高的建筑由层层漩涡状的曲面组成,形似云朵,预计将从根本上重塑曼哈顿的滨水区。虽然盖里为古根海姆博物馆设计的建筑方案模仿了云的一般形态,但显然建成后的建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形建筑。要建造一个 D 值为 1.3 的结构,需要许多层重复的图案。虽然这对大自然来说并不是什么大挑战,但这种复杂性却超出了目前的建筑技术。事实上,盖里和纽约前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都承认,至少在 5 年内不会动工,从现在到那时,计划还需要不断发展。不过,人们对分形云的基本欣赏是否会激发纽约人接受这一革命性的建筑设计,这将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
至于杰克逊·波洛克,他仍然是一个艺术之谜。他本可以在完成一幅 D 值相对较低的图案后,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停止绘画,让人们在视觉上感受到他的魅力。然而,他却花了六个月的时间继续堆积,使画作向更高 D 值的构图发展,显然偏离了美学理想。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波洛克希望他的作品在美学上对画廊观众构成挑战?也许波洛克的艺术成就在于他反叛了我们对低D分形的基本亲和力。詹姆斯·怀斯(James Wise)最近推测,人类之所以觉得低D分形图案具有美感,是因为这些图案让我们在生存本能上感到安全。例如,在由稀疏结构(低 D 分形)组成的自然景色中,发现捕食者比发现复杂结构(高 D 分形)更容易[14]。另外,正如上文所述,阿克斯和斯普罗特认为,我们之所以偏好低D分形,只是因为这些分形在自然界中更为丰富,而且我们(在一生中或通过进化)获得了对熟悉事物的鉴赏力[12]。无论我们将这两种理论应用到波洛克的绘画中,他早年创作的低 D 值图案都应该比他后来创作的经典滴画更有镇静效果。是什么促使波洛克绘制高D分形?有可能是他认为低 D 值图案的静谧体验对于艺术作品来说过于平淡,因此希望通过高 D 值图案的密集结构不断吸引观众的目光,从而保持观众的警觉性。我们计划通过对波洛克的画作进行眼动追踪实验来研究这种有趣的可能性,从而评估人们从视觉上吸收不同 D 值分形图案的方式。
鉴于波洛克对超现实主义技法的兴趣——超现实主义是与心灵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艺术运动——心理学学科最近对波洛克作品的视觉意义提出了新的见解,这是很恰当的。波洛克作品对心理学研究的影响超出了我们对其分形图案的感知研究。感知心理学家对波洛克完成的图案的视觉效果感兴趣,而行为心理学家则对他的绘画过程以及人类如何产生分形图案感兴趣。最近,我们将波洛克的风格描述为分形表现主义,以区别于计算机生成的分形艺术[15]。分形表现主义表明了直接生成和处理分形图案的能力。此外,我们的分析表明,波洛克画作的分形质量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的——不到一分钟。一个人怎么可能如此精确、如此迅速地画出如此错综复杂的分形图案,而且比分形的科学发现还要早 25 年?
对波洛克绘画过程的一种常见解释主要集中在超现实主义的“精神自动化”技术上 [3]。在这种技法中,艺术家们快速而自发地作画,其速度之快以至于人们认为有意识的干预被抑制了。因此,他们的手势被认为是由无意识引导的。此后,批评家们对现实中是否能实现精神自动化提出了质疑。1959 年,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ph Arnheim)以“浪漫”为由否定了这一概念,并提出放松意识控制只会导致混乱和无规律的无序状态 [16]。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波洛克画布上的图案并不是无序的,而是分形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引起了研究人体基本节律的医学研究人员的注意。艾里·戈德伯格(Ary Goldberger)和他的研究团队研究了不受意识控制的人体动态过程,包括心跳和行走时的步幅[17]。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过程中严格的周期性是病理状态的标志,而健康的行为则显示出周期性周围的分形变化。这表明,在放弃有意识控制的过程中,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化方法可能会调整到人体的基本分形节奏,波洛克将其应用到了他的滴水技术中。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分形图案的美学特质与人类绘制分形图案的能力之间的联系。
参考文献
[1] B.B. Mandelbrot, The Fractal Geometry of Nature, New York, W.H. Freeman and Company, 1977 and The Visual Mind, M. Emmer, ed., MIT Press, 1993.
[2] R.P. Taylor, A.P. Micolich and D. Jonas, “The Construction of Jackson Pollock’s Fractal Drip Paintings”, to be published in Leonardo, 35, 202, 2002.
[3] André Breton outlined the aims of Surrealism in his Manifeste du Surréalisme, Paris 1924. See, for example, “Dada and Surrealism” by Dawn Ades in Concepts of Modern Art, ed. N. Stango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4.
[4] E.G. Landau, Jackson Pollock,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8.
[5] H. Rorschach, Psychodiagnostics, New York, Grune and Straton, 1921.
[6] R.E. Rogowitz and R.F. Voss, “Shape Perception and Low Dimension Fractal Boundary Contours”,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Human Vision: Methods,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S.P.I.E., 1249, 387, 1990.
[7] R.P. Taylor, A.P. Micolich and D. Jonas, “Fractal Analysis of Pollock’s Drip Paintings”, Nature, 399, 422, 1999.
[8] K. Varnedoe and P. Karmel, Jackson Pollock, New York, Abrams, 1998.
[9] R.P. Taylor, “Splashdown”, New Scientist, 2144, 30, 1998.
[10] R.P. Taylor, A.P. Micolich and D. Jonas, “The Use of Science to Investigate Jackson Pollock’s Drip Paintings”,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7, 137, 2000.
[11] C. Pickover, Keys to Infinity, New York, Wiley, 206, 1995.
[12] D. Aks and J. Sprott, “Quantifying Aesthetic Preference for Chaotic Patterns”,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Arts, 14, 1, 1996.
[13] R.P. Taylor, “Architect Reaches for the Clouds”, Nature, 410, 18, 2001.
[14] See, for example, J. A. Wise and T. Leigh Hazzard, “Bionomic Design”, Architech, 24, Jan. 2000.
[15] R.P. Taylor, A.P. Micolich and D. Jonas, “Fractal Expressionism”, Physics World, 12, 25–28, 1999.
[16] R. Arnheim, “Accident and the Necessity of Art”,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6, 18, 1959.
[17] J.M. Hausdorff, P.L. Purdon, C.K. Peng, Z. Ladin, J.Y. Wei and A.L. Goldberger, “Fractal Dynamics of Human Gait: Stability of Long Range Correlations in Stride Interval Fluctu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80, 1448, 1996 and A.L. Goldberger, “Fractal Variability Versus Pathologic Periodicity: Complexity Loss and Stereotypy in Disease”,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40, 543 Summer edition 1997.
[18] Richard Taylor, Ben Newell, Branka Spehar and Colin Clifford, Fractals: A Resonance between Art and Nature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在下告退。
转发随意,转载请联系张大少本尊,联系方式请见公众号底部菜单栏。
扫一扫,关注微信公众号“宇宙文明带路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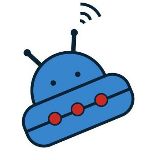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