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老少爷们儿们!在下张大少。
1. 凯尔特回纹图案
在公元前10世纪后半期,即盎格鲁·撒克逊和维京时期,在不列颠群岛创作的手稿和石碑中,所谓的凯尔特回纹纹样与更广为人知的交错纹样一样常见。罗米利·艾伦(Romilly Allen)[2]对这些图案的分类仍然是考古学家的标准,自从相关章节再版后[6],这种分类变得更容易获取,而且提供了很多有用的分析,但所有这些图案分类尝试都有一个固有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确定哪些是基本图案,哪些只是变体。交错图案的情况更糟,因为通常有许多方法来选择基本单位,而且有人提出了替代罗米利·艾伦尝试的方法[9]。彼得·克伦威尔(Peter Cromwell)在他最近基于绳结类型的调查[10]中避免了这个问题,因为它仅限于小绳结。有时,对回纹图案进行更直接的分类可能会掩盖在数学上更重要的特性。
虽然只有几种基本结构,但现存的凯尔特回纹图案显示出相当大的差异。最有特色的结构之一是以Z形图案为基础,其最基本的形式如图1所示(Romilly Allen [2]),它出现在林迪斯芳福音书和苏格兰的几个石质十字架上。其他的变体是在Z形的角上连接螺旋线而不是单条直线,还有许多其他的变体,如装饰图案主体的一对三角形。

图1:一种常见的凯尔特回纹图案。
本文所讨论的回纹图案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其成员通常刻在方格中,这些方格或单独出现,或单行重复出现,或拼成一个表面图案。图 2(a)显示的是罗米利·艾伦的第995号作品[2],该作品在不列颠群岛随处可见,同时还有一个来自麦克杜南福音书(Gospels of MacDurnan)的简单变体(第 997 号)。

图2:(a)另一种常见的凯尔特调式(罗米利·艾伦的第 995 号),(b) 一种简单的变体(罗米利·艾伦的第997号[2])。
图3显示的是在威尔士安格尔西Penmon Priory教堂的一个字体左侧发现的图案[1],该字体据信最初是一个十字底座,可追溯到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这是罗米利·艾伦分类中的第 1001号[2],他认为它是第995号的四个副本(图 2),中间部分做了一些修改。

图3:Romilly Allen从他的995号作品中得出的具有自相似性的凯尔特回纹图案(图2(a))。
2.底层结构
像这一时期的许多与世隔绝的艺术一样,这种图案似乎是为了以其错综复杂来制造炫目效果。给人的直接印象是许多指向不同方向的箭头,尽管正如罗米利·艾伦所观察到的,这组中的所有图案也可以被看作是由直角等腰三角形构成的,这种洞察力将成为理解自相似性某些方面的回纹。仔细观察会发现,每个箭头都是作为其他箭头之间的空间产生的,感知在它们之间以一种典型的图形/背景错觉的方式翻转。许多众所周知的分形曲线,如科赫的雪花(http://mathworld . wolfram . com/Koch snow flake . html),都有相同的性质:只给出曲线的一小部分,就无法判断雪花的内部是哪一面。这表明,这种特殊的回纹图案比罗米利·艾伦的陈述分析所暗示的有更多的数学结构,并且可以从中推导出自相似分形。
事实上,取自Romilly Allen的结构(图4(a))的构造基础(对应于泥瓦匠切割的凹槽)可以进一步重复,如图4(b)所示。这种排列与Mandelbrot的河流系统模型[15]相同,基于安东尼奥·塞萨罗的三角形扫描。

图4:递归深度为(a) 2和(b) 3的基本构造。
递归规则可以看作是科赫雪花曲线的变体,角度由 60 变为 90,同时缩短了一些线段,以避免产生类似正方形网格的图形。单位长度的直线被长度为 ½,一个 90 度的转折,一条长度为 5½ 的 "短 "线,它在自己身上翻了一倍,一个 90 度的转折,一条长度为 ½ 的线所取代。实际上有两个骨架(内骨架和外骨架)。外骨架是将递归规则应用于正方形的边缘;内骨架是将递归规则应用于从正方形中心开始的四对前后短线(长度 5½),比例系数为 1/√2。内骨架的递归深度比外骨架少一个,因此在图 4(a) 中,内骨架的递归深度为 1。
3. 完成构建
在骨架的两端添加箭头,就完成了图案的构建(图 5)。外骨架和内骨架上的箭头是不同的,因为它们遵循的是具有两个不同大小角度(45 和 90)的三角形的形状。在数学确定的结构中,需要仔细调整组成线段的长度,以达到美观的效果。

图5:箭头添加到图4的基本框架中。
很明显,我们缺少了一些东西,因为并不是每个箭头之间的空隙都有另一个箭头。内骨架上的箭头工作正常,每个空隙都由外骨架上的箭头填补,但外骨架上的箭头留下的空隙意味着内骨架上有额外的箭头。额外箭头的空间不大,因此需要非常小。在内层骨架中任何一条全长直线的中点(递归中的每一步)添加一对箭头,就完成了这个图案。
外层骨架中的三个箭头集群(图6中的粗线)现在需要特殊处理,因为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箭头,所以不能全部用同样的方法绘制,这样当然会产生形状相同的箭头。通常情况下,在递归的底层只画一条线,但现在我们需要在递归的第一层画一个完整的箭簇:中央箭头较小,侧面箭头也不对称。同样,出于美观的考虑,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地调整几条不同线段的相对长度。图6(a)显示了递归到第2层的情况,再往前推进一步(图6(b)),表明原始的回纹图形确实可以扩展到更深的递归层。

图6:递归生成的回纹图案:(a) 第 2 级和 (b) 再上一级。
4. 箭头的形状
如前所述,这些图案的基础是将正方形分割成三角形,三角形内填充直线螺旋线。由于等腰直角三角形可以被反复分割成更小的副本,因此可以递归地绘制这些图案。由于三角形的边缘与螺旋线平行,它们决定了箭头的形状。外骨架上的箭头从斜边开始平行于斜边,因此一开始要转 45 度;内骨架上的箭头从直角开始。小箭头的进一步增加需要更多的类型。如果所有箭头的形状都相同,那么自相似性就会更强。
有一种构造也依赖于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特殊性质,它可以生成一个以正确方式组合在一起的箭头形状。图7是图6左下角的一部分。ABCDE 是内骨架的半个箭头,WXYZ 是外骨架的半个箭头。WA 是周围小正方形的一条边(例如,单位长度),WX 是外骨架的一条“短”线,长度为某个分数,例如,f。AB是内骨架的一条相应的“短”线,长度为√2f。BC 和 XY 也是相应的线段,因此它们的比例也必须相同,即 √2:1。YC 在 45 .

图7:两个几何相似箭头的部分。
因为XA=1-f,所以AB线和XY线之间的距离是(1-f )/√2。所以WX和CD的距离是(1-f )/2(因为相似)。现在
于是
注意, Y 位于 DE 的延长线上,而 BC 在正方形底面的上方(1-f),所以

图8显示了这两条线是如何沿着重复平分的等腰直角三角形的边缘相互螺旋缠绕的。对应的边缘比例为√2:1,因此每条螺旋路径上的线段每转一圈都会减半,也就是一个直角,从而产生了一条近似对数螺旋的正方形路径,这与石头上的设计不同,石头上的设计是一条类似阿基米德螺旋的三角形路径。新螺旋的自相似性确保了不再需要对其进行修改以适应额外的小箭头。图9显示了图6中带有螺旋箭头的图案。

图8:图7中箭头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图9:箭头形状一致的图案。
图10和图9左侧的图案一样,是根据图3所示的原始雕刻设计的。轴已被移除,剩下的只是一对正方形螺旋,只留下一条边界线,在螺旋的两极有奇异点。显然,递归可以继续到任何深度,从而产生一个自相似分形。

图10:以维京时期的原作为基础的设计。
5中世纪的自相似设计
虽然递归和自参照在20世纪已变得司空见惯,但自相似性的例子在早期却非常罕见。它们最常出现在伊斯兰世界的装饰艺术中。杰伊·邦纳[7]追溯了这种自相似设计传统的起源,从9世纪的开罗开始,大胆的主要图案将较小比例的次要元素融入背景区域。到14世纪的西方和15世纪的东方,多层次几何图案的不同发展路线导致了真正的自相似设计,他将其分为三种类型。西方的例子依靠色彩来确定底层小比例图案的大比例副本。东方的例子则是将较小比例的图案作为背景,或作为较大复制图案线条中的装饰。
没有一个伊斯兰的例子有超过两个的递归深度,邦纳把这归因于材料的限制,而不是艺术家缺乏创造性。Jean-Marc Castera [8]更进一步,认为这些设计有意表达了无限递归的可能性,是有意识地唤起人们对无限的感知。
另一个自相似的设计出现在13世纪的科斯马蒂作品中。除了最小的三角形之外,其他三角形经常出现在这幅作品中,它们由四个较小的相似三角形(连接较大三角形边的中点)构成,内部三角形的颜色与其他三个三角形形成对比。这个过程被重复,这样每个小三角形都得到了同样的装饰性处理,这样的例子几乎一样普遍。这可以立即被认为是Sierpinski三角形的开始。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发生在意大利阿纳格尼大教堂的人行道上(由雅格布和卢卡·科斯马蒂兄弟设计),其中曲线三角形的装饰达到了递归深度四[16](
http://odur.let.rug.nl/koster/dolls.htm)。
自相似回纹图案与这些例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线性的。它的构造方法是将线段替换为更小线段的集合,而不是将一个区域或一块瓷砖替换为更小瓷砖的集合。它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没有明显的先例来暗示其构造方法。邦纳发现了伊斯兰自相似图案的历史发展过程,而科斯马蒂图案显然是从一种明显的装饰手段自然发展而来的。
一般来说,凯尔特几何艺术,特别是回纹图案,由有限范围的标准设备的精心制作组成。例如,只有少数可能的对称被使用,即使当视觉印象暗示一个不同的。其他考古学家罗米利·艾伦通常忽略对称的整体外观,有时会扭曲图案以符合标准方案,只保留拓扑特征[12]。他对1001号图案的分析(如上所述)同样忽略了看似明显的特征,这可能是为了他的分类。这种图案的几个版本出现在爱尔兰西海岸外的阿兰群岛的Inishmore上,它们表明罗米利·艾伦关于标准图案的四个副本的解释和递归构造都没有反映出这种设计的当代11世纪观点。由于唯一已知的例子发生在岛屿上,使得海上交流变得容易,有理由假设它们是相关的。
6. 爱尔兰的例子
图 11 [11] 显示了D.格里菲斯·戴维斯绘制的Leabha Brechain横轴的细节。它似乎与安格尔西的例子完全相同,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底部中央区域有不规则之处。事实上,爱尔兰的例子没有一个是完全准确的。对这种异常现象的常见解释是艺术家的谦逊,他并不追求完美,例如[4],但其他例子显示出更明显的偏差,其他解释也是可能的。

图11:伊尼什莫尔一个十字轴上的回纹图案的副本。
另一种爱尔兰回纹图案[3](图12)明显更不规则。右手边似乎支持Romilly Allen的观点,因为它由公共基本图案的两个精确版本组成,而中心部分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尝试,以合并连贯的更大图案所需的修改。它可能是一个试验版本,或者是一个拙劣的复制品,但雕刻师不事先计划就直接在石头上工作似乎不太可能。

图12:伊尼什莫尔基勒尼十字架轴上的回纹图案。
图13显示的是1895年出版的一幅完整图画[17],图中的说明显示,人们认为这些碎片都属于同一个部分。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轮子的形状与十字架的其他部分并不相关,但无论如何,它确实提供了回纹图案的另外两个例子,以及一些其他类型的几何图案,以供比较。

图13:显示两个回纹图案示例的图纸。
十字架的左臂上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维京时期的打结设计。例如,简单闭环的存在就很有特点。事实上,所有具有这种回纹图案的纪念碑也显示了该时期的典型元素(例如,本文初步版本中的图15[13]),这证明了估计的建造日期约为1000年。
右手手臂显然是基于相同的图案,但它以相当极端的方式扭曲。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群岛上的维京雕刻经常展示这种狂野的蜿蜒小路,在这种文化中,重复和规则性似乎并没有多少美学价值。最近的一项工作[14]讨论了类似的扭曲编织Maen Achwyfan(惠特福德十字架)作为维京人的创新。两个版本的设计并置可能是艺术家即兴创作的展示,也可能是为了对比传统凯尔特/盎格鲁·撒克逊设计的有序规则和北欧人的野性风格。
两个回纹图案之间存在类似的对比。上图(图14)相当精确,只有中央部分(右下角)有一处不规则。在下例(图15)中,中心部分完全规则,但作为外边界的部分却有很多变化。雏形的曲线螺旋(左侧)是 Inchbrayock 十字架的一个极端构思[14,第 218-219 页]。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些变化有什么意义,但图15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维京美学在回纹图案上的应用。

图14:图13 中的上部回纹图案。

图15:图13中较低的回纹图案。
无论对这种图案的变化有什么解释,总之它们似乎表明,这种图案的构思是一个带边框的中央部分,而不是像罗米利·艾伦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带修改过的中央部分的基本图案的四个副本。当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们意识到了它的递归结构,始作俑者最初是如何发明它的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证据表明,这一时期的石匠使用模板[5],至少在雕刻作品中是这样,而且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断,当时也有用于几何设计的模板。有可能是在使用两种尺寸的模板(一种尺寸是另一种的一半)进行试验时出现的。
7. 结论
近代以前,图案中的自相似性非常罕见,即使出现,也是早期做法的自然发展。没有明显的传统可以解释11世纪末凯尔特回纹图案中出现的自相似性,而且现存的例子表明,即使艺术家们意识到了自相似性,他们也没有赋予它任何特殊的美学价值。不过,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自相似性意味着一种递归的构造方法,可以以新颖的方式加以发展。遗憾的是,由于这种构造方法依赖于直角等腰三角形的特殊性质,因此没有明显的方法将其更广泛地应用。基于螺旋而非箭头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箭头之间的空间的构造可能会带来更广泛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揭示出与凯尔特螺旋图案的相似之处。
参考文献
[1] J.R. Allen, Early Christian art in Wales, Archaeol. Cambrensis XVI (1899), p. 42.
[2] J.R. Allen, The Early Christian Monuments of Scotland,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Scotland, Edinburgh, 1903 (edition limited to 400 copies; reprinted The Pinkfoot Press, Angus, 1993).
[3] Anonymous, Cruise in connexion with the Munster meeting, Whitsuntide, 1892, Proc. Roy. Soc. Antiq. Ireland 27 (1897), p. 267.
[4] J. Backhouse, The Lindisfarne Gospels, Phaidon, Oxford, 1981, p. 55.
[5] R.N. Bailey, Viking Age Sculpture, Collins, London, 1980.
[6] I. Bain, Celtic Key Patterns, Constable, London, 1993.
[7] J. Bonner, Three traditions of self-similarity in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y Islamic geometric ornament, Meeting Alhambra ISAMA-Bridges, University of Granada, Granada, Spain, 2003, pp. 1–12.
[8] J.-M. Castera, Play with infinity, Meeting Alhambra ISAMA-Bridges, University of Granada, Granada, Spain, 2003, pp. 189–196.
[9] R. Cramp, Corpus of Anglo-Saxon Stone Sculpture in England, General Introduction, Part 1, Vol.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Oxford, 1984.
[10] P.R. Cromwell, The distribution of knot types in Celtic interlaced ornament, J. Math. Arts 2 (2008), pp. 61–68.
[11] Editor, Archaeological notes and queries, Archaeol. Cambrensis, XIV (1897), p. 259.
[12] P. Gailiunas, Celtic key patterns, Symmetry: Cult. Sci. 20 (2009), pp. 191–200.
[13] P. Gailiunas, A Fractal Celtic Key Pattern?, Bridges Pecs 2010, Tessellations Publishing, Phoenix, 2010, pp. 293–298.
[14] D. Hull, Celtic and Anglo-Saxon Art Geometric Aspects,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Liverpool, 2003, pp. 229–232.
[15] B.B. Mandelbrot, Fractals Form, Chance and Dimension, Freeman, San Francisco, 1977.
[16] G. Perneczky, The Poly-dimensional Fields of SaxonSzasz, International MADI Museum Foundation, Budapest, 2002, pp. 19–21.
[17] T.J. Westropp, Aran islands, Proc. Roy. Soc. Antiq. Ireland vol. 25 (1895), p. 254.
[18] Paul Gailiunas, A recursive construction of a Celtic-key pattern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在下告退。
转发随意,转载请联系张大少本尊,联系方式请见公众号底部菜单栏。
扫一扫,关注微信公众号“宇宙文明带路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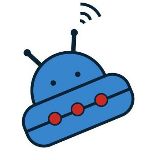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