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老少爷们儿们!在下张大少。
20世纪上半叶,拉斯洛·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Nagy)和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的艺术圈子相互重叠,他们对自己的作品如何影响观众有着截然不同的初衷。虽然他们的目的大相径庭,但他们各自采用的技法都植根于数学基础。莫霍利·纳吉使用简单的二维形状,这些形状的比例重复和透视变化来说明机器技术对普通人的潜在好处。蒙德里安则将其作品中的元素限制在垂直线、不对称和对平面的专注上,以便将观众的形而上状态与潜在的普遍精神统一起来。在本文中,我们将结合莫霍利·纳吉的《无题》拼贴画和蒙德里安的《百老汇爵士钢琴曲》(Broadway Boogie Woogie)这两位艺术家的著作和其他作品,重点探讨他们两件作品背后的数学灵感和总体意图。
1. 引言
20世纪初的抽象艺术对于那些对数学与艺术的交集感兴趣的人来说是一座宝库。从立体派对形状和透视的实验[2]到超现实主义者对四维空间的迷恋[9],艺术与数学在这一时期以多种方式交织在一起。人们花了大量时间研究这一时期的主要艺术家及其对基本几何元素的运用。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Nagy)和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就是这样的两位艺术家,特别是莫霍利·纳吉希望通过简单的几何图形进行交流,而蒙德里安则相信水平线和垂直线的神秘象征意义。
虽然莫霍利·纳吉没有像蒙德里安那样受到关注,但在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学院和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大型回顾展《莫霍利·纳吉:未来的现在》[34](2016-2017)展示了他对20世纪早期艺术的重要而多样的贡献。对蒙德里安作品的分析已经是研讨会核心阅读内容的一部分[5]。本文共同探讨这两位艺术家,旨在强调他们对推动人类进步的共同兴趣。
准确地说,我们在这里呈现了莫霍利·纳吉的拼贴画《无题》和蒙德里安的《百老汇爵士钢琴曲》的比较分析,借鉴了研讨会背景下发展出来的想法。图1包含了这两部分的图片。两位艺术家都用基本的几何元素来说明人类进步的不同方向。前者通过深思熟虑地使用现代技术来改善整个社会,而后者则专注于将观众的形而上学状况与潜在的普遍精神结合起来。这些艺术目标的差异通过以下对上述两个作品中的数学成分的分析,以及艺术家的相关作品和著作来说明。
图 1:本文主要讨论的两件艺术作品:(a)莫霍利·纳吉,《无题》,1920-1921 年,纸上水粉和拼贴画,24.45 × 16.19 厘米,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b)蒙德里安,《百老汇爵士钢琴曲》,1942-1943 年,布面油画,127 × 127 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2. 背景
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Nagy,1895-1946 年)是匈牙利的一位抽象艺术家,他深受建构主义的影响,建构主义强调艺术在推动社会走向更加平等的模式中的作用。他在《教育与包豪斯》(1938 年)中写道,技术进步是“提高生活水平不可或缺的因素”[19,第 345 页]。莫霍利·纳吉20多岁时在柏林工作,与当时的主要艺术家(包括埃尔·利西茨基和提奥·范·多斯伯格)打交道,并尝试使用各种媒介。不可否认的天赋和前卫的审美观,再加上他的个人魅力[32],使他于 1923 年至 1928 年在德国魏玛包豪斯学院(Bauhaus)任教。学校的个人政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莫霍利·纳吉先后前往荷兰、伦敦和芝加哥。1937 年,他在芝加哥创建了新包豪斯,即现在的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特别是在《无题》中,莫霍利·纳吉通过简化的二维形状、比例和透视等数学元素,将他对乌托邦式未来的憧憬融入其中。
虽然荷兰艺术家皮耶·蒙德里安(1872-1944)受过正规的风景画训练,但他与哲学家M.H.J .休恩梅克斯和艺术家特奥·凡·杜斯堡的交往将蒙德里安推向了抽象艺术。他的许多相交的水平和垂直线条的可识别的风格,用原色填充许多合成的矩形,是他和范杜斯堡开创的艺术运动的特征。这两位艺术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分道扬镳,蒙德里安的余生都在磨练和宣扬新造型主义,这是艺术美学背后的理论。他的六个新塑性定律给出了使用直线、直角、不对称、比例和颜色的指导,以表达一种基本的和普遍的精神力量。[25,26]和其他地方出现了每种新塑性原理的具体和单独的陈述。对这些支配公理的认识和随后的整合是蒙德里安人类进化愿景的核心。蒙德里安在纽约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在那里他迷恋于网格状的城市规划,他认为这是新造型主义的具体体现。他最后完成的作品《百老汇爵士钢琴曲》可以说是他一生作品的顶峰,于他去世前一年在纽约完成。
这两位艺术家似乎并不看重对方,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对人类和艺术进步所设想的道路截然不同[4]。1923 年,莫霍利·纳吉等人在一份关于真正的建构主义目标的宣言[11]中,指责 De Stijl 艺术家创造了视野有限的资产阶级艺术。蒙德里安在[27,第 129 页]中反驳说,那些“赞成大众进步而反对精英进步的人[是]违背人类进化的逻辑的”。后来在 [27, 第 129 页] 中,他称赞“精英”是大众的“最高表现形式”,使大众更能理解他的作品。尽管饱受批评,莫霍利·纳吉还是受命为蒙德里安的包豪斯著作《新造型主义》和范·多斯伯格的《新塑性艺术原理》设计封面。值得注意的是,莫霍利·纳吉为凡·多斯伯格的文本设计了一种典型的 De Stijl 美学,这很可能与他本人的观点相反[16]。就蒙德里安而言,他认为莫霍利·纳吉的新包豪斯(New Bauhaus)是一个有缺陷的机构,尽管他曾在那里谋求一个教职,尽管那是他在二战边缘离开欧洲的一种手段[10, page 310]。因此,他们之间截然不同的理念似乎导致了长达数十年的不愉快。
3.形式分析
《无题》和《百老汇爵士钢琴曲》都有一个共同的配色方案,即在浅灰色的背景上用蓝色强调黄色。百老汇爵士钢琴曲中的线段由黄色、蓝色、红色和灰色的小矩形组成。整幅画中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蓝色色调;较大的蓝色矩形比较小的蓝色矩形颜色浅。线段的交叉点产生大的灰色块,读起来像负空间。和明显的蓝色一样,使用了两种灰度:较大的矩形用较浅的灰色,较小的用较深的灰色。
《无题》中的浅灰色被用作取景装置,而黑色的长方形创造了负空间和结构。灰色边框上的铅笔标记进一步指明了作品周围的非正式框架。《无题》中一个有趣的空间特征是蓝色圆圈和黄色圆盘的排列;它们看起来是互锁的,而不是简单的分层。虽然莫霍利·纳吉没有使用真正的红色色调,但他对栗色和橙色的使用以类似蒙德里安的方式强调了构图。他的拼贴画中的两个元素都提供了与《百老汇爵士钢琴曲》中的红色矩形相同的暖色调。此外,《无题》前景中橙色的线性排列呼应了蒙德里安的直角,并与圆圈的曲率形成对比。两位艺术家都通过对比色而不是深色轮廓来描绘作品中独立的几何元素。这解释了在百老汇爵士钢琴曲中使用两种不同深浅的灰色,尽管同样的情况不适用于蓝色颜料。
两幅作品的色彩饱和度都很高。由于没有使用阴影或光源,单个造型的视觉重量和冲击力由其面积决定。这一特点使画面平面变得扁平,但在《无题》中比在《百老汇爵士钢琴曲》中要轻一些。在《无题》中,我们可以看到黄色或深灰色矩形被对比色矩形包围的少数情况。为了进一步突出红色、黄色、蓝色和灰色,正方形画布漂浮在一块更大的涂成白色的正方形木板上(图 1(b)中看不到)。在黑色背景的衬托下,《无题》中橙色、黄色和蓝色的色调更加鲜艳。因此,彩色几何元素似乎漂浮在黑色负空间中。
乍一看,这两件作品也都非常精确。线条和曲线似乎都是精心制作而成,几乎就像机器生产出来的一样。然而,仔细观察《百老汇爵士钢琴曲》,蒙德里安的艺术创作过程显而易见,笔触和色彩区域略有重叠;在黄色的不同部分,红色和蓝色的色调从后面探出。这无疑是他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尝试的结果[12]。在《无题》中,蓝色圆圈上的胶渍尤为明显。拼贴画右侧边框附近的黄色大圆圈的扁平弧度透露出一种人情味。在栗色半圆内观察到的纹理表明,莫霍利·纳吉用纸条将一个黑色长方形分成了两个小块。尽管两位艺术家都有意将自己从作品中剥离出来,但鉴于媒体的性质,这些元素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18, 27]。
4. 二维几何图形
如图 1 所示,我们所讨论的作品普遍采用的基本二维形状是矩形和圆形。蒙德里安的《百老汇爵士钢琴曲》只有长方形,而莫霍利·纳吉的《无题》中两种形状都有。他们选择使用简化的几何元素反映了当时的前卫艺术。由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领导的建构主义者正值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兴起之际,他们认为纯粹的几何图形是所有观众都能接受的,并反对将客观绘画作为精英阶层的标志。他们的意图是创造出能为大众服务的艺术[13]。莫霍利·纳吉深受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视觉语言的影响。莫霍利·纳吉在《艺术家抽象》(1944 年)中回顾了自己的艺术生涯[20,第 364 页]:
所谓的“非政治”艺术是一种谬论。这里的政治……作为一种实现思想、造福社会的方式……艺术可以像社会革命者推动政治行动一样,大力推动社会生物问题的解决……我相信,抽象艺术不仅记录了当代问题,而且预测了理想的未来秩序,不受次要意义的阻碍,而习惯上的背离自然通常因其不可避免的内涵而涉及次要意义。我认为,抽象艺术创造了新型的空间关系、新的形式、新的视觉法则——基本而简单——作为更有目的的人类合作社会的视觉对应物。
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莫霍利·纳吉将建构主义风格与他所认为的工业在创造这一理想未来中所能发挥的潜在作用相结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幅《无题》拼贴画完成于莫霍利·纳吉生涯的早期,但却包含了莫霍利·纳吉一直到去世前都在追求的工业和倡导无阶级社会的主题。
《无题》中简单形状的组织方式给人一种工业和机械的感觉,这与他早期的其他作品不谋而合。莫霍利·纳吉在《艺术家抽象》一书中写道 [20, 第 362 页]:
我来自匈牙利农业中心的一个农场,对奥地利首都巴洛克式的华而不实并不感兴趣,倒是对德国高度发达的工业技术很感兴趣……我当时的许多画作都体现了柏林工业景观的影响。它们不是以摄影的眼光呈现的现实投影,而是作为我自己的机器技术版本,从拆卸的部件中重新组装起来的新结构。
特别是前面提到的蓝色圆圈和黄色圆盘,它们连接在一起,给人一种机械零件在运动的感觉。此外,橙色线段模仿了机械臂、起重机或管道的形状。这些元素让人联想起莫霍利·纳吉20年代早期的其他作品中出现的圆形和线形部件,如《Perpe》、《F in Feld》和《Y》。莫霍利·纳吉在《无题》中进一步推进了抽象主义,削弱了与工业背景的明显联系,但其内涵却巧妙地保留了下来。最有说服力的是《Y》(1920-1921年)中线段的排列方式描绘了一个排水系统,与《无题》中的橙色线段非常相似;见上图 2。
图2:L´aszl´o Moholy-Nagy,《Y》,1920/1921,纸上灰泥和拼贴画,27.5 × 21.5 厘米。
在形式方面,《无题》中有两个长方形即使不完全是正方形,本质上也是正方形:左上角的浅灰色小方块和下方包含蓝色圆圈和黄色圆盘的黑色大块。灰色小正方形的直线边缘与其下方黄色小圆圈的弧度形成鲜明对比。此外,正方形没有颜色,而圆形元素则是原色。莫霍利·纳吉在他的论文《论新内容和新形式的问题》(1922 年)[14,第 287 页]中讨论了正方形的使用:
一个三角形的任何一个角,一个梯形或一个不规则的形状,凭借其形状具有明显的心理效果,而正方形,作为最中性的形式,只作为颜色的载体具有重要意义,并在颜色的内部关系中产生最小的干扰。
正方形形状的中性因缺乏主要颜料而得到加强。推而广之,较小的黑色矩形和灰色矩形框保持了正方形在形状和颜色上的公正性。所有这些基本元素赋予了《无题》与更复杂的自然秩序相反的结构和组织。从前面的段落以及莫霍利·纳吉在[20, 第 363 页]中的反思来看,他之所以使用熟悉的二维形状,主要是因为这些形状服从于色彩之间的关系。中性正方形与填充其中的柔和色彩的组合,确实会将观众的视线引向对比鲜明的颜料。
把《无题》和同时期的作品放在一起看,很明显莫霍利·纳吉把工业元素提升到了一个值得艺术努力的水平,并尊重它们在所有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莫霍利·纳吉的学者和他那个时代的先锋派Krisztina Passuth在[32,第26页]中表达了这种情绪:
莫霍利·纳吉对机器深信不疑。他相信,在新的机器文明的帮助下,人类可以开启一个新时代。因此,他赋予机械零件以英雄主义和与新时代的到来相称的不朽表现力。
他在[15,第 185 页]中将技术描述为伟大的均衡器:“在机器面前,人人平等——我可以使用它,你也可以——它可以压垮我,同样的事情也可以发生在你身上。技术中没有传统,没有阶级或地位意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机器的主人或奴隶”。因此,莫霍利·纳吉认为,只要不是系统地剥削普通工人,工业就是人类进步的关键。
蒙德里安在包括《百老汇爵士钢琴曲》在内的所有抽象作品中都使用了类似的小型视觉词汇,但却没有莫霍利·纳吉对人类生活的微妙指涉。他的第四条新塑性法则指出,垂直排列的线段是对保持平衡的内在普遍力量之间张力的理想艺术表达[26]。具体来说,垂直线相交形成的90度角体现了蒙德里安所说的“生命的运动”[25, 第 210 页]:相反能量和互补能量的动态平衡,类似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符号和异教中的六芒星[5, 22]。考虑到人体的物理限制,与画布特定垂直和水平方向平行的线条在相交时会产生直角[1],这充分体现了直角的象征意义。因此,蒙德里安在他的作品中排除了斜线,即使他将画布本身旋转45度,例如在他的菱形系列作品中;见图3。经过有限的实验2和深思熟虑后,蒙德里安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任何非传统方向的线段[25,第 210 页](强调是他的):
在新造型艺术中,基本问题不是垂直或水平,而是垂直的位置——以及由此获得的关系。因为正是这种关系表达了自然界中不可变的事物。因此,通过将这种关系转向斜角,可以创造出非常精细的东西。倾斜自然是相对的,取决于我们的位置或事物的位置。但是尽管有相对主义,人类的眼睛还没有脱离身体。视觉与我们的正常位置有着内在的联系。只有头脑能够知道第四维度的任何东西,并把自己从我们可怜的肉体中分离出来!作为人,我们必须处理人的平衡;如果我们打乱了它,我们什么也创造不了!可塑性表达是由我们身体和精神的平衡决定的。
图3:皮耶·蒙德里安,《Tableau No. IV》黄色和黑色的菱形构图,约 1924/1925 年,布面油画,142.8 × 142.3厘米
同样,相交的曲线可以在切线上产生一个直角,但它们会阻碍人们更深刻地认识蒙德里安试图传达的平衡[27]。这样的曲线也不那么抽象,而是更加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为艺术作品引入了主观性,减弱了新造型主义的核心——普遍真理[24]。
垂直线条的网格状排列自然地在整个百老汇爵士钢琴曲创造了矩形。在他题为《走向现实的真实愿景》(1941)的文章中,蒙德里安将他作品中的矩形描述为这种结构的无意副产品:“事实上,矩形本身从来不是目的,而是它们在空间中连续的决定性线条的逻辑结果;它们通过垂直和水平线条的交叉自发地出现”[29,第339页]。尽管是无意的,但他坚持认为,矩形和产生矩形的线条是最纯粹、最适合抽象艺术的形式。这些特殊的几何元素自然包括直角,这些直角代表了二元对立的基本普遍原则。此外,单独的矩形能够容易地构建更大的整体。与积木相似,蒙德里安作品中的矩形创造出的组合大于其各部分的总和。
蒙德里安的第三条和第五条新造型法则规定,必须将作品中的各个元素与更大的作品联系起来考虑[26]。通过单一构图中线段和矩形的多重性,产生了关系和节奏。就像独立房间的组合创造出的建筑产生了一个繁荣的城市一样,《百老汇爵士钢琴曲》中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矩形为画布注入了一种统一的、脉动的能量。只有当较小的组成部分为整体服务而失去个性时,观众才能识别出这种潜在的活力。因此,蒙德里安明令禁止几何形式保留其独特性。圆就是一个特别的例子,他认为圆是自成一体的,无法创造出他的理论所必须的视觉关系[28]。他在《艺术、建筑和工业新教学的必要性》(1938 年)中写道:“最大的开放性是由相互交叉的垂直线产生的,因为这些线永远不会相遇,永远不会封闭”[28,第 313 页]。莫霍利·纳吉的《无题》中相互交错的圆盘和圆圈同时支持和反驳了蒙德里安的论点。圆周,尤其是在黑色背景的衬托下,确实强调了它们与拼贴画中其他元素的分离性。同时,它们相互连接的位置创造了一种视觉关系,给作品带来了一种运动感。
在蒙德里安的宏大构想中,意识到并思考在一个奇异整体中的超越平衡是人类进步的关键。通过在艺术中表达一切存在的精神实质,蒙德里安相信,他的观众可以根据他传达的普遍真理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进而塑造整个社会。蒙德里安在1919年写道:“新造型主义”[23,第 80 页](强调是他自己写的):
但艺术的任务是表现超人的东西。这就是直觉。它纯粹表达的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力量,这种力量普遍活跃,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普遍”……只有有意识的人才能纯粹地反映普遍性:他能有意识地与普遍性融为一体,从而有意识地超越个体。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有意识地在包罗万象的普世精神中迷失自我,就像《百老汇爵士钢琴曲》中的小矩形在大构图中连成一体一样。蒙德里安在他的宣言“新造型主义的一般原则”(1926 年)的结尾宣称,他试图揭示的平衡“消灭了作为特殊个性的个人,创造了作为真正统一体的未来社会”[26,第 215 页](着重号是他的)。认识到平衡的整体是人类意识向蒙德里安乌托邦愿景进化的第一步。
5.通过不对称和缩放实现平衡
图1中的两个部分都不能被描述为对称的组合;相反,两者都通过偏离对称成功地实现了视觉平衡。在蒙德里安的绝大多数作品中,包括《百老汇爵士钢琴曲》,饱和原色的小区域与不对称网格中的大中性区域相对。在《百老汇爵士钢琴曲》的彩色线段中,颜色分组被重复,例如在第三象限中水平出现三次的蓝—黄—红—黄—蓝排列。但是在这个伪图案中,非黄色方块之间的间隔通过其垂直循环不均匀地减少,从而以一种非系统的方式创造了一种运动感。
百老汇爵士钢琴曲的较大元素也有助于它的能量平衡。从画布的顶部到底部,有一个由黄色、蓝色、红色和深灰色矩形组成的连续细带,位于中间偏右的位置。同样,有两条连续的细条,从左到右,在中心的上方和下方。通过放置这些特殊的组件,蒙德里安有目的地将作品的中心留在负空间,并禁止在方形画布上建立任何潜在的对称轴。此外,前述垂直条带的偏离中心的位置在它的故意性上是明显的;通过避开中心,蒙德里安“预先假定了它的存在”[1,215页]并强调了不对称在其理论中的基本作用。
新造型主义第六条要求禁止重复和对称[26],以免抑制动态平衡,而在蒙德里安的绘画中,动态平衡正是上述色彩和尺寸的生动视觉平衡。它描绘的是相称的力量之间竞争的张力,而不是通过对称和形式重复在视觉上体现的平静、安宁和静止的能量感[27]。例如,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的《向方形致敬》系列(1950-1954 年)中的一件单色作品通过重复几何形状的对称组织实现了稳定。这种静态平衡正是蒙德里安在《百老汇爵士钢琴曲》中通过使用不对称和不规则性所摒弃的。
《百老汇爵士钢琴曲》的彩色线条为作品注入了明显的能量。蒙德里安意识到,他之前作品中随处可见的黑线削弱了他的预期效果。在1943年给策展人詹姆斯·约翰逊·斯威尼的一封信中,在他完成百老汇爵士钢琴曲的同时,这位艺术家对静态和动态平衡做了如下观察[30,357页]:
在我以前的作品中,许多人欣赏的只是我不想表达的东西,但却因为无法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平衡中的动态运动——而产生了这种作品。但是,为这一表述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使我更加接近这一表述。
黑线会无意中充当脚手架,将彩色矩形固定在一个固定的平衡中。相比之下,《百老汇爵士钢琴曲》是在柔和的背景下以不同的节奏闪烁的原色的生动展示。
通过它的不对称和活力,百老汇爵士钢琴曲是对纽约市的形式和能量的庆祝性描绘,供其他人模仿。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城市的各色各样的个人都为这个独特的大都市的跳动的心脏做出了贡献,体现了蒙德里安的平衡、整体和活力的中心信条。为了配合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1995年的回顾展,馆长比阿特丽斯·克南思考了蒙德里安与这座城市的关系[12,第7页]:
蒙德里安的抽象艺术在最现代的大都市中找到了共鸣。他的乌托邦主义颂扬了纽约为他呈现的形象,一个充满多样性、和谐统一、生机勃勃的整体。他喜欢这座城市的棱角分明的规则性——高耸的垂直和不屈的网格,闪闪发光的模块化玻璃窗和夜间的几何光。在世纪中期的纽约,最坚定的现代抽象主义者找到了精神家园。
蒙德里安从他的优越地位出发,从纽约市充满生机的矩形棱镜或“平面交汇处”[28,第 317 页]中看到了他对人类进步的部分憧憬。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莫霍利·纳吉谴责这种景观是资本主义的堡垒[14,第 287 页]:
我们需要机器。我们需要它,摆脱浪漫主义。摩天大楼确实是一种不健康的建筑,不值得效仿,但我们可以支持缆索、起重机和水塔,它们是同一建筑精神的巧妙创造。一件作品的绝对价值不能被这个社会的敲诈勒索和腐败行为所损害。不是机器不好,而是当今的社会秩序不好。
在莫霍利·纳吉看来,让蒙德里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场景是剥削性的,而且对公共利益有反作用。两人都同意,现代工业和技术进步应该用来促进人类进步,但内心的哲学却大相径庭。
尽管他们之间有这样的鸿沟,莫霍利·纳吉在《无题》中同样拒绝任何对称感。他主要通过按比例重复特定的形状来达到视觉上的平衡。重复的形式包括两个黄色的圆盘,浅灰色的小方块与较大的灰白色的纸呼应,这是作品的一部分,以及将整个拼贴画分成两部分的黑色大矩形。黑色矩形和黄色圆盘的具体尺寸和位置禁止建立对称轴或中心焦点。通过大小和位置的刻意不对称,创造了一种紧张的视觉力量,与《百老汇爵士钢琴曲》中活泼的能量形成对比。此外,《无题》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亲切感,这与不相关的橙色线段和褐红色半圆形成了平衡。在1982年的展览目录[33]中,凯特·斯坦尼茨写道,这些橙色的线性元素是拼贴不稳定的视觉平衡的核心。它们薄而完整,统一了原本分割作品的两个密集的矩形区域。
缩放主题图案在莫霍利·纳吉的作品中很常见;一个特殊的案例被很好地记录下来[20]。1922年,就在莫霍利·纳吉完成《无题》后,他向一家标志厂订购了五幅画;通过电话,他和工厂主管用绘图纸传达了艺术家的各种设计。其中之一,描绘在EM 1-3(电话图片),是在三个不同的矩形大小,纵向和横向的比例约为2。图4显示了其中最小的EM 3(电话图片)。回忆这个过程,莫霍利·纳吉写道[20,第381页]:
其中一张图片以三种不同的尺寸交付,这样我就可以研究放大和缩小所导致的颜色关系的细微差异……我的信念是,精确制作的数学上和谐的形状充满了情感,它们代表了情感和理智之间的完美平衡。
图4: L aszl o Moholy-Nagy,EM 3(电话图片),1923,钢铁上的搪瓷,24 × 15 cm,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外推至无题,同样的平衡是通过圆形和矩形的缩放重复实现的。在深色背景的映衬下,重复的直边暗示着不同尺度的智力结构,而圆圈的曲率和颜料给人以动感和创造性的感觉。栗色半圆将这些看似不同的元素结合成一种互补的平衡。
莫霍利·纳吉在他的《无题》、《EM 1-3(电话图片)》和其他作品中使用了缩放效果,实现了对立力量之间的视觉平衡,突出了工业在创作大众消费艺术品中的应用。艺术家的创造力产生了设计,而机器则高效地生产出各种尺寸和媒介的设计。因此,工业技术是莫霍利·纳吉关于艺术惠及大众的愿景的核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总结了这一艺术与技术综合体的影响,见 [21,第 360 页]:
今天的设计师有一种建立在大规模生产基础上的政治和社会责任。他设计什么以及如何设计将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一个好的设计师必须知道他的历史背景和我们的政治方向。无知专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一个预制价值观的世界里,工业设计组织有责任激发这种责任感。
因此,社会的进步可以通过艺术与工业的深思熟虑的结合来引导,向人们灌输莫霍利·纳吉所致力于的平等主义信息。
6. 透视或缺乏透视
由于采用了拼贴的媒介,《无题》通过对独立作品的层叠处理而具有了内在的三维深度。这一点在栗色半圆盘下两个黑色矩形之间的白色纸条轮廓上尤为明显。蓝色圆圈和黄色大圆盘的布局产生了进一步的空间效果,观众会将蓝色圆圈的一部分看成是在黄色圆盘的后面,反之亦然。此外,前景中细长的橙色线段漂浮在更大的形状之上,同时将它们固定在一起。斯坦尼茨指出,半圆盘在莫霍利·纳吉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是“与斜线相互作用以创造构图深度的装置”[33,第 87 页]。亮色和暗色颜料的对比也有助于产生深度感,因为亮色向平面外推进,而暗色则向平面内后退 [33]。
《无题》中的空间深度和张力显然是有意为之的,莫霍利·纳吉的作品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一个艺术家的摘要》[20,362页]的以下段落中描述了1920年左右柏林的工业景观:
在路上,我发现了废弃的机器零件、螺丝钉、螺栓、机械装置。我把它们固定、粘合、钉在木板上,结合图纸和绘画。对我来说,用这种方式我可以产生真实的空间清晰度,正面和侧面,以及更强烈的色彩效果。
这是从这个描述到《无题》的一个短暂跳跃,创作于上述艺术家描述的时间,其图层和缩放元素表达了一些三维的外观。帕苏斯指出,莫霍利·纳吉对“平面间复杂关系”的使用……和轴线的明显的“莫霍里式”解释在他的拼贴画中尤其明显;基本的几何图形“在背景的衬托下清晰突出,具有很大的可塑性”[32,第24-25页]。
莫霍利·纳吉对空间衔接的持久兴趣,无论是否依赖线性透视,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显而易见。图 5(a) 所示的 1922 年绘画作品《K VII》是线性透视的典范;观众可以看到淡色线段将正面图案的顶点与较小的重复图像的相应顶点连接起来,并汇聚到画布右上角的消失点。在 1926 年的摄影系列《玩偶》、《施莱默女孩》和《奥斯卡·施莱默,As cona》中(见图 5(b)),莫霍利·纳吉将线性透视变成了他和观众关注的主题。每幅作品左侧的栅栏再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透视网格,栅栏的阴影落在不同的人物身上时发生了扭曲。这些引人注目的线段和曲线强调了线性透视法在表现人形方面的失败 [7]。
图 5:L´aszl´o Moholy-Nagy 的透视探索:(a) K VII,1922 年,布面油画颜料和石墨,115.3 × 135.9 厘米 ;(b) Oskar Schlemmer,Ascona,1926 年,明胶银版画,29. 2 × 21.2 厘米,;(c) 《城市之光》,约 1928 年,明胶银版画,30.2 × 23.5 厘米。
作为莫霍利·纳吉透视实验的范例,最有趣的是他的摄影蒙太奇作品——他利用杂志和报纸图片制作的纸质拼贴照片——在这些作品中,他颠倒了线性透视的组成部分,使较大的物体位于背景,较小的物体位于前景,而消失点则位于画面平面之外,与观众处于实际空间中。这类透视实验的作品包括约 1926 年的《城市之光》(Die Lichter der Stadt)(见图 5(c))和《Kinetisch Konstruktives System》(Kinetisch Konstruktives System):Bau mit Bewegungsbahnen f¨ur Spiel und Bef¨orderung》(《动感结构系统:带有活动部件的结构,用于游戏和秩序》):1928年创作的《带活动部件的结构,用于游戏和传送》(Structure with Moving Parts for Play and Conveyance)。这些作品特有的空间感从照片中凸显出来,进入观众的视野。反向透视是 20 世纪 20 年代许多前卫艺术家(其中包括莫霍利·纳吉和埃尔·利西茨基)进一步与具象艺术拉开距离并挑战观众对作品的疏离感的一种手段 [7]。
在《绘画与摄影》( 1932)中,莫霍利·纳吉通过摄影的现代进步,将他对眼睛如何感知世界的兴趣与他理想的未来社会联系起来。他认为自己的角色和作品挑战了既定的空间规范,帮助观众训练他们对未来无阶级社会的视觉[17,318-319页]:
光学作品是一种无意识的、无意的教育工具,我们试图用它来准备一种适合未来社会的意识形式……资本主义的座右铭“利润高于一切”使机器与人对立。这已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几代人的生理机能变得衰弱。阶级斗争提供了一种方法,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来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错误,从而改善生活的有机条件。但也有其他方式,它们不那么有意识,但它们的目的是通过经验(五种感官)而不是通过智力告诉人类,在当前体系部分或全部崩溃后,他将需要什么来重建他的生活。艺术是无意识的准备,是人潜意识的教育。
在这种情况下,莫霍利·纳吉在《无题》中模糊的深度感对于他对人类进步的看法至关重要。通过考虑作品中相互矛盾的空间元素:黄色圆盘的后退、相互交错的蓝色圆环和黄色大圆盘以及拼贴画的突出层,观众的光学感得到了潜移默化的磨练。
与莫霍利·纳吉对透视的浓厚兴趣不同,蒙德里安断然拒绝在其作品中加入任何立体感。他在[22, 第 29 页]中宣称:
这是绘画自由表达关系的独特特权——换句话说,它的表达方式(通过一致和彻底的转变)允许极端对立被表达为纯粹的位置关系,而不通过封闭呈现形式,甚至形式的外观(如在建筑中)。在绘画中,关系的双重性可以彼此并置(在一个平面上),这在建筑或雕塑中是不可能的。因此,绘画确实是最纯粹的“塑料”。
垂直线和直角是新造型主义的基本二维组成部分。将线的交点延伸到平面的交点会混淆相对实体之间的中心关系。因此,即使是三维物体的二维表现也不能恰当地传达新造型主义的原则。
在《百老汇爵士钢琴曲》中,有一个误导观众辨别浅深度的机会;几个矩形似乎是用对比鲜明的颜色叠加在其他矩形之上的。外层矩形的饱和原色并没有像《无题》中那样通过层叠产生物理深度,而是突出了平面的平面感,在内层矩形周围形成了一个框架。在《百老汇爵士钢琴曲》中,明显缺少了阴影或色调上的变化,而这些都能传达出一丝深度。悬挂画布的木板也与这种扁平化效果相呼应。
蒙德里安对二维的坚定承诺源于对非传统色彩方案和立体主义者对体积的革命性描绘的日益浓厚的兴趣[24]。这位艺术家从透视风景画到致力于画布平面的抽象画的演变通过他在1910年左右的树木绘画得以展示。在图6中,我们提供了四个不同抽象层次的树的例子,从《红树》(1908-1910)开始。树本身被相当忠实地渲染,但是颜色方案是蒙德里安在[25,211页]中描述的“变性”的早期探索。立体主义对蒙德里安的变革性影响在《灰树》(1911)和《盛开的苹果树》(1912)中显而易见。特别是在后者中,表现树的结构的垂直和水平线段的出现。这位艺术家对完全抽象的持续探索记录在《椭圆形树木构图》(1913)中,其中有大量相互连接的垂直和水平线段,此外还强调了它们所形成的直角。画布本身是矩形的,但被画成椭圆形的中心。几年后,在《百老汇爵士钢琴曲》中,框架设计进一步强调了作品的二维性。
图6:皮耶·蒙德里安的《抽象中的探索》:(a)《红树》,1908-1910,布面油画,99 × 70 cm;(b)格雷树,1911年,布面油画,高78.5厘米;(c)盛开的苹果树,1912年,布面油画,78.5 × 107.5cm;(d)椭圆形树木构图,1913年,阿姆斯特丹Stedelijk博物馆。
致力于平面,蒙德里安和他的同事“相信绘画可以为更广泛的环境重建提供一种图表”,在物理意义上,也就是说,通过城市生活[6,第11页]。蒙德里安希望,总的来说,一个大都市可以成为理想世界中的一个空间的范例,这个空间“完全由精神的、宇宙的、我们称之为先验的关注所驱动”。因此,“可塑”是一个人出于对完美或进步的渴望而创造未来的能力。思考建筑创造这样一个未来世界的特殊潜力,蒙德里安在[25,211-212页]中传达了他对人类的终极希望:
身体和精神上的快乐——健康的先决条件——将通过比例和颜色、物质和空间关系的平衡对立而得到推进。如果有意愿,创造一种伊甸园并非不可能……男人呢?他自己什么都没有,他将是整体的一部分;失去了他渺小而可怜的个人骄傲,他将在他创造的伊甸园里快乐!
通过蒙德里安对潜在精神的平面表达,我们被引导到这个伊甸园,我们将不再被我们自己对生命和存在的个人版本所束缚;相反,我们的集体意识会承认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抽象的普遍力量,我们会相应地采取行动。
7.总结
莫霍利·纳吉和蒙德里安都认为抽象艺术及其基本数学语汇是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手段,但他们在作品中所追求的哲学和艺术目标却大相径庭。艺术和工业促进社会公平的能力是莫霍利·纳吉创作生涯的核心。另一方面,蒙德里安发展其艺术理论是为了促进人类的精神统一。简单的几何形式受到机器技术和普遍原则的启发。两位艺术家都有意回避对称,以捕捉相反但又互补的实体之间的动态张力。他们对三维深度进行了与人类视觉相关的严格研究,或者干脆放弃三维深度,转而追求形而上的纯粹平面。尽管两人在风格和目标上存在差异,但他们都为受数学启发的艺术做出了重要而持久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Rudolf Arnheim, The Power of the Center: A Study of Composition in the Visual Arts, the New Vers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A, 1988.
[2] Guillaume Apollinaire and Dorothea Eimert, Cubism, Parkstone International, New York, 2014.
[3] Carel Blotkamp, Mondrian: The Art of Destruction, Harry N. Adams, New York NY, 1995.
[4] Y. Bois, “Mondrian and the theory of architecture”, Assemblage, Number 4 (October 1987), MIT Press, Cambridge MA, pages 103–130.
[5] Paul A. Calter, Squaring the Circle: Geometry in Art and Architecture, John Wiley, Hoboken NJ, 2008.
[6] John Elderfield and Kay Larson, “Mondrian at MoMA. An interview with John Elderfield”, MoMA Number 20 (Autumn 1995),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NY, pages 6–13.
[7] Devin Fore, Realism After Modernism: The Rehumaniza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012.
[8] Lynn Gamwell, Mathematics + Art: A Cultur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2016.
[9] Linda Dalrymple Henderson, The Fourth Dimension and Non-Euclidean Geometry in Modern Ar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1983.
[10] Harry Holtzman and Martin S. James, editors, The New Art - The New Lif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Piet Mondrian, Da Capo Press, New York NY, 1993.
[11] Ern˝o K´allai, Alfr´ed Kem´eny, L´aszl´o Moholy-Nagy, L´aszl´o P´eri, “Manifesto”, 1923, republished in and available on pages 288–289 of [31].
[12] Beatrice Kernan, “Mondrian at MoMA. Mondrian’s New York years: A visual celebration of the city and Boogie-Woogie’s syncopated beat”, MoMA Number 20 (Autumn 1995),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NY, pages 7–13.
[13] Christina Lodder, Russian Constructiv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CT, 1983.
[14] L´aszl´o Moholy-Nagy, “On the problem of new content and new form”, 1922, republished in and available on pages 286–288 of [31].
[15] L´aszl´o Moholy-Nagy,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roletariat”, 1922, republished in Moholy-Nagy, edited by Richard Kostelanetz (Praeger, New York NY, 1970), pages 185–186.
[16] L´aszl´o Moholy-Nagy and Alfr´ed Kem´eny,“Dynamic-constructive system of forces”, 1922, republished in and available on page 290 of [31].
[17] L.´aszl´o Moholy-Nagy, “Painting and photography”, 1932, republished in and available on pages 318–319 of [31].
[18] L´aszl´o Moholy-Nagy, “From pigment to light”, 1933, republished in and available on pages 323–326 of [31].
[19] L´aszl´o Moholy-Nagy, “Education and the Bauhaus”, 1938, republished in and available on pages 344–348 of [31].
[20] L´aszl´o Moholy-Nagy, “Abstract of an artist”, 1944, republished in and available on pages 360–364 and 381–383 of [31].
[21] L´aszl´o Moholy-Nagy, “Art in industry”, 1947, republished in and available on pages 357–360 of [31].
[22] Piet Mondrian, “The new plastic in painting”, 1917, republished in and available on pages 27–74 of [10].
[23] Piet Mondrian, “Dialogue on the new plastic”, 1919, republished in and available on pages 75–81 of [10].
[24] Piet Mondrian, “The new plastic expression in painting”, 1926, republished in and available on pages 202–204 of [10].
[25] Piet Mondrian, “Home-street-city”, 1926, republished in and available on pages 205–212 of [10].
[26] Piet Mondrian, “General principles of Neo-Plasticism”, 1926, republished in and available on pages 213–215 of [10].
[27] Piet Mondrian, “Plastic art & pure plastic art”, 1937, republished in Modern Artists on Art: Ten Unabridged Essays, edited by Robert L. Herbert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1964), pages 114–130.
[28] Piet Mondrian, “The necessity for a new teaching in art, architecture, and industry”, 1938, republished in and available on pages 310–317 of [10].
[29] Piet Mondrian, “Toward the true vision of reality”, 1941, republished in and available on pages 338–341 of [10].
[30] Piet Mondrian, “An interview with Mondrian”, 1943, republished in and available on pages. 356–357 of [10].
[31] Krisztina Passuth, editor, Moholy-Nagy, Thames and Hudson, New York NY, 1985.
[32] Krisztina Passuth, “L´aszl´o Moholy-Nagy and the international avantgarde”, Hungarian Studies Review, Volume 37 (2010), pages 21–27.
[33] Kate Steinitz, Art and Collection: Avant-Garde Art in Germany in the 1920s and 1930s, California State College, San Bernardino CA, 1982.
[34] Matthew S. Witkovsky, Carol S. Eliel and Karole P. B. Vail, editors, Moholy-Nagy: Future Present,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Chicago IL, 2016, pages 21–36.
[35] Kimberly Spayd, Molly Reynolds, Christian Lansinger, On the Use of Geometric Elements in the Works of L´aszl´o Moholy-Nagy and Piet Mondrian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在下告退。
转发随意,转载请联系张大少本尊,联系方式请见公众号底部菜单栏。
扫一扫,关注微信公众号“宇宙文明带路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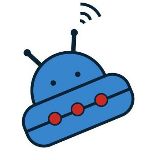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