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老少爷们儿们!在下张大少。
本文着重于建筑表面的镶嵌、密铺和编织。这三个过程会让覆盖平面的连接形状的出现几何图案。在建筑中,这种技术通常用于为地板、墙壁或天花板创造更耐久或防风雨的饰面。但它们也提供了一种装饰表面的方法,以获得美学、诗意或象征性的结果,其中一些被用来唤起特定的数学属性。本文概述了建筑拼块的发展,强调了与数学的重要联系。建筑实例从简单的新石器时代编织和石头切割实践到二十世纪末主要公共建筑中的不定期覆层系统。这一章也提到了过去对建筑中贴砖的研究以及过去已经研究过的主要主题。
介绍
Nikos Salingaros (1999)认为,纵观历史,图案提供了建筑、数学和社会之间的基本联系。人类的思维不仅被吸引去识别自然和社会中的图案,还被吸引去开发新的图案,并可视化地表现它们,以理解它们的应用或结果。Salingaros认为,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这种对图案制作和识别的社会文化亲和力“解释了视觉图案在人类传统艺术和建筑中的普遍性”(1999: 76)。他甚至认为密铺、镶嵌或编织的几何排列是社会中数学的“可见端倪”(Salingaros 1999: 76),提供了抽象概念及其实际应用之间的重要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是建筑中最基本的拼块图案制作也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数学和世界之间的实用和诗意的联系。但是对于Salingaros (1999)来说,这些基本的几何图案曾经是维持这种联系的关键,但并不总是被庆祝或尊重。例如,在20世纪上半叶,他提出现代主义建筑师贬低了拼块的作用,从那时起,大多数建筑师要么忽视了它,要么忘记了它的潜力。现代主义建筑师贬低镶嵌的原因为建筑师和数学家对镶嵌的态度差异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
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现代建筑运动在欧洲和美国蓬勃发展,对大型雕塑造型、功能表达和机械化生产情有独钟(Ostwald和Dawes,2018年)。因此,现代主义建筑师倾向于珍视混凝土、钢材和玻璃等不需要应用饰面的材料,他们还呼吁摒弃一切装饰和装潢。例如,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1998年)等欧洲建筑理论家拒绝拼块,理由是拼块不卫生(有太多不必要的接缝)、有社会偏见(因为它需要特定阶层的工匠)和文化低劣(因为非洲和亚洲的原始或部落艺术中经常使用几何图案)。
现代主义建筑师认为唯一可以接受的镶嵌图案是大规模工业制造的副产品。因此,使用预制构件制作的简单直线网格或“堆叠”图案被认为是“诚实”,因为它体现了材料的基本特性(图 1)。标准的“拉伸”粘结拼块排列被认为是“功能性的”,因为其重叠图案增强了其结构特性(图 2)。然而,“人字形”图案则被认为是“不诚实的”,因为这种材料是用来达到装饰效果的,因此在道德上是不光彩的(图 3)。从数学意义上讲,这三种镶嵌——堆叠、拉伸和人字形——都有些微不足道。事实上,它们都可以用完全相同的部件或拼块拼成,而且都能有效地覆盖一个表面。但对于现代主义建筑师或理论家来说,图案的选择还必须考虑到伦理、道德或象征意义。

图1:堆叠图案

图2:拉伸或流动图案

图3:人字形图案
虽然详细分析早期现代派对图案制作的态度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但它们确实让我们了解到这一主题的复杂性。对于数学家来说,可以用代数或算法符号来表达镶嵌,也可以用几种相关的方法对其本质进行分析或分类。对于建筑师来说,拼块或图案表面必须适合场地的环境条件、建筑物的功能和预算。此外,图案还可能唤起社会或文化属性,象征价值观或传达特定信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与数学发展联系更为紧密的,正是建筑拼块的后一种更具美学或诗意的特性。事实上,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人们对建筑中的复杂密铺重新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一直持续到今天。
尽管人们对贴砖的态度不断变化,但最近一个用于分类建筑与数学之间联系的框架将“表面衔接”确定为贯穿建筑史的一贯主题。表面衔接被定义为“使用数学来有效或可控地覆盖一个确定的平面”(Ostwald and Williams 2015: 40)。这一类别包括“根据经验或直觉得出的实现防水或防风[......]表面的方法”,以及使用几何拼块“实现复杂的图案表面覆盖”(40)。这些定义包含了拼块在建筑中的实用和美学意义。不过,在本文中,我们只是简要地讨论了铺贴的实用性,因为建筑与数学方格之间一些最有趣的联系往往是设计师从数学的特殊发展中获得灵感而产生的。
本文介绍了建筑环境中拼块铺贴的历史背景,并概述了数学领域的平行发展。不过,在继续讨论之前,有五点注意事项必须说明。首先,本文讨论的大多数“建筑”实例都是室内或室外表面,而不是完整的建筑物,因此它们也可以被视为来自室内设计或外墙设计领域。其次,本文还讨论了编织表面,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拼块。增加这一内容的原因在下一节中将会更加清楚,但原始社会最早创造的图案表面通常是编织而成的,其几何表现形式类似于拼块或棋盘格表面,即使它们的制作方法并不相同。第三,本文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表面或“平面填充”拼块的。然而,我们也可以讨论空间的密铺或镶嵌,这与“空间填充”特性有关。正如正方形拼块可以轻易地覆盖一个表面,形成网格状图案,立方体拼块也可以轻易地填充网格中的体积。除少数例外,建筑界对拼块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前一类,即表面网格,而使用体积网格的例子并不多见。最后,当艺术家、设计师或建筑师受到数学启发时,他们倾向于改编而不是采用数学家的语言。因此,建筑师描述密铺的方式与数学中使用的术语并不一致。此外,建筑师对当代镶嵌理论的了解有限,在应用镶嵌图案时往往对其数学特性缺乏深入了解。在阅读本文和研究其中的实例时,应牢记最后这一点。
密铺背景
在建筑学和数学中,“密铺”和“镶嵌”这两个词经常交替使用,用来描述用多边形覆盖表面的过程。虽然有些数学文献在图案有明确的基本规则时使用 “tessellation”(镶嵌)一词,而在没有规则时使用 “tiling”(密铺)一词,但这种用法并不一致。tessellation "一词源于拉丁文 tessela,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世界用于镶嵌的半规则立方体小拼块。而 “tile”(拼块)一词的起源通常可追溯到拉丁语 tegula,意为覆盖某物。从本质上讲,这两个词都起源于用更小、更耐用或装饰性更强的元素覆盖大面积墙壁、地板或天花板的过程。
镶嵌的一个更数学的定义是,它是使用平面形状覆盖一个表面的过程,以满足两个条件。首先,任何拼块之间不得有重叠,其次,在生成的表面上不得有间隙。如果这两个条件都满足,那么这种密铺就被称为“完全的”或“真实的”除此之外,图案中特定多边形的每个实例都被定义为一个“拼块”,用于创建镶嵌的不同多边形类型的数量被称为“拼块集”因此,如果一个表面被相同大小的正方形拼块覆盖,这是一个拼块集,因为只有一种类型的拼块(图4)。上一节中的堆叠、拉伸和人字形示例都有一个拼块集。如果一个表面被正方形拼块和直角三角形拼块(由一个正方形的对角线分割而成)的混合物覆盖,则它被描述为两个拼块集,以此类推。理论上,拼块集没有最大数量,因为每个拼块都可能与其他拼块不同。相比之下,只有三种“规则”或“全等”镶嵌,即正方形、等边三角形和六边形(图4、5和6)。像这样显示多条对称线或重复其配置的镶嵌通常被称为“周期”集。一些最容易辨认的周期性图案是基于正方形、长方形、梯形或平行四边形。此外,通过仅重复单一形状,几个三维形状也可以完美地填充空间体积。最明显的例子是立方体,但是菱形十二面体以及一些三角形和菱形棱柱也具有这种性质。

图4:正方形

图5:等边三角形镶嵌

图6:六边形镶嵌
周期性拼块必须有对称线或重复其配置,而“非周期性”拼块也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拼块既可以周期性地填充平面,也可以非周期性地填充平面,这取决于组装它们的规则。加德纳四边形就是第一类非周期性拼块的一个例子(奥斯特瓦尔德,1998 年)。第二类拼块是数学家和建筑师最感兴趣的拼块,它们只能以非周期方式密铺。近年来,这类拼块已成为大量研究的焦点,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们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
1961年,王浩开始研究,如果给定一个特定的多边形拼块集,是否有办法确定其周期性地铺贴平面的能力(即确定它们是否会重复其配置)。然而,1965 年,罗伯特·伯杰(Robert Berger)证明,不可能开发出周期性铺贴的程序,因此非周期性拼块集和图案必然存在(鲁宾斯泰姆,1996 年)。这一认识引发了该领域的一系列发展,伯杰提出了第一个非周期性拼块集,该拼块集有 20426 种不同的形状。1967 年,伯杰将这一数字减少到 104 个;1968 年,唐纳德·克努特将其减少到 92 个;1971 年,拉斐尔·罗宾逊将该集合减少到只有 6 个拼块。两年后,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证明,利用平行四边形密铺法,可以将图形集减少到两块拼块,这就是今天的“彭罗斯拼块”或“飞镖和风筝”图形集(图 7)。20 世纪90年代初,约翰·康威发现了另一种双拼块非周期性集合,即“风车”集合。

图7:彭罗斯的“飞镖和风筝”非周期镶嵌
有趣的是,彭罗斯的“飞镖和风筝”组合呈现出一种“准对称性”,让人联想到20世纪60 年代在准晶体几何中发现的五重对称性,以及20世纪80年代在铝锰晶体中发现的五重对称性(Stewart和 Golubitsky,1993年;Ostwald,1998年)。康威拼块的一个奇特特征是,与分形几何形式一样,它们也可以按比例缩放,这样较小的拼块集可以嵌套在较大的拼块集中(图 8)。有多种周期性集合可以出现这种情况,但康威图案是唯一具有这种特性的著名非周期性集合。尽管如此,这种拼块集往往是贝努瓦·曼德布罗特(Benoit Mandelbrot)所说的“微不足道的分形”,这意味着细分图案与分形几何之间的联系并不一定像这个例子所暗示的那样重要或有趣(奥斯特瓦尔德和沃恩,2016 年)。一些细分图案会在更大尺度上重复其小尺度几何形状,这也是分形定义的一部分。但也有很多非分形图案具有相同的特性,包括全等正方形(图 4)和等边三角形(图 5)。

图8:康威的“风车”非周期镶嵌
在开发平面填充非周期性拼块集的同时,也有一些关于空间填充非周期性拼块集的建议。Koji Miyazaki(1977 年)和罗伯特·安曼(Robert Ammann)都发现了两种可以填充空间的非周期性拼块集。安曼的拼块集由一对菱形组成,这对菱形由两个实体构成,每个实体都有六条边,这些边都与彭罗斯形成飞镖和风筝集的起始菱形相同。此外,还开发了非周期性沃罗诺伊镶嵌的平面填充和空间填充变体。虽然这些沃罗诺伊集合不具备安曼集合和Miyazaki集合的数学纯度,但它们却非常有趣,因为它们似乎复制了一些自然现象,而这些自然现象反过来又启发了建筑师、设计师和艺术家。
建筑中的拼块
纵观历史,拼块一直与建筑密切相关。即使是最早的原始住所也常常铺着编织席子,用粗略堆叠的砖石砌成墙壁,并刻有几何图案。最古老的建筑基础神话之一,“古代人的原始小屋”,描绘了史前人类将树枝拼成一个紧密的网格,以创建第一个庇护所(Rykwert 1991)。这种编织篮子、垫子和屏风的方法可以在中石器时代之前和新石器时代(公元前10,000年)找到证据。这些早期的建筑是通过密铺干树叶或藤蔓来创造更大的表面。通过重复规则的图案,这些编织物品变得更加耐用,通过组合不同的材料,它们成为装饰性的表面,通常具有文化意义(Gerdes 1999)。
Indra Kagis McEwen(1993 年)认为,建筑的起源——不仅指最早的建筑作品,还包括神话中作为建筑起点的作品——可以追溯到编织结构或马赛克地板。虽然从数学的角度来看,编织和镶嵌是不同的过程,但它们有几个共同的语言祖先,而且它们的表面条件具有相似的特性。例如,在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被认为是第一位建筑师,因为他创造了克诺索斯的迷宫和阿里阿德涅的舞池——马赛克舞池。然而,关于哪一个被认为是第一个建筑作品,仍然存在一些混淆。在神话中,这两件作品都被归类为建筑,因为它们都是使人类行为生动的几何编织物。首先,代达罗斯在克诺索斯建造的迷宫是一个复杂的空间图案,它描述了米诺陶洛斯在迷宫核心走过的路径,以及被释放到迷宫中的牺牲者。相反,阿里阿德涅的“咏叹调”则囊括了舞者在参与编排仪式时所遵循的运动图案。在这两种情况下,表面图案都很重要,因为它塑造或激发了人们的行动。无论这些例子中的哪一个可以被视为第一件建筑作品,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建筑的起源显然与创造表面图案的行为息息相关。
Grünbaum 和 Shephard(1987: 1)认为,实用的“拼块艺术”始于首次使用石头铺设地板。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可以发现这种不规则的地板,而从公元前7000年左右开始,有证据表明粮仓中使用了更加规则的石质和木质地板。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原始砖块的制作方法是将粘土放入正方形或长方形的模具中(通常中间部分加厚或挖空,以便于堆放),然后在窑中烧制或在太阳下晒干。这些砖块被用来建造道路、小径、地板和墙壁,并以各种图案拼接在一起,以增加其强度或耐久性。
Grünbaum和Shephard(1987: 1)还特别将“拼块艺术”与建筑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最早的社会中,人们就意识到拼块图案可以增加建筑物表面的丰富性、装饰性或点缀性。此外,在任何历史时期,“无论哪种拼块受到青睐,其艺术和技术总是吸引着高超的工匠、富有创造力的从业者和宽宏大量的赞助人”(Grünbaum 和 Shephard,1987 年:1)。例如,最早的马赛克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当时人们将彩色拼块组合在一起,在墙壁或地板上创造出图案或图画。在古波斯和印度的建筑中也广泛使用了以几何而非图像表现为主题的彩色拼块,如今它们通常与伊斯兰建筑联系在一起。虽然这种密铺图案的使用比这更普遍,但北非和中东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宫殿代表了有史以来最先进的密铺应用,至今仍是引人入胜和争论的焦点(Bonner,2017 年;Wichmann 和 Wade,2017 年)。
密铺是伊斯兰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宗教信仰限制使用图像或形象表现。因此,在伊斯兰建筑中,精心雕刻和镶嵌的拼块和阿拉伯式花饰达到了可能是最高的精致程度,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例如,位于格拉纳达(安达卢西亚)的摩尔人宫殿阿尔罕布拉宫就有13到16种不同类型的全等或等距图案。这些拼块大多来自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扩建工程,如今因其丰富性和创造性而备受赞誉。后一个方面,即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直到17世纪,约翰内斯·开普勒才完成了对镶嵌的首次认真研究,而到了19世纪,叶夫格拉夫·费奥多罗夫才确定周期性的棋盘格都符合17种等距或“壁纸”组中的一种。因此,在数学家们对周期性密铺中不同类型的全等进行分类和理解的三百年前,阿尔罕布拉宫的设计师们就已经使用了其中的许多全等。
Lu和Steinhardt(2007 年)在另一个例子中指出,15世纪中期伊朗建筑中的几种镶嵌图案与彭罗斯镶嵌图案有相似之处,它们似乎具有准周期性。Lu最初在布哈拉(乌兹别克斯坦)的宗教学校中观察到了这些特性,并在伊斯法罕(伊朗)的 Darb-i Imam 神殿中观察到了更先进的版本。虽然有关伊玛目神庙拼块图案的真实性和制作日期都存在争议(Lauwers,2018 年),但布哈拉的库克尔达什伊斯兰学校也在三维棱形天花板穹顶或拱门内拥有几个复杂的拼块表面(Makovicky,2018 年)。
欧洲出现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拼块铺设传统,修道院、公共建筑和商业建筑的地板通常铺设对称、重复的彩色图案,而教堂和宫殿则铺设马赛克,表现《圣经》中的场景、著名战役或风景。因此,欧洲的拼块铺设方式出现了分化,功能性较强的图案被保留在内部通道或轴线上,而绘画传统有时与壁画或特罗姆普尔(tromp l orl)同时出现,成为一种交流或娱乐方式。
第一种类型的拼块,尤其是所谓的“棋盘格”拼块,在古希腊神庙、罗马别墅、中世纪酒庄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院中随处可见。一般来说,这类几何拼块多用于入口、走廊或中庭。虽然基础图案通常比较简单,但也经常使用“边砖”或装饰性拼块,有时会描绘纹章或行会标志和徽章。尽管使用了彩色拼块和具有不同纹理或插图的拼块,但这些拼块中的许多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功能性应用。不过,也有明显的例外,包括共济会会所和寺庙的拼块地板。这些仪式用的地板通常呈直角形,由黑白棋盘式拼块铺成(通常是对角线铺成),边框由三角形(或菱形)拼块围成。这些地板的中央有许多装饰拼块,上面刻有十字架("saltires")和六角星,或者在四角镶嵌有共济会工具的图案:正方形、圆规、铅垂线和泥铲。
西班牙巴伦西亚著名的2世纪马赛克作品就是第二种拼块镶嵌的典范,这种拼块镶嵌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表现或描绘。这幅镶嵌画描绘了正方形场地上的四季景色,场地被对角线分割成四个三角形区域,再细分为八角形、梯形和十字形。每个三角形区域都以人脸为中心(在八角形拼块内),周围是鸟类、植物和神兽的图案,代表一年中时间的流逝。另一个例子是六世纪意大利拉文纳的圣维塔莱大教堂,精致的马赛克以海伦式罗马装饰传统中丰富的金色和棕色色调描绘了《旧约圣经》中的故事。这些马赛克中拼块图案的基本几何形状并不重要,因为其目的是说明圣经主题与自然元素(植物和动物)的结合。圣维塔莱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Vitale)也有一个著名的马赛克地板,上面描绘了一个迷宫,法国13世纪的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 Cathedral)也是如此。虽然这类迷宫的实际目的尚不清楚,但它们通常被解释为朝圣者为到达礼拜场所而走过的艰难道路的象征,或者是跪在地上的忏悔者为寻求赦免而在大教堂地板上走过的真实道路。这些例子与克诺索斯的大神迷宫和阿里阿德涅的舞池一样,都是用拼块来说明潜在的或期望的运动。
到19世纪初,象形拼块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已不再受欢迎,因为它既昂贵又令人望而却步,而且在一些国家,社会对它的接受程度也不如从前。与此相反,简单的装饰性拼块变得非常经济实惠,在许多房屋的壁炉周围、门窗台,甚至厨房的墙壁上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在英国和美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拼块不仅坚固耐用,还是展示中产阶级财富的一种手段,而且还具有以前的石材、木材或灰泥表面所不具备的卫生水平。然而,在19世纪末期,一系列相互冲突的力量开始改变拼块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工业革命扩大了大规模生产的规模,拼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得;另一方面,随着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兴起,人们对手工制作的拼块产生了新的热情。现代建筑逐渐成为二十世纪早期建筑的主流,它摒弃了维多利亚、哥特复兴和工艺美术风格的建筑以及几乎所有的拼块传统。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可能是唯一一位在其设计的潘普利亚和巴西利亚(巴西)宗教建筑中加入精致壁画和拼块表面的现代主义建筑师。
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开始批评现代主义,认为其空间和形式往往冰冷、缺乏人性。对现代主义的反弹被统称为“后现代主义”,旨在重新引入与历史的联系和人文关怀。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后现代主义建筑师采用的一种设计策略是在墙壁和地板上铺设华丽的拼块装饰,其中一些装饰旨在复制或唤起人们对历史名胜或事件的回忆。例如,建筑师查尔斯·摩尔于 1978 年在美国新奥尔良建成的意大利广场。这个公共空间的设计采用了多种装饰性的、超大的、色彩鲜艳的拼块图案,这些图案通常会让人联想到古罗马(或古希腊)建筑(詹克斯,1991 年)。意大利广场的地面铺设了黑白相间的同心圆拼块,让人联想起圣维塔莱大教堂和沙特尔大教堂的迷宫地板,以及拉斯维加斯赌场和购物中心的标志性图案。由于摩尔选择的拼块通常都是廉价的批量生产的,整个效果就像是一个临时的舞台布景。罗伯特·文丘里和丹尼斯·斯科特·布朗于1982年设计的戈登·吴厅(美国普林斯顿)在其入口立面上方使用了宏伟的装饰性拼块图案,而他们于1983年设计的路易斯·托马斯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美国普林斯顿)则覆盖了多种不同的砖块方格图案。在这两种情况下,拼块图案都趋于简单,但它们如此突出和大胆的摆放方式是为了与现代主义形成反讽,并唤起人们对历史建筑风格的回忆(von Moos,1987 年)。
20世纪最后十年,建筑界首次直接接触到数学密铺。在澳大利亚墨尔本,ARM 建筑师受委托翻新历史悠久的 Storey Hall 礼堂。他们的设计于 1996 年完成,在历史悠久的外墙以及整个新门厅和礼堂上都铺设了石灰绿色的彭罗斯拼块。虽然可以将 ARM 对拼块的使用归类为后现代传统的延伸,但他们的设计多次引用了非周期性拼块的实际数学特性,其解释直接参考了彭罗斯的著作(Ostwald,1998 年)。他们设计的飞镖和风筝组合不仅在三维空间中发挥了部分作用,而且还强调了表面上那些被搁置的部分或由于所遵循的逻辑中的故意缺陷而无法铺贴的部分的重要性。另一个较近的例子是,墨尔本联邦广场是一个大型艺术娱乐综合体,于2002年竣工。它由LAB建筑师事务所设计,使用了一种针轮非周期性拼块组作为外部覆层,并对其部分规划进行了造型。外部的风车拼块由锌(实心和穿孔)、玻璃(半透明和磨砂)和砂岩制成。联邦广场的公共空间铺设了鹅卵石(通常镶嵌有文字碎片),鹅卵石下面是一个隐藏的环境“迷宫”。
联邦广场和斯托里大厅并不是唯一一个大胆采用最新数学拼块集来生成建筑空间和形式的建筑。Voronoi 网格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Minifie Nixon于2004年设计的墨尔本创意中心(Centre for Ideas)和ARM于2009年设计的墨尔本演奏厅(Melbourne Recital Hall)。非周期性和准周期性铺地图案非常受欢迎,已被用于许多公共建筑和空间,例如牛津数学研究所、巴黎科学中心和里耶卡的扎梅中心,甚至还被用于商业生产的浴室和厨房拼块。
在本文所举的大多数例子中,重点都放在无缝覆盖的表面上,但某些周期性拼块组的组合会造成无法铺贴的区域。按照惯例,这种情况被视为缺陷或错误,可以通过移除周围的一些拼块并重新制作图案,直到没有孔洞为止。但是,如果将孔洞、其形状和频率视为密铺图案的另一个维度呢?约翰·康威将这种对密铺的思考方式称为“孔洞理论”,它类似于想象“一座巨大的寺庙,地面由彭罗斯拼块拼成棋盘格,中间正好有一根圆形圆柱。拼块似乎在柱子下面,[但]柱子却盖住了一个无法镶嵌的洞”(Gardner 1989: 26-27)。ARM's Storey Hall 在早期建筑设计中就诠释了表面无法铺设拼块部分的意义。
结论
公元前1世纪,罗马作家和军事建筑师马库斯-维特鲁威·波利奥出版了《建筑学》。在这部著作中,他将建筑的三大核心特性定义为坚固、商品和愉悦。这些特性也是拼块、镶嵌和编织表面在建筑中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密铺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增加表面的强度或稳定性,它还能改善表面的功能或可用性,并提供了发展装饰性、象征性或诗意性的机会。因此,出于实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密铺在建筑中一直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建筑密铺与数学密铺之间的关系却不那么一致。
可以说,建筑,尤其是伊斯兰建筑中的密铺,实际上早于有关密铺的正式数学知识的发展。还必须指出的是,近来,建筑师和设计师已经从非周期性密铺的进步中汲取了经验,并对其进行了公开的改造。由于多种文化和社会因素影响着建筑师和设计师使用数学概念的方式,这种关系是否会继续下去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无论建筑与数学之间的关系如何演变,密铺仍然是其最明显和最显著的接触点之一。
参考文献
Bonner J (2017) Islamic geometric patterns: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raditional methods of construction. Springer, Cham
Gardner M (1989) Penrose tiles to trapdoor ciphers. W. H. Freeman, New York
Gerdes P (1999) Geometry from Africa: mathematical and educational explorations. Mathematical Associate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Grünbaum B, Shephard GC (1987) Tilings and patterns. W. H. Freeman, New York
Jencks C (1991) The language of post modern architecture. Wiley, London
Lauwers L (2018) Darb-e imam tessellations: a mistake of 250 years. Nexus Network J 20:321–329
Loos A (1998) Ornament and crime: selected essays. Ariadne Press, Riverside
Lu PJ, Steinhardt PJ (2007) Decagonal and quasi-crystalline tilings in medieval Islamic architecture. Science 315:1106–1110
Makovicky E (2018) Vault mosaics of the kukeldash madrasah, Bukhara, Uzbekistan. Nexus Network J 20:309–320
McEwen IK (1993) Socrates ancestor: an essay on architectural beginnings. MIT Press, Cambridge, MA
Miyazaki K (1977) On some periodical and non-periodical honeycombs. University Monographs, Kobe
Ostwald MJ (1998) Aperiodic tiling, Penrose tiling and the generation of architectural forms. In:
Williams K (ed) Nexus II: Architecture and mathematics. Edizioni dell’Erba, Florence, pp 99–111
Ostwald MJ, Dawes MJ (2018) The mathematics of the modernist villa: architectural analysis using space syntax and isovists. Birkhäuser, Cham
Ostwald MJ, Vaughan J (2016) The fractal dimension of architecture. Birkhäuser, Cham
Ostwald MJ, Williams K (2015) Mathematics in, of and for architecture: a framework of types.
In: Williams K, Ostwald MJ (eds) Architecture and mathematics from antiquity to the future: Volume I. Birkhäuser, Cham, pp 31–57
Rubinsteim H (1996) Penrose tiling. Transition 52(53):20–21
Rykwert J (1991) On Adam’s house in paradise: the idea of the primitive hut in architectural history. MIT Press, Cambridge, MA
Salingaros N (1999) Architecture, patterns and mathematics. Nexus Netw J 1(1):75–85
Stewart I, Golubutsky M (1993) Fearful symmetry. Penguin, London
von Moos S (1987) Venturi, Rauch and Scott Brown: buildings and projects. Rizzoli, New York
Wichmann B, Wade D (2017) Islamic design: a mathematical approach. Springer, Cham
Michael J. Ostwald, Tessellated, Tiled, and Woven Surfaces in Architecture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在下告退。
转发随意,转载请联系张大少本尊,联系方式请见公众号底部菜单栏。
扫一扫,关注微信公众号“宇宙文明带路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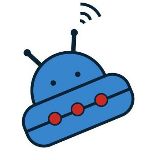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