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栏目语: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特开设“家风”栏目,为您讲述政协委员的家风故事。
我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母属于晚婚晚育,生我的时候都已早过了而立之年,但从小父母亲给了我颇为严格的家教,也给了我无条件的爱。
如果说他们的一言一行留给了我什么样的影响,我想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何韵: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大学工会副主席、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一
父亲出生于1949年,爷爷的家庭成分是大官僚资本家地主,在那个特别讲究阶级成分的年代,父亲的生活过得并不算顺利。
父亲没能接受很高的教育,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但他天生爱学习爱思考。他爱读普希金的诗,还自学了一点点俄语,时不时就会“蹦跶几句”出来;他爱好乐器,会弹奏二胡、手风琴、阮和各式各样的弦乐,家里时常飘荡着悠扬的琴音;他关注时事政治,重要的国际局势他分析起来头头是道。总而言之,父亲在我心中是一位帅气有才又十分浪漫的男人。
相比多才多艺的父亲,母亲在相貌和才情上并未有太多出彩的地方。母亲也是工人,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安安分分地忙工作,剩余的时间就是在操劳家务,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父母亲对我的培养自襁褓中开始。刚有记忆,母亲便常常指着窗户告诉我,那是window,跟你同名(我的乳名叫韵坨)。他们非常重视在语言方面对我的培养,认为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一把能够去了解、认识陌生世界和不同文化的钥匙。他们的薪资并不高,却宁愿多年来省吃俭用,从微薄的收入里拿出一笔笔钱送我去学习英语,他们对我的爱从不吝啬。
记忆中,父母对我的教育自有一套方法论。
他们很少带我逛游乐场,但书可以随便买,我打小钻在书堆里,对我而言,每一本书都是一座小型的避难所。以至于现在只要我遇到烦心事,看一个小时书就足以抚慰我。
他们也几乎不表扬我,但每当我掌握了一个小小的历史常识,或是写出了一个优美的句子,父亲都会歪着头瞅着我,用惊讶的语气问我:“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呀?”我自小很少听到“你太棒了”这样的话语,但就是父母亲这一句句带点表演性质的小惊讶,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和好奇心去了解这个世界。
后来父亲告诉我:“表扬是一种毒药,因为我们可能会对别人的表扬产生一种依赖。只有自己的内心能做主时,才是真正的自由。”
小学时,有一段时间我迷恋上了打电子游戏,甚至会翘课和小伙伴去游戏厅。那个年代上游戏厅的可都是“坏小孩”,为此班主任非常着急,还专门到我家家访。
老师走后,我以为免不了要挨揍,结果父亲很平和地对我说:“韵儿,一个人的兴趣爱好总数守恒,你想改掉一个,就要增加一个。”他拿出一袋瓜子告诉我,想打游戏的时候就嗑瓜子。按照父亲提供的法子,我居然改掉了爱打游戏的毛病。
母亲对我影响最深的应是她一直以来的勤劳节俭。小时候吃饭要吃干净,穿衣不可挑剔,母亲认为养小德才能成大德。有一回我在国外出差,受周边朋友影响也想买一个奢侈品牌的行李箱,打电话问母亲:“我可不可以买?”母亲并没有直接反对,只是反问我:“你买这个行李箱是看中它的实用性,还是觉得买了它便高人一等?”
母亲的话让我释然,挂掉电话后,我没有再看那个行李箱,后来的人生中也没有再买过奢侈品。摆脱了这些繁重的束缚,我的内心更加自由。

二
2004年9月,我顺利考入清华大学文科实验班,2008年免试进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学系,2017年获得清华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一路走来,父母亲并没有在我的学业上有过什么指引,基本上是由着我的性子来。父亲只告诉我,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能出一个清华博士不容易,是国家投入了许多金钱和资源在培养你,要爱国,要回报祖国。
在清华读书这些年,我相继走访过欧洲、亚洲、非洲的17个国家,也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短暂地居住过,流利的英文让我能更深入地了解不同国度的人文民俗和政治生态。
我记得,有一年在印度参加学术交流会,去酒店的路上经过印度的贫民窟,几百个居民各拿一个水桶围着一根自来水管排队接水,这一幕让我震惊,印度和中国虽同为发展中国家,但在基础设施上的差距何其之大……
在非洲的肯尼亚,同行的学者在超市里买咖啡,我在外面等待的间隙里看到一个盲人乞丐在唱歌,我走过去递给他一美元当作对歌声的奖赏。当他得知这是一美元后,开心地好像自己得到了全世界的财富。这让我看到,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没有选择留在国外,我都会坚定地回答:“那儿不是家。”这些年,我当然也见识过欧美国家的富裕多彩,但也见到了他们枪支泛滥、毒品肆虐带来的社会问题,还看到了他们因为中国崛起、优越感不再而感到的深深焦虑。而我,只有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的内心才觉得踏实,才有归属感,异国他乡纵然美,但心始终是漂泊的。

三
2017年7月,我回到了家乡,成为湖南大学的一名老师,也回到了父母身边。父亲今年已经75岁,母亲也有73岁,是需要我尽心照顾的年纪了。
曾经我一度认为父母亲并不算般配,缺少点荡气回肠的爱情,如果不是遇上特殊的时代,应该不太可能走到一起。可当我现在再看着满头白发的父亲和略有驼背的母亲,他们之间在看似毫无关照中偶尔无意的交流,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谁说轰轰烈烈、至死不渝才是爱情呢?细水流长、鸡毛蒜皮同样是爱情。
作为独生子女,我们这一代人往往不懂得分享,不懂得妥协,不懂得付出。但是父母之间的相处模式告诉我,爱并不是执着于自己的感受,而应该努力去看到另一半所做的努力。爱不是占有,是给予。
一直以来我和父母的关系都很融洽,唯有在我的感情和婚姻方面发生过争吵。像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我也一度十分抵触婚恋。母亲气急了便会摔门而出,父亲倒是很沉得住气。其实我也明白,他们并非是受传宗接代的观念束缚,而是害怕作为独生子女的我今后会很孤独。这与我的一个清华老师非常不同。他曾对自己不婚不育的女儿怒吼:“结婚生孩子是你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 我很庆幸父母没有将婚恋问题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
父亲说:“恋爱中的人就像是得了一场感冒。”我挺惊讶,年过七旬的老头儿能说出这么洋气的话来,哪知父亲对此还有自己的一番理解。他说,感冒发烧的人脑子都不太清晰,判断力也会下降,会做出很多傻事来,所以对恋爱中的自己和别人都要多一些包容,特别是不要贸然去评价别人的感情生活。
我时常细细品味父亲的话语。小时候的我忙于学业,并不了解我的父母,18岁去北京上大学再到回来长沙,已是匆匆十几年过去,在父母身边的日子少,交流也不过局限在琐事范围。直到这几年,我从一个被照顾者变成被依赖者,才对父母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我发现老人和小孩一样,需要哄,讲多少道理都不如一个撒娇。和他们在一起生活,也让我观察到“老去”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做同样一件事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虽然仍然有着对新生事物和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但却没有能力再去探寻他们;一个年老的身躯里面有一颗挣扎的、年轻的心……
于是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些“小规矩”。例如,如果出差需要坐飞机,一定在登机前给他们发个信息说“我爱你们”;如果吵架,一定要在睡觉前和好,不要等到第二天;在父母需要的时候,一定第一时间赶到他们身边……这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孝顺,而是因为我怕该说的话如果没说,该给予的如果没给予,未来的自己可能会后悔。
如果我们生存的社会能够分出大小,父母和子女所构成的这个关系可能是最小、最原始的社会,但对每一个人来说,也可能是最大、最持久的社会。在这里,我们见证了爱,学会了面对生活的困苦,也常常忽略身边最亲近的人。
当我在这个年纪再回到父母身边,在一个更成熟的维度上去观察他们,好像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父母或许老派,但并非不比我们智慧,他们的人生经历、爱情故事、人生体验都在潜移默化影响着我和我的人生。
口述 | 何韵 文 | 政协融媒记者 仇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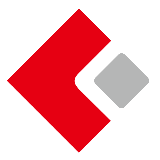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