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维坦按:
文中提到的“二分心智假说”很有意思,按照朱利安·杰恩斯的观点,人类一直到3000年前,大脑都一直处于这种分裂的状态,其体验外部世界的方式,与其说他们在遇到新奇或意外状况下能够有意识地做出评估,不如说会产生幻听,或是幻想“神”给出了建议或命令,然后无条件服从这些幻觉。
换言之,他们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思维过程本身。这种“指令性幻觉”经常会指挥患有精神分裂症主要症状的患者,而杰恩斯的假说为“指令性幻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杰恩斯在分析了《伊利亚特》、《旧约》后认为,其中没有提到任何一种认知过程 (例如内省) ,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作者具有自我觉察。他由此认为,早期人类的心灵状态与我们十分不同。 他还指出,现代精神病理学所提及的精神分裂症就是人类早期二分心智所遗留的痕迹 (当然,这也是他遭到诸多批评的所在) 。
快问快答:你是右脑型还是左脑型?
你可能会很快回答出这个问题。如果你是富有创造力和直觉的人,喜欢音乐、图像和其他形式的艺术,那么你就是右脑型。反之,如果你更善于分析和逻辑,喜欢数学和模式识别,那么你就是左脑型。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是哪一种,网络上有无数的在线测试,帮助你确定、加强和最大限度地发挥你固有的认知优势。
事实上,左右脑理论已经渗透到各种行业——尤其是商业领域,许多公司雇佣右脑员工担任更具创造性的角色,左脑型员工担任管理职位。鉴于其被广泛接受和使用,这一理论一定是基于最新的神经科学,对吗?
抱歉,这种观点并不准确。
就像认为我们只使用了大脑10%的说法一样,左脑/右脑理论也是一个持久的流行心理学神话——这种说法就像许多性格测试(包括著名的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测试)一样,其预测能力和占星术也差不了多少。不过,像许多现代科学神话一样,左-右脑二分法是基于某种事实的内核。某些大脑功能的确集中在不同的半球,但这种侧化(即功能分布于不同半球的现象)比流行心理学所呈现的简单模型要复杂得多。
那么,这个现代神话究竟有多少是真的,又有多少是完全虚构的呢?

© Wikimedia Commons
从外部看,大脑似乎是完全对称的。底部是后脑,由两个结构组成:脑干,它控制自主功能,如呼吸和消化;以及边缘系统,它控制更复杂的基本功能,如记忆处理、情绪和动机。后脑下方是小脑,它负责感官处理和运动协调;而包裹着它的是前脑,负责更高级的认知功能。大脑沿中线分为两个半球,每个半球又进一步分为四个叶:额叶、顶叶、颞叶和枕叶。小脑也分为对称的两个半球,而大脑半球通过称为胼胝体(corpus callosum)的一束神经纤维相互连接。
不过,早在19世纪60年代,证据就开始表明大脑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对称。1861年,法国医生兼解剖学家保罗·布罗卡(Paul Broca)遇到了两位有显著语言障碍的病人。第一位病人,路易·维克多·勒博涅(Louis Victor Leborgne),几乎完全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只能发出一个词:“temps” [发音为“tan”或“tahn”]——即法语中的“时间”。奇怪的是,他的其他认知能力——包括阅读、写作和理解口语的能力——并未受损。

勒博涅的大脑,由布罗卡存放于巴黎迪皮特朗博物馆(Dupuytren museum)。© Neurosciences and History
第二位病人,拉扎尔·勒隆(Lazare Lelong),也有类似的障碍,他只能说出五个词:“是”、“否”、“三”、“总是”和“lelo”——对自己姓氏的错误发音。在两位病人去世后,布罗卡对他们的大脑进行了尸检,发现两人都患有神经梅毒(neurosyphilis),导致他们大脑的同一区域出现了损伤:左半球额叶第三回。
这些发现使布罗卡在1865年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语言在左侧额叶第三回的定位》(Localization of Speech in the Third Left Frontal Cultivation)[1],他在论文中推测,言语生产集中在这个区域,现在被称为布罗卡区(Broca’s Area)。
十年后,1874年,德国医生兼解剖学家卡尔·韦尼克(Karl Wernicke)描述了一种类似但又不尽相同的失语症,患者能够流利地发音,但所说的句子是缺乏结构和意义的无意义语句——今天被称为“语词沙拉”(word salad)。奇怪的是,这些句子保留了普通语音的节奏和句法,而患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语言存在任何紊乱。他们对语言的理解能力,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通常也受到损害。和布罗卡一样,韦尼克发现,这种损害是由大脑中一个特定区域的损伤引起的:这个区域位于左后侧额叶,现在被称为韦尼克区(Wernicke’s area)。
这些观察使韦尼克将失语症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布罗卡的或称为运动性失语症(Motor aphasia),和韦尼克的感觉性失语症(Receptive aphasia)。
布罗卡和韦尼克的发现让心理学家得出结论,语言的产生和理解完全集中在大脑的左半球。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真正开始理解大脑侧化的程度。20世纪60年代初,神经外科医生开始实施一种全新的激进手术,帮助严重癫痫的患者。
这种手术称为胼胝体切断术,涉及切断胼胝体的神经纤维,以防止癫痫信号从一个半球传导到另一个半球。最初,人们认为这项手术没有副作用,但随着对患者的长期观察,他们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奇怪。他们在执行日常任务时开始偏爱使用右侧身体,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左侧的任何刺激。例如,如果有什么东西碰到了左臂,他们不会注意到;如果一个物体放在他们的左手里,他们会否认其存在。

出于对这种奇怪行为的兴趣,1962年,加州理工学院神经生理学家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和他的研究生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开始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实验,试图弄清这些裂脑患者的脑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的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大脑的理解。
虽然胼胝体以前被认为是一个功能不大的结构,心理学家卡尔·拉什利(Karl Lashley)甚至曾推测它的作用不过是“防止两个半球下垂”,但斯佩里和加扎尼加很快发现了它在大脑功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由于脊椎动物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奇怪现象,我们的神经系统是交叉控制的,这意味着每个半球主要接收来自身体另一侧的信息。例如,视神经将来自眼睛的视觉信息传递给我们的枕叶,这些神经在视交叉处交叉,这意味着来自右眼的信息传递到左半球,反之亦然。同样,每个半球控制身体的另一侧,例如左半球中风会导致身体右侧瘫痪,反之亦然。通常,这种看似反直觉的安排可以很好地工作,因为信息会立即通过胼胝体传递到正确的半球。但在裂脑患者中,这种沟通通道不再存在,这意味着传递到特定半球的信息会停留在那个半球中。此时,事情变得奇怪了起来。
斯佩里和加扎尼加通过刺激身体的另一侧来分别探测患者的半球功能——例如,通过给右眼呈现一个图像来刺激左半球。在一项早期实验中[2],他们在患者的视野中闪现了一系列灯光。当被要求报告看到灯光的时间时,患者只报告了右侧的灯光。但当被要求在看到灯光时用手指示出来时,他们成功地报告了两侧的灯光。

接下来,斯佩里和加扎尼加投射了单词“HEART”,使得字母“HE”出现在患者的左侧视野中,字母“ART”出现在右侧视野中。当被要求报告他们看到了什么时,患者口头回答“ART”;但当被要求用左手指向他们看到的单词时,他们指向了“HE”。类似地,如果一个物体放在患者的右手中,他们可以轻松地说出它的名称,但当被要求用右手指向相同物体的图像时,他们却无法做到。当侧向反转时,患者可以轻松地指向物体,但令他们感到困惑的是,无法说出其名称。这些实验证实了语言处理能力几乎完全局限于左半球,而右半球则专门负责视觉感知任务,例如识别面部和情绪以及发现物体之间的差异。
尽管这些差异已足够令人费解,生活在“裂脑”状态下的患者的体验有时更加离奇,患者会感到自己确实有两个独立的大脑——这些大脑常常彼此冲突。例如,患者曾报告他们用一只手系扣子,而另一只手却会自发地解开这些扣子,或者用一只手把物品放进购物车,而另一只手却会把它们放回架子上。许多患者甚至能够用双手同时绘制两幅不同的图像,但由于右半球在空间推理能力上的优势,左手在这一任务上通常优于右手。

《奇爱博士》中的异手综合症:左右脑互搏下,左手控制不住右手行纳粹礼。© Pinterest
在极少数情况下,这种现象甚至会表现为“异手综合征”(Alien hand syndrome),患者的一只手似乎有自己的独立意志,有时甚至试图勒住患者自己或他人。这种现象也有时被称为“奇爱博士综合症”(Dr. Strangelove Syndrome),以斯坦利·库布里克1964年电影中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的角色命名,该角色就表现出了类似的症状。 不幸的是,除了让“作乱的手”忙于其他任务或在夜间限制其活动以防止伤害外,没有治愈该病的方法。
斯佩里在1974年发表的一篇开创性论文中总结了他的研究成果,这篇论文最终为他赢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他总结道:
“……[每个半球]确实是一个独立的意识系统,它在感知、思考、记忆、推理、意愿和情感方面都以人类特有的水平运行……左半球和右半球可以同时在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心理体验中保持意识,这些体验平行进行。”
斯佩里特别得出结论,左半球专长于逻辑、排序、线性思维、数学、硬性事实和文字思维。相比之下,右半球处理“柔性”任务,如想象、整体思维、直觉、视觉空间处理、面部识别以及解读非语言社交线索。
事实上,根据斯佩里的实验,数学思维的这种侧化几乎已经完成:
“……通过非语言输出以及将感官输入限制在左视野或左手上的次半球的数学测试表明……次半球的计算能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通过操控弹珠或木棒,观察左视野闪烁的灯光点,并用左手指示……(裂脑)患者可以成功地匹配数字,或者将一个数字加到小于10的数字上,但当要求他们加减两个或以上的数字时,以及在最简单的乘除运算时,他们都失败了。”
后来,斯佩里观察到,右半球实际上可以进行小于20的加法运算——这是左半球对数学思维完全主导地位的唯一例外。

后来的观察似乎证实了斯佩里的发现,神经学家得出结论,原发性计算失能(Primary acalculia),即根本无法理解和进行数学运算,仅在大脑左顶叶受损时才会发生[3]。相比之下,由右半球受损引起的继发性计算失能(Secondary acalculia),影响的是大脑通过感官接收数学信息或通过语言表达这些信息的能力,但不会影响大脑理解和处理这些信息的基本能力。
侵入性较小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大脑的任务偏侧化。1973年,旧金山兰利波特神经精神病研究所的罗伯特·奥恩斯坦(Robert Ornstein)博士和戴维·加林(David Galin)博士要求受试者在脑电图(EEG)监测他们各自半球活动的情况下进行各种认知任务[4]。当要求他们进行心算、思考写信或执行语言练习(如列出以字母R开头的动词)时,受试者的左半球产生了表明注意力和活动的快速脑电波,而他们的右半球则产生了表明放松的低频α波,这表明在这些任务中右半球基本上处于关闭状态。然而,当受试者被要求用彩色积木拼图、记住音乐音符的顺序或使用画板绘图时,情况正好相反,右半球产生了快速脑电波,左半球则产生了α波。
奥恩斯坦和加林总结道:
“我们的看法是,在大多数日常活动中,我们只是交替使用不同的认知模式,而不是将它们整合在一起。这些模式相辅相成,但不能相互替代。”
然而,尽管斯佩里曾警告说:
“……右左认知风格的实验性极性这一理念非常容易被泛化。”
……但已经为时过晚。在1973年《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讨论奥恩斯坦和加林实验的文章中[5],两位科学家表示,不同的人一侧半球占主导地位,塑造了他们的天赋和能力:
“理想情况下,我们应该能够根据任务需要激活相应的半球,关闭另一侧半球。但事实上我们并不能总是做到这一点。‘许多人被一种或另一种模式所支配,’奥恩斯坦博士指出。‘他们要么难以应对手工艺和身体动作,要么难以处理语言。’文化显然对此有很大影响。来自贫穷黑人社区的孩子通常更多地使用他们的右半球——例如,在不完整图形的模式识别测试中,他们的得分高于白人,但在语言任务上表现不佳。其他已经学会用言语表达一切的孩子发现,在模仿网球发球或学习舞步时,这种方法是一种障碍。用言语分析这些动作只会减慢他们的速度,并干扰通过右半球的直接学习。”
“我们没有应有的灵活性,”奥恩斯坦说,“我们幻想自己拥有比实际更多的控制权。”在人生早期,许多人似乎就被塑造成“左半球类型”,主要在语言世界中运作,或者“右半球类型”,更多依赖非语言表达方式。这是两种基本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文章进一步指出:
“奥恩斯坦和加林博士认为,当总是习惯性地使用同一侧大脑变得过于明显时,它会限制一个人的个性。这两位研究人员目前正在研究一种测试,可能帮助他们判断一个人长期偏爱哪一侧大脑,并且这种习惯是否妨碍了在必要时将主导权转移到另一侧。他们计划在那些真正专精于某种领域的人身上进行测试,比如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一个没有任何兴趣爱好的左半球类型)和右脑占主导地位的陶艺家、舞蹈家和雕塑家(‘最好是那些在语言方面有困难的人’)。他们预计会在这两组人之间发现显著差异。这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工具,用以引导孩子或成年人发现自己新的层面,开放他们体验。”
由此,一个持久的流行心理学迷思诞生了,各类出版物包括《时代》杂志、《哈佛商业评论》和《今日心理学》很快也加入了“左脑/右脑”的行列。这个理论通过贝蒂·艾德华(Betty Edwards)在1979年出版的《用右脑绘画》(Draw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rain)一书进一步得到了普及。
该书中,作者提出了各种技巧,帮助人们绕过“分析性”的左脑,从而让视觉创造力蓬勃发展。如今,左脑/右脑理论催生了大量的在线测试、研讨会和其他材料,旨在帮助人们确定哪一侧大脑占主导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能,甚至加强大脑中非主导的那一侧。这种观念甚至渗透到了商业领域,一些公司试图雇佣右脑型员工来从事更具创造性的角色,而左脑型员工则担任管理职位。
但正如我们在研究人类心智时常常遇到的情况一样,事情远不像流行心理学让我们相信的那样简单。

虽然斯佩里、奥恩斯坦等人的发现似乎表明右半球在数学思维和语言处理方面几乎没有作用,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斯佩里观察到,右半球在所谓的左脑任务中也发挥了活跃的作用。例如,当一位患者通过左眼看到他女友的照片时,虽然他无法说出她的名字,但却能够用拼字游戏的字母拼出她的名字。
他们还发现,尽管左脑擅长直接的词汇联想,但右脑在识别更微妙的关系和暗示上表现更好。例如,当左脑看到单词“foot”时,它更擅长从词汇列表中挑出相关词汇如“heel”。但是,当右脑看到两个额外的词“cry”和“glass”时,它更容易找出连接词——在这种情况下是“cut”。
右脑在数学思维中也扮演了比预期更大的角色。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教授卡拉·费德梅(Kara Federmeier)解释道: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同意‘逻辑’和‘创造力’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让我们考虑一个(相对来说)更明确的例子:数学能力,这通常被认为是‘逻辑’左脑擅长的部分。
数学能力有很多种,从能够估算两个集合中哪个物品数量更多,到计数,到各种类型的计算。研究表明,总的来说,数学能力的形成来自于两个半球的处理(特别是每个半球中的一个叫做顶内沟的脑区),而且任何一个半球受损都会导致数学能力的困难。左脑在数学中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如计数和背诵乘法表这样的任务上,这些任务依赖于大量记忆的语言信息(因此,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逻辑’并不完全一致!)。而在一些数学相关任务中,右脑也有优势,尤其是在估算物体数量时。这种模式,即两侧大脑都对大多数认知技能作出关键贡献,普遍存在。要做到逻辑或富有创造力,需要两个半球共同作用。”
确实,按照人们对左脑/右脑分工的普遍认识,我们以为那些右脑受损的人会变得冷酷无情,但却是超理性的计算和决策机器,就像《星际迷航》中的瓦肯人一样。然而,现实中,这些人甚至连做基本的决策或计划都有困难,因为他们缺乏直觉和情感功能,无法构想出整体大局并将逻辑转化为实际行动。逻辑和情感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彼此对立;要在现实世界中有效运作,两者都是必需的。
最近的研究表明[6],许多认知功能实际上是由两个半球平均分配的,包括处理视觉和听觉刺激、空间操控、面部识别、艺术能力、数值估计和比较。即使是布罗卡、韦尼克等人确定的核心语言能力的左侧化也并不总是正确的。
例如,虽然布罗卡区和韦尼克区通常位于左半球,但在5%的右撇子和30%的左撇子(记住,他们的惯用手由另一半球控制)中,布罗卡区和韦尼克区却位于右半球[7]。事实上,不同认知功能的侧化在个体之间差异很大,因此神经外科医生在进行肿瘤切除等侵入性脑外科手术之前,通常会进行特殊测试来查明这些认知位置。该检查被称为颈动脉内注射戊巴比妥钠或Wada-Milner测试[8],其涉及向一个半球或另一个半球注射巴比妥类镇静剂以使其失效,并要求患者执行各种认知任务。


威廉(William)的大脑在子宫内发育异常。2005年7月12日出生后,他每天要经历多达80次癫痫和痉挛,他的父母决定为其实施一项激进的脑半球切除手术。手术前,医生警告他,手术可能会让他失去行走能力。但手术后的八年,这个四年级学生不仅能跑,还能投篮和得分。© Indianapolis Monthly
大脑侧化的普遍观念也无法解释“神经可塑性现象”——大脑适应物理损伤的惊人能力。因癌症或其他疾病导致一整个大脑半球被切除的儿童,仍然能够过上完全正常的生活,大脑通过重组来使用仅存的半球执行所有必要功能[9]。在经历类似手术或遭受创伤性脑损伤的成年人身上,也观察到了这种神经可塑性,尽管程度较轻。
好吧,所以大脑比流行文化让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其功能也比我们预期的分布得更均匀。但不同的人肯定会偏向使用大脑的一侧吧?毕竟,如何解释有些人更具逻辑性和分析性,而另一些人则更具创造性和艺术性?
不幸的是,科学并不支持这一观点。
2013年,犹他大学贾里德·尼尔森(Jared Nielsen)和同事们进行了一项研究[10],分析了1011名年龄在7到29岁之间的个体在执行各种认知任务时的神经活动,使用的是静息态功能连接磁共振成像(RS-FCM-MRI)设备。研究发现:
“确定了9个左侧化和11个右侧化的枢纽……[作为]显著侧化的连接。左侧化枢纽包括默认模式网络中的区域……而右侧化枢纽包括注意控制网络中的区域……左侧化和右侧化枢纽形成了两组可分离的相互侧化区域网络。仅涉及左侧化或仅涉及右侧化枢纽的连接在受试者中显示出正相关,但仅限于共享节点的连接。脑连接的侧化似乎是局部而非全球性的大脑网络属性,我们的数据与个体间更‘左脑’或更‘右脑’网络强度的整体大脑表型不一致。随着年龄的增加,侧化的增加很小,但未观察到性别差异……[我们还发现]不同个体的侧化连接是相互独立的,大多数功能侧化在7岁之前就已经发生。”
换句话说,虽然各种认知功能的定位在个体之间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没有哪一侧半球在显著程度上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许多技能和才能不是来自某一半球的更多工作,而是来自于两半球更高效的合作。例如,被认为在数学或音乐方面有天赋的儿童往往表现出两个半球之间的更好交流,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结合逻辑/分析和创造/直觉的能力。相反,那些在某些任务上挣扎的人,不一定是因为大脑某一半球较弱,往往是因为一半球为执行通常由另一半球处理的任务而发展起来的。正如几乎所有的认知任务一样,即使是最薄弱的技能也可以通过练习逐渐得到加强。
尽管有超过50年的研究驳斥了这种观点,但估计仍有超过68%的人相信左脑/右脑的迷思。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人类喜欢思考自己,并想出各种系统将自己和他人划分为整齐的类别。
像星座和许多性格测试一样,用来确定左脑或右脑占主导地位的测试利用了一种被称为巴纳姆效应(Barnum effect)的心理现象——即,人们倾向于相信那些看似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制的描述,实际上这些描述足够模糊,以至于可以适用于任何人。
这个效应常被占星师、通灵者和其他骗子利用,最著名的例子是舞台魔术师、超自然现象揭秘者詹姆斯·兰迪(James Randi),他向一群学生发放了个性化的星座运势,并要求他们评估描述的准确性。几乎毫无例外,学生们都认为这些星座运势非常准确。然后兰迪要求学生们交换星座运势,这时他们才发现实际上都收到了相同的内容!

左脑/右脑的谬误,验证了我们日常观察中一些人似乎更具逻辑性和分析性,另一些人则更具创造性和直觉性,并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它也让我们能够为自己的不足找到借口:我数学不好,不是我的错,你看,我天生就是右脑型的!但实际上,我们的认知技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基因、成长环境、心态以及训练和教育——这些都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右脑型”或“左脑型”。
尽管认知功能的侧化可能对我们的个性或天生技能没有显著影响,但它仍然对大脑的运作方式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尽管每个半球接收到和处理的信息通常通过胼胝体与另一半球共享,但这种共享并非总是可能的。正如心理学家拉·费德梅解释的那样:
“每个半球内部的处理依赖于一个丰富、密集的连接网络。连接两个半球的胼胝体对于纤维束来说很大,但与每个半球内部的连接网络相比,它非常小。因此,从物理上讲,让两个半球完全共享信息或以完全统一的方式运行似乎并不可行。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让两半球各自独立运行其实是更聪明的选择。将任务分开并允许两半球独立工作并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同一问题,似乎是大脑的一种良好策略。
我最喜欢的一个发现来自于一项实验,我们用形容词改变了同一个名词的含义。例如,词语‘green book’(绿皮书)指的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很容易在脑海中形成图像的东西。然而,给出‘interesting book’(有趣的书)时,人们通常会想到书的内容,而不是其物理形式,因此同一个词变得更加‘抽象’了。
我们想看看,对于完全相同的词语,具体性差异是否会出现,以及两半球是否同样受到具体性的影响。在这项实验中,我们发现……左脑对词语组合的可预测性非常敏感。能与‘green’搭配的名词比与‘interesting’搭配的要少得多,当这些词语首先呈现给左脑时,大脑活动反映了这一点。
然而,令我们惊讶的是,与‘interesting book’相比,右脑对‘green book’表现出更多与图像相关的大脑活动。因此,尽管左脑在语言处理方面显然非常重要,但右脑可能在创造伴随语言理解的丰富感官体验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这也是阅读如此令人愉快的原因。”
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的大脑胼胝体完好无损,有时大脑仍然会表现得像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就像斯佩里的裂脑患者一样。
更奇怪的是,直到人类历史上相对较近的时期,这种拥有‘两个意识’的状态可能在字面意义上是真实存在的。

据说《二分心智的崩溃与意识的起源》是大卫·鲍伊最喜爱的书籍之一。© The Bowie Book Club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朱利安·杰恩斯(Julian Jaynes)在他1976年的著作《二分心智的崩溃与意识的起源》(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中提出,距今约3000年,地中海青铜文明以前的时代,人类的正常心灵曾经以“二分心智”的方式普遍存在。两个半球作为独立的实体运作,“主导”的左脑产生想法并传达给“从属”的右脑,后者则服从并执行这些指令。

根据杰恩斯的说法,这种二分心智解释了古代人类将思想和灵感归因于缪斯或众神的观念。由于他们无法意识到这些想法是来自他们自己大脑内部的,他们会将这些思想体验为听觉幻觉,并将其来源归因于外部——通常是超自然的来源。这种体验类似于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他们将内部产生的思想表现为听觉幻觉。
实际上,精神分裂症、自闭症和许多情绪障碍(包括抑郁和躁郁症)都与认知功能的不对称性显著变化有关[11][12]。例如,左脑更多与积极情绪相关,右脑更多与消极情绪相关,抑郁症患者往往左脑活动过多。而精神分裂症则与两半球活动的对称性减少相关。

不过,杰恩斯的理论并不意味着人类大脑曾经物理上分裂过;古代人类的神经结构与我们完全相同——包括胼胝体等结构。古人的心理图式使他们能够对情况做出反应、产生想法并采取行动,而无需内省能力来反思这些想法并了解其内部起源。
换言之,人类缺乏元意识或自我意识。杰恩斯认为,这种心理模式是古代人类更简单的群体生活条件的产物,这些条件不需要一个自省的、统一的心智来运作。只有当人们开始生活在更复杂的社会中,如城市国家,并开始发展书写时,大脑的两半才开始融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统一的、自省的意识。
在杰恩斯理论的基础上,英国精神病理学家、哲学家伊恩·麦克吉尔奇斯特(Iain McGilchrist)更进一步,他认为大脑的统一化和侧化已经过于偏向了一个方向——这对现代西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他2009年出版的《主人与使者:分裂的大脑与西方世界的形成》(The Master and His Emissary: the Divided Brain and the Making of the Western World)一书中,麦克吉尔奇斯特认为,不仅两个半球功能不同,它们还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并推动不同的伦理与价值观。比如,左脑倾向于将复杂、微妙的主题,如伦理学,简化为简单的规则和标准,而右脑则能够更全面地将世界视为互相联系的系统。麦克吉尔奇斯特指出,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明越来越受到左脑思维的支配,这种思维推动了一种狭隘的、还原主义的宇宙观,这导致了我们许多现代全球性问题。
尽管杰恩斯和麦克吉尔奇斯特的观点影响深远且广受欢迎,但它们也招致了大量批评,许多神经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这些理论和左脑/右脑的流行心理学观念一样,过于简化并扭曲了大脑侧化这一复杂而微妙的事实,并且基于不可靠的历史证据。
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正如苏格兰生物学家约翰·伯顿·桑德森·霍尔丹(J.B.S. Haldane)所言,人类的大脑不仅比我们想象的更奇怪,而且很可能比我们能够想象的更奇怪。
参考文献:
[1]pubmed.ncbi.nlm.nih.gov/3530216/
[2]www.jstor.org/stable/24926082
[3]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476153/
[4]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0028393274900529
[5]www.nytimes.com/1973/09/09/archives/we-are-leftbrained-or-rightbrained-two-astonishingly-different.html
[6]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300231/
[7]www.nature.com/scitable/blog/student-voices/lefthand_man/
[8]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117406/
[9]www.indianapolismonthly.com/longform/boy-with-half-brain-william-buttars/
[10]pubmed.ncbi.nlm.nih.gov/23967180/
[11]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0218831/
[12]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931527/
文/Gilles Messier
译/tim
校对/tamiya2
原文/www.todayifoundout.com/index.php/2024/09/are-people-actually-right-or-left-brained/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tim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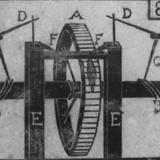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