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老少爷们儿们!在下张大少。
我喜欢看、思考或与朋友讨论各种各样的埃舍尔作品。其中包括他画的野花、意大利风景、“不可能的图形”和周期性的绘画。我最喜欢的是他的野花。它们既有力度又微妙。它们强调本质而忽略其他,这也是好的自然科学模型的特征。然而,我预计埃舍尔的周期性绘画将是他所有作品中影响最持久的。本文探讨了这些绘画对科学家的吸引力。
当引入废除对称平面的概念时,就意味着对称平面已经建立。的确如此,因为反射是最常见的对称。说到对称,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人体的两侧对称,无论这种对称多么近似。在这种情况下,对称平面将人体一分为二。对称平面在自然界和人类的创造物中无处不在。然而,就空间的良好利用而言,它的作用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本文要传达的信息是,无论是埃舍尔的周期性绘画,还是晶体结构,抑或是生物分子的相互作用,对称平面都不是常见的对称元素。
最密堆积与互补
埃舍尔的周期性绘画提供了最密堆积的模型。它们被广泛用于展示二维图案的对称特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密堆积是通过结构元素排列的互补性实现的。生成这些图案的对称运算很少包括对称平面。只有在结构元素本身具有高度对称性的极端情况下,才会涉及到对称平面。然而,对于任意形状的结构,如果使用对称平面,就会使相当大块的表面未被覆盖,从而排除最密堆积。最密集堆积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利用可用空间,无论是表面还是三维空间。当然,在埃舍尔的作品和大多数晶体学教材中,重点都是二维平面。
最大限度地利用可用空间是最密集堆积的目标。自伽利略以来,“大自然厌恶真空 ”这一经验之谈被反复提及,但却很少有人仔细研究。我的论断是,在自然界中寻找结构元素最佳排列方式的最终目标并非受这一原则支配。相反,在更深层次上存在着一个基本原则,即所寻求的排列方式应该提供最大的稳定性,也就是最低的总能量。当结构元素之间可能发生的相互作用达到最大程度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前提是这些元素具有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当相互作用的表面积达到最大时,相互作用的数量就会达到最大。两个任意形状相同的部件互补排列就能满足这一条件。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两块材料通过一个对称平面相连,互补性就远远达不到最大化。在此,我们将引用从卢克莱修到分子生物学最新发现的一些例子,来说明互补性概念的实用性。
用卢克莱修的话说
埃舍尔的画是平面上最密集堆积的最美范例。一个物体的空隙被另一个物体的突起填满。
卢克莱修(约公元前 96 年-约公元前 55 年,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和哲学家)在两千年前就提出了最佳堆积排列的基本原则。事实上,他提出了互补原则。卢克莱修在他的《自然论》(Deerum natura)中指出:[3]
事物的面料呈现出相匹配的对立面、
一个凹,另一个凸,就会形成最紧密的结合,反之亦然。
重要的预测
分子晶体提供了自然界最密集堆积的无数实例。伟大的俄罗斯晶体学家亚历山大·基塔哥罗斯基(Aleksandr I. Kitaigorodskii)在这一科学领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4] 他预言,在晶体结构中,低对称性的三维空间群比高对称性的空间群更为常见。这是在很少有人通过实验确定晶体结构的情况下做出的预测。
Kitaigorodskii曾经说过,“第一流的理论预测,第二流的理论禁止,第三流的理论在事后解释。”即使是第三流理论也很重要,因为即使我们没有预料到我们的发现,至少我们想在事后理解它们。然而,当我们的发现可以被合适的理论或模型预测时,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所研究的现象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因此,Kitaigorodskii对三维空间群分布的成功预测意味着对分子堆积基本原理的理解。
Kitaigorodskii发现分子的堆积是空间互补的。为了达到最密集的堆积,任意形状的分子以最佳的排列互补。因此,如果分子以一个分子的空腔与另一个分子的空腔相匹配的方式彼此转向,则具有空腔和突起形状的分子将不会最有效地利用可用空间。如果它们通过反射相关,就会是这种情况。相反,最好的排列是当一个分子的突起与另一个分子的空腔相吻合时,以此类推。这是互补原则的另一种表达,它在科学中以如此多的方式出现,因为它在自然界中也是如此。
进入分子生物学
当然,空间互补原则本身并不是Kitaigorodskii的发明。他只是将它发挥到了极致,最终预测出晶体结构中230个三维空间群的频率分布。
1940年,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结构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和由物理学家转为生物学家的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uck)——联合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他们在《科学》上发表的论文标题为 “生物过程中分子间作用力的性质”。[帕斯卡尔·乔丹(Pascal Jordan)曾提出,量子力学稳定相互作用优先作用于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分子或分子的一部分。该建议与生物分子合成过程有关,导致细胞中分子的复制。鲍林和德尔布吕克认为,互补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比相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更重要。他们认为,范德华吸引和排斥、静电作用、氢键形成等分子间相互作用使两个并列的具有互补结构的分子系统具有稳定性,而不是两个具有相同结构的分子。因此,他们认为在讨论分子间相互作用时应首先考虑互补性。
通过双螺旋最终发现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功能机制,是分子生物学中互补性最著名的例证。这一发现的直接关键是 Erwin Chargaff 发现的碱基互补性。
低对称性更好地堆积
鲍林和德尔布里克对分子间作用力性质的描述似乎直接适用于分子晶体的堆积。对于Kitaigorodskii来说,除了他出色的猜想之外,他还花费了多年时间进行艰苦的测量,才得出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正确结论。
在他的科学研究计划的早期,Kitaigorodskii决定使用相同但任意的形状来探索平面上可能的最佳排列。他建立了二维层的对称性,使得相对于层晶胞的倾斜轴,分子的任意倾斜角度的配位数为6。他发现这样的排列总是在最密集的排列中。我们在这里引用一个任意形状分子的一般情况的例子。Kitaigorodskii致力于选择二维空间群的任务,对于这些空间群,有效地堆积任意形状的分子是可能的。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方法,因为结果将回答为什么在晶体中少数空间群出现率高而许多230空间群几乎不出现的问题。
Kitaigorodskii首先研究了致密堆积问题。对于对称性最小的平面群(仅平移对称,p1),如果平移周期(t1和t2)以及它们之间的角度选择得当,任何分子形式都有可能实现最密集的堆积。由两次旋转产生的平面群(p2)也是如此(图 1)。另一方面,具有对称平面的平面群(pm 和 pmm)不适合最密集堆积。由于在这些排列中存在对称平面,分子的凸面部分会面向其他分子的凸面部分。这种排列方式不利于密集堆积(图 2)。具有滑移反射的平面群(pg 和pgg)可能适合 6 配位。这一层的密度不是最大的,在分子的不同方向上只能实现 4 配位(图 3)。对于对称性较高的平面基团,有效利用空间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分子本身具有反射对称性,即保留了一个对称平面,那么即使是在对称元素数目较多的对称组中,也有较好的机会进行更密集的堆积,其中包括对称平面。

图1:空间群p1和p2的最密堆积,摘自 Kitaigorodskii [4]

图2:空间群pm和pmm中的对称平面阻止密集堆积,摘自 Kitaigorodskii [4]

图3:pgg空间群的两种堆积形式:一种是最密集的堆积,另一种是利用分子的不同取向将配位数从六个减少到四个;摘自 Kitaigorodskii [4] 。
在考虑了用于密集堆积的平面群之后,下一步就是应用几何模型来研究三维空间群是否适于这种堆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是选择那些可以进行层间堆积的空间群,使其具有尽可能多的配位数。显然,镜面平面不适用于重复层。
低对称性晶体种类是有机化合物的典型。通过与层面成任意角度的平移,或通过倒置、滑动面,或通过螺旋轴旋转,可以实现层的最紧密堆积。在极少数情况下,最紧密的堆积也可以通过两次旋转来实现。
Kitaigorodskii从最密堆积的角度分析了所有230个三维空间群,发现只有6个空间群可用于任意形式分子的最密堆积(p1,P21,P2J/c,Pea,Pna,P212121)。对于有对称中心的分子,合适的三维空间群就更少了(P1,P21/C,C2/c,Pbca)。在这些情况下,分子的所有相互取向都是可能的,而不会失去六配位。
低对称空间群之一(P21/c)在有机晶体中占据着引人注目的特殊地位。该空间群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可以在单位晶胞的所有三个坐标平面上形成密度最高的堆积层。在提供最密集堆积的空间群中,还有另外两个空间群(P21 和 P212121)。根据统计分析,这三个群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群。对于手性分子,这些可能性只适用于左旋或右旋形式。
Kitaigorodskii关于分子有机化合物在空间群上的分布的开创性工作不仅是科学信息的重要来源,也是科学研究的典范。
复制DNA
DNA分子的作用机制以互补性为特征,但复杂程度不同。聚合酶链式反应的发现者Kary Mullis这样描述它:[6]
DNA有一个非凡的特性,即任何特定的嘌呤和嘧啶碱基序列都有两种形式可以串联在一起。可以串成一条链,也可以串成另一条顺序相反的链;这就是互补,它们被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这是一个美丽的螺旋,但它也有扭结,会引起很多兴奋。不过,这两个螺旋夹得很紧,必须煮沸 DNA 才能把它们分开。这也可以通过酶来完成,燃烧大量的 ATP(51-三磷酸腺苷)。这种 DNA 可以自我繁殖。粘土也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你考虑到它的分层结构,每一层都会将上一层的互补层结合在一起。DNA 也具有这种能力。
如果你把 DNA 的一个字符串做成一小段,比如20个碱基,这一小段就会对互补序列产生巨大的亲和力。你把这个20个碱基长的序列放到一个混合物中,这个混合物中有十亿个甚至万亿个(10^12)不同的片段,它将在大约 30 秒内找到与它完全互补的序列。
开尔文勋爵的几何学
Kitaigorodskii的主要贡献集中在晶体结构的几何性质,而不是它们的物理性质。他的前任之一是开尔文爵士。1904年,开尔文勋爵发表了他著名的巴尔的摩讲座,关于分子动力学和光的波动理论,最初发表于1884年。[7]本卷中的二十篇巴尔的摩讲演录由12篇相关主题的讲演录增补而成。附录H是“晶体的分子策略”,它讨论了晶体结构中分子排列的几何学。这是开尔文爵士于1893年5月16日在牛津大学青年科学俱乐部发表的罗伯特·波义耳演讲。
这篇演讲显示了开尔文勋爵的远见卓识。例如,他向未来的晶体学家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我建议你们中任何希望研究晶体学的人,与木匠或家具流苏或念珠的珠子制造商签订合同,购买一千个每个直径约半英寸的木球。在这些木球上穿孔不会有什么坏处,甚至可能会有用;但要确保这些木球彼此几乎相等,而且每个木球都尽可能接近球形"。
开尔文绘制的这两种图案的不同之处在于,一种图案中的分子都以相同的方式排列,而另一种图案中的分子行则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交替排列(图4)。每个分子的边界给开尔文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他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几何问题。在这一点上,他的后继者们引入了对分子间相互作用的考虑,而对于Kitaigorodskii来说,这最终形成了他所比喻的“给分子穿上范德瓦耳斯域的毛皮外衣”。开尔文的平面镶嵌技术领先于普拉亚和埃舍尔,但伊斯兰和摩尔人在他之前几百年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图4:开尔文勋爵的两种分子形状排列[7]。
开尔文勋爵一直在寻找一种更有效的方法,也就是在平面上更紧密的堆积,他在代表任意形状的相同分子的平面图案周围移动,最终找到了一种更有效的堆积方法。他试图使用尽可能接近直线的形状来分割平面,并且不让分子相互接触。除此之外,他还创造了平面分子堆积的现代表现形式。
尽管开尔文勋爵确实认识到了互补性在分子堆积中的重要性,但这一特性并没有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原因之一可能是他的其他作品太出名了。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只在附录中对此进行了描述。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1893 年他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时,或者 1904 年这些演讲出版时,科学界还没有为这一发现做好准备。
埃舍尔图案
乔治·波利亚(George Po1ya)[8]对 17 个二维空间群的介绍最为人熟知,因为他用完全填满表面、没有间隙或重叠的图案来说明这 17 个群。今天,我们称之为埃舍尔式图案。事实上,多丽丝·沙特施耐德(Doris Schattschneider)曾描述过波利亚和埃舍尔之间的重要联系。[9]
由于晶体结构也没有间隙或重叠,因此填充平面而没有间隙或重叠的平面图形深受晶体学家的青睐。因此,平面图形是晶体对称性教学的绝佳工具。阿塞拜疆晶体学家库杜·马梅多夫(Khudu Mamedov)的图画是将其几何图形与过去的图案联系起来的有趣例子。Mamedov 和他的同事们有意识地收集和记录他们的发现,以保护他们的文化。在这方面,他们认为晶体学大大有助于他们的人类学探索。马梅多夫和埃舍尔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用两个简单而有力的反对称图案来象征。反对称是对立面的对称,当对称操作伴随着属性逆转时就会出现。马梅多夫在阿塞拜疆巴库 15 世纪的希尔万夏宫发现了[10]一个结构徽章。这块石刻浮雕徽章上的“阿里”一词重复了六次(图 5)。六次中的三次写在石头的凹陷处,另外三次写在凹陷处之间的突起上。埃舍尔于1941年创作的《爬行动物的平面填充图案》(图 6)与这幅结构徽章有着密切的关系。胡杜·马梅多夫对 M.c. 埃舍尔的艺术非常尊敬。

图5:库菲克文字中的六个“阿里”。Shirvanshahs宫,阿塞拜疆巴库,15世纪;马梅多夫之后,1986年

图6:M.c .埃舍尔,爬行动物的平面填充主题,1941年。木刻
当然,埃舍尔的周期图是最著名的。让我引用多丽丝·沙茨施耐德对其重要性的评论
当我教授 “数学与装饰艺术 ”课程时,我看到了卡罗琳娜·麦吉拉弗里(Carolina MacGillavry)的一本书,书中有埃舍尔的设计。书中有40幅图版,大部分是黑白的,但也有几幅是彩色的。她的介绍性文章中有一个诱人的信息,埃舍尔曾做过笔记本。她是将埃舍尔引入晶体学世界的人。她在50年代末看过埃舍尔的一次展览后,去他的工作室拜访了他,了解了一些他的对称图。她在他的工作室里看到了他已经完成的大量作品。到50年代中期,他已经画了一百多幅对称画。他还向她展示了他的个人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在1938年至1941年间独自开发的理论。卡罗琳娜在序言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因此,我知道他曾写过笔记本,也知道他提出了所谓的外行理论。从那时起,我就想知道埃舍尔做了什么?他是怎么做的?
卡罗琳娜很有兴趣将埃舍尔的周期图案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向晶体学初学者传授双色和多色图案的晶体学分析。50年代末,当她去埃舍尔的工作室拜访他时,她萌生了让他在1960年剑桥(英国)国际晶体学联合会会议上举办展览的想法。他发表了演讲,演讲结束时全场起立鼓掌。会后,她萌生了用埃舍尔的图画制作一本书的想法,并得到了国际联盟的赞助。她实际上与埃舍尔共事过。她翻阅了埃舍尔所有的周期性图纸,从中挑选出那些能够说明她想要说明的特定颜色对称组的图纸。这时,她发现缺少了一个最简单的组,于是她要求埃舍尔画一幅图来说明那个组,他画了。这就是只有两种颜色的p2群。(见图 7)他还重新绘制或修改了其他一些图纸。顺便提一下,p2群在伊斯兰装饰中也并不常见,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阿尔罕布拉宫中没有这种装饰,除非考虑到某些图案的上下交织。如果您只在阿尔罕布拉宫中寻找点对称的图案,就不会看到遍布的p2图案。

图7:M·C·埃舍尔。115号对称图。这幅画是埃舍尔应卡罗琳·麦克吉拉夫里的要求为她1965年的书而画的
哈吉泰:“埃舍尔似乎也不喜欢反射对称。”
我认为这是因为他想有可识别的形状,完全可识别的轮廓。他还希望这些生物不是对称的。如果你有鸟在飞,爬行动物在蠕动,它们就不是对称的。如果你把它们排成一行并固定住,就像你用一只蝴蝶来展示它一样,这就是对称,但在自然界和行动中,这种对称消失了。他有一些反射对称的图案,它们看起来很静态;他真的很喜欢运动这个想法。在他自己的分类系统中,他不谈论反射,他只谈论滑移反射。只有当主题对称时,整体图案中的反射对称才会被引入——这就是他如何看待它的。因此,他自己的分类系统只使用旋转、平移和滑移反射。当他碰巧有一个对称的主题时,他会在分类符号上加一个小星号,表示这个也有反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只是诱导反射对称。他根本没有想到全局反射对称,只想到局部反射,当然,局部反射有时会引起全局反射。一个例子是鸟、蝙蝠、蝴蝶和蜜蜂的图案,这是当时为菲利普斯公司展览室的天花板设计的。这些形状的轮廓是从大约一平方米的木板上切割下来的,在洞上放一层薄膜,然后画上图案。天花板是背光的,有这些飞行物体的形状。相当奇妙的景象。这个天花板的某些部分是最近才从储藏室抢救出来的。
对称越少越好
推翻对称平面就等同于鼓吹不对称的优点吗?完全不是。重复也是一种对称,大自然中重复出现的图案数量相当有限,这让我们有希望了解更多。正如最常见的晶体结构一样,埃舍尔的周期图也充满了旋转对称、反转、滑移反射以及平移。然而,其中几乎没有反射。不对称就是完全没有对称。事实证明,埃舍尔的周期图就像晶体结构一样,具有“较少对称性”的特点,即对称性少于最大可能量。
我想提两个有启发性的例子来说明“对称性越少越好”的论点。当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寻找α-角蛋白结构模型时,他突破性地认识到,关键在于将非对称图案(即氨基酸)做成螺旋状排列。[121] 当他发现部分实验观察结果与他的模型不符时,他甚至置之不理。当然,他之所以能如此大胆,只是因为他积累了大量关于化学结构及其规律性的观测数据。
我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在探索生命的化学基础时,不那么完美的结构相对于更完美的结构的重要性。分子生物学奠基人之一德斯蒙德·贝纳尔(J. Desmond Bernal)写道:[13
我应该在这里说,完全和部分晶体结构之间的区别在实践中充分认识到阿斯特伯里和我自己。我拿的是结晶物质,他拿的是无定形的或杂乱的物质。起初,似乎我必须拥有最好的,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双螺旋结构的故事中,这是正确的。事实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螺旋结构的图片包含的斑点比常规三维晶体结构少得多,因此原子位置的详细信息也少得多,但它更容易粗略地解释,因此为整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线索。尽管一般的结构是众所周知的,但还没有研究出原子规模的核酸结构。可能矛盾的是,携带信息越多的方法被认为对检测真正复杂的分子越没用,但这是分析策略而不是准确性的问题。
策略上的错误可能与事实错误一样糟糕。我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信守与阿斯特伯里的君子协定,从研究无定形核酸转向研究核酸的结晶成分--核苷。
这是对20世纪最具独创性的科学家之一的思想的非凡洞察。
总而言之,用埃舍尔的周期图进行创新可能有助于我们避免研究中的错误,并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复杂性。
参考文献
[1] Much of the message of the present contribution and detail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numerous references can be found in I. Hargittai, M. Hargittai, In Our Own Image: Personal Symmetry in Discovery, Kluwer Academic/Plenum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2000.
[2] To dedicate such a contribution to the memory of Caroline MacGillavry does not need much justification. She, more than anyone else, built the bridge between M.e. Escher an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See e.H. MacGillavry, Symmetry Aspects of M.e. Escher's Periodic Drawings, A. Oosthoek's Uitgeversmaatschappij, Utrecht, 1965 (republished as Fantasy and Symmetry, Harry Abrams, New York, 1976). See also e.H. MacGillavry, "The Symmetry of M.c. Escher's 'Impossible' Images," in I. Hargittai, ed., Symmetry: Unifying Human Understanding. Pergamon Press, New York, 1986, pp. 123-138. She was, however, first of all an outstanding crystallographer, a scientist of structure. My personal encounters with Caroline MacGillavry were very enriching and memorable. I thank Henk Schenk,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Crystallography, for providing the photo of her, taken on the occasion of her farewell lec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3] Lucretius, The Nature of Things, De rerum natura, translated by EO. Copley. W.W. Norton & Co., New York, first edition, 1977. This quoted passage is from Book VI, lines 1084-1086. I am grateful to Jack D. Dunitz for calling my attention to this quotation.
[4] A.I. Kitaigorodskii, Molekulyarnie Kristalli. Nauka, Moscow, 1971. English translation Molecular Crystals and Molecules.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73.
[5] L. Pauling, M. Delbriick, "The Nature of the Intermolecular Forces Operative in Biological Processes." Science vol. 92 (1940), pp. 77-79.
[6] I. Hargittai, Candid Science II: Conversations with Famous Biomedical Scientists, Imperial College Press, London, 2002. Dr. Mullis shared the 1993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for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within DNA-based chemistry, for his invention of th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method."
[7] Kelvin, Lord, Baltimore Lectures on Molecular Dynamics and the Wave Theory of Light, Appendix H, pp. 618-619. London: e.J. Clay & Sons, 1904.
[8] G. P6lya, "Uber die Analogie der Kristallsymmetrie in der Ebene." Z. Kristall. vol. 60 (1924), pp. 278-282.
[9] D. Schattschneider, "The P6lya-Escher Connection," Mathematics Magazine, vol. 60 (1987), pp. 293-298.
[10] Kh.S. Mamedov, "Crystallographic patterns." In I. Hargittai, ed., Symmetry: Unifying Human Understanding. Pergamon Press, New York, 1986, pp. 511-529.
[II] I. Hargittai, "Transmitting M.C. Escher's Symmetries: A Conversation with Doris Schattschneider." HyperSpace (Kyoto), vol. 6, no. 3 (1997), pp. 16-28.
[12] L. Pauling, "Discovery of the Alpha Helix." The Chemical Intelligencer, vol. 2, no. I (1996), pp.32-38. This was a posthumous publication of Linus Pauling, communicated by his associates.
[13] J.D. Bernal, "The Material Theory of Life." Labour Monthly, (1968), pp. 323-326.
[14] Istvan Hargittai, Dethronement of the Symmetry Plane [1]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在下告退。
转发随意,转载请联系张大少本尊,联系方式请见公众号底部菜单栏。
扫一扫,关注微信公众号“宇宙文明带路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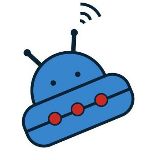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