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曹旭
前接:萌一、生二、存三、活四


鲁迅墓
滚滚而深沉的黄浦江,暗流汹涌,波涛拍岸。对面的浦东尚未开发。身着洋估大衣,枣红暗围巾,目视东方,冷光脸颊,中原紫红。手抚当年外滩堤岸那水泥墙的李非,第一次远赴上海,寻亲问路,那是橡胶厂辞职待岗时期,观看大千世界,谛视漫漫生途的照片。
幼年救命之恩的四叔已经从西安调往上海,最后见他的一面,是他从戎的一身军装,转眼已十春秋。李非按家乡提供的地址,找到长海医院的康复部,在接待室值班台处,听到喊四叔名字,以及走廊里清亮的回答声。是四叔,是他,过来如风,听着眼前的陌生人喊四叔,他愣在那里。他们没有多言,四叔掂起包,说,走,回家。推一辆自行车给李非,爷俩一前一后,往北而行。大概九点的上海朔风,吹痛了四叔的眼睛。
两室单厨的二楼,不知何名。四叔说你先洗个澡,我给你烧水。李非说,不用热水,我冷水浴习惯。狭小的卫生间,一会儿热气腾腾,赤裸上身,皮肤鲜红的李非走出来,接过四叔递来的干净衣裤,叔还是吃了一惊:“先生你就是这样洗啊”。
为不影响四叔一家三口的白天工作,早上的泡饭过后,李非一个人到南京路,黄浦江外滩,在虹口公园终于可以找到周树人先生的墓塚。伫立良久,围坟茔端详,这就是《伤逝》与《祝福》的鲁迅先生吗?民族魂的埋葬之地,是那燃烧的地火,旷原的野草,三味书屋的园子,是民族苦难的彷徨者吗?黑暗时代的呐喊人,他的匕首与投枪,他的秋夜与刑天,还有他的家人,捣烂而践踏的风筝,他的胞弟周作人,夫人许广平,民国时期的滚滚黄浦江,熙熙攘攘的徐家汇,他的济南惨案,他的方志敏,瞿秋白,宋庆龄与刘和珍?他活着什么样的一生呢?李非走着什么样的道路?李非立于墓碑前,神圣的鞠躬,整个公园没有人影,不见鸟踪,只有黑紫色的灌木,远墙上矜持的藤蔓丛。
晚饭时李非和四叔四婶说白天的行程,告知归途的时间,四叔接过他送的书,《热风》与《野草》。你怎么去墓地,虹口公园有什么看的。次日,四叔走到李非居住的房间,递返程的车票和四百元钱。李非并未推辞,只是临走时,把两元压在桌上的一本书下。另两百元和一张四叔的照片,夹在购置的新书《坟》内,一别便是无期。


陈桥驿
禹州的群山,因延宕于伏牛山及嵩山山系。若晴空百里,在塚蒙李及夏庄一带,可以隐见紫蓝色的山峦。李非被发配到夏庄村西的小学,不远处便是夏校长和夏芳的家。
几年前的初秋,李非经校长推荐,借调到乡政府计生办工作,应有更大的作为和坦荡的前途。他是大学生的缘故,很少参加到乡村里逮人、抄家、推房那类事情,只是耳闻“上吊给绳儿,吃药给瓶儿。”只要不超生的土政策。他主要的工作是写新闻、审表册、整理资料,每逢加班干活,会到深夜,大家都愿意和他搭班。这年初冬,他代表区市到禹州检查工作,到了很多乡镇,最后不知何镇,一个叫陈桥的山村,终于看不惯村民的卑微和村干部的献媚,那家家超生,通过表格造假,各级红包通融,瞒混过关。
整个检查结束,那一晚庆祝,李非醉着吃完大宴中的五粮液,又在宾馆外的散酒摊买醉,而且不顾同事人员和组长的劝阻,在深夜步行有半个小时,截一辆货车,回到了许县。此违纪行为,引起了市里领导的震怒,由乡政府大会当场处理,发到最边远的小学去。李非听到训诫和处理结果,似曾相识,原来是初中时那位女语文教师宣布考试不及格的瞬间,竟还是我。
夏校长也去求情,说不行还回到我们中学,如若不行,那就回我们夏庄小学吧。后来,那个大会上声嘶力竭的乡领导死了,俗称“爬烟囱。”八月怀胎的外地孕妇,被乡政府逮住也要打掉孩子的事情,还会少吗?李非在近五十岁时开悟:“谁得罪我,就没有好下场;违天理,反天志”。
李非在夏庄小学有两年半时间,正好读书。新婚夫妇,还在城里居住,夏芳早年母亲已经过世,老家无亲。油菜花开的季节,夏芳会在花地的桥头接他,满路的花香;暑假两人相依,李非剃光头,坐凉水盆中读书;冬天寒变,李非顶着朔风,踏着雪泥,橡胶厂家属院的楼洞里,夏芳早已等候,互怜不语。
到了春节,李非一个人的工资,先列下过年的清单,新衣新鞋,新鲜肉五斤,甚至烈酒两瓶,都要一笔笔的算好。平静读书的两年半,除了四叔寄来的婚礼的邀请,以及胞弟寄来的小册子,李非也曾参加县公检法的公开招聘。一辆警车那么老远过来,惊动整个夏庄,通知他笔试第九名,参加面试。结果面试加笔试,以一名之差落聘。后来李非对西城说,那年未去公检法,不一定是遗憾,也许是牢狱之灾。他微笑的嘴角轻轻扬起。
玄武门陈桥驿的故事,夏老师讲过。每每复读知新:塞翁马浅井蛙的寓言,铭刻记而践思。那浑然不知人事的暑假结束,重返夏庄小学,当年的灵井槽已坍塌,只有残垣还立于村口,如门如祭。有同事见他,惊讶道:“你怎么还来,没接到通知吗?你回郊七中学报到。昨天乡教办已经宣布了。”而次年的夏末,原来的校长被打,对前来看望的李非说:“我只能调走了,宫廷政变啊”。


左眼跳
李非当校长的消息,半年之内传播了左右纵横和上下,二十七岁当校长超乎自己的想象。他子时眼跳,没有意外之喜吗?好运连连,人生不知的运道,传说子时还好,丑时跳起,家中很麻烦,和夏芳的婚事,已有好几年的时间。然而李非的父亲来了,他听谁谁所言,推着车从简陋的校门过来,没有军装了,穿什么忘了,他的儿子副校长主持工作。
跳鲍老是杂技的一种,宫廷事变是单位的两派相互不让,乡政府新的教育领导过来说,就你们那事儿多,那好吧,民主选举。民主推选,两派皆输,李非竟然当选副校长,谁会相信。当夏芳沐浴着秋月的银辉,带来被子的门口,李非还说难听的话,夏芳在其后的日子里祈祷一般:我就没有看错人。然而,左眼跳在子时是好运,丑时则麻烦。那个父亲因为当年遗弃的儿子跳龙门,前来打扰,李非淡然会见
不管左眼桃树,还是右眼桐花之落,实则不是神话和凤凰年代,不过就是用眼过度脑神经神经过度兴奋而已。同学们也过来,李非结婚后去贺鹏家,照例给曹师傅及几位老人拜年。知道贺鹏不在,家里的娘说:“斐斐呀,他不在了啊!”良久之际,李非说不要相信,如果他真的没有,我养老送终,娘你放心吧。当年的老贺叔贺副厂长脑溢血,早几年过世,那临近春节的冬风里。
几乎不是一天,做此多事,李非迎着西城说,唉,阴差阳错呀,好像女人的仙人跳啊。是主管教育的,也只是三十多岁的女乡长,肯定这一办法,竟然因两票之差“中黑了”呀!什么校长了。干就干吧,你老班长不也是领导吗?付西城连连摆手,说我们到现在才知道雅斯贝尔斯的话。另一个同学接过来说:“逃避自由。还有谁说呢?”那声音很粘稠的流淌在地上说:“弗罗姆《爱的艺术》”。
第二年主持工作的李非,因学校合并,市郊四中的老校长资历老,来任一把手,美丽的副乡长劝导李非:“他是老同志,干两年就退休了,你忍一忍。被李非拉上来的两个主任也说:你不要看那些跳梁小丑,你要辞职,在不在这个位置上是不一样的。两个大姐也劝,然而,其中一个,儿子正读研究生,谈恋爱失恋,跳武汉长江,漂到安徽,学生证发现:另一个调往河北,蒙月兰生李非的地方。
这是什么样的世道与活法呢?李非的那个大姐,灌木丛中的劝告:“你还要像往年一样对待他们。”旁边远处的梧桐并不相干,只是说:“冯姐,英雄气短,那些知道我当校长的,不远五里,会早晨骑自行车过来,带我上班;那些职前职后的嘴脸,我看到了,随他们去吧。”是的,冯姐哪里会料到,高贵的呵护的优秀的儿子,会漂到安徽江滩上的命运。何止是梧桐的叶殇呢?那一晚,李非和父亲的右眼开始跳动不停,在子时,又丑时,那个曾是父亲的男人李贵生。


西城鬼
付西城已是自来水公司的副总了,打电话过来,李非已经知道西城有了女儿,你啊你过来,就是几个同学。他不提孩子,李非夏芳一直生不出孩子,只听见年级同学的嘶叫声。婚姻已定,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的。夏芳计较,李非无所谓,有时候看陶渊明吧,没有苏轼的那种豁达。夏芳则有变化。
人民路,对,就是当年李非上学的那个地方,李非说,你将来上班,要进修,延安路学校在升级,没有一定的学历不合适。夏芳用三年半的自学考试,也是河大专科毕业。那次考试,李非恋恋不舍得看着她一袭红裙登上车,一月的绘画专业培训,那是什么样的夏晨笙歌。过了这个季节,已经与妻商量也好:干啥校长,我调往其他学校。
离婚的女乡长与李非饮酒说,学校合并是正常的。你太倔了,老本科生几年就退休了,能主持学校合并的夏庄中学吗?李非说,我本就不愿意做什么校长,你要帮我就调走我吧,就调到夏庄吧。那本科的老大学生,那老校长不久退休了,不久也死了,一生做了些什么呢?
骑单车接李非上班的那个会计曾说,告诉你可以防着出纳;后又给调来的老本科生说,李校长吃喝嫖赌什么不干?但真的也不是意外,他在酒醉之后就在公路被车轧死了,是头天的傍晚,次日公交车才看到做鬼碾压。盯着他已扁的被子几乎不能掩盖的尸体,仿佛还能听到这会计在风中大声说:李校长你可要防着出纳啊,有的账不要经她手,她阴毒着呢。
给付西城说这么多的时候,李非饮着酒笑了:“啊城,这就是一个乱啊,这个死鬼,也还是我和夏芳当年见面的撮合人,是夏老师的另一个学生了,比咱大点儿。”付西城说,那他是你的大媒人,人死为大,说他干嘛?你喝酒吧!
那天李非喝醉了,他调走后的学校,丑若男子的出纳任校长,李非又调来更大的合并校,夏庄中学。不料,两年之后,那女丑又追回过来任校长。李非嫉妒而自嘲:“我的出纳当我校长,岂不快哉”。
李非在夏庄中学工作了五年,那野路上的碎花,兰兰如星,散落在天涯,想到母亲,不看月亮,在暑假前要到六一儿童节,依然可以俯首给孩子们写庆祝贺词,校长曾经是我的出纳我的兵又如何?能大能小一条路。他自言自语,在灵井槽的那段田野里,一段沟渠坍塌而坠下不去,是个斜面,当然已无泊泊的泉水,灵井已无水,传说有大型的煤矿在地下,就是那座七层佛塔的周围。
背倚伏牛山,东望京广线,南面收割完毕的浅黄色麦田里,只有谁家的望族之位,铲不平的孤坟,与那七层高塔,夜星昼晨相望,没有料到,军校毕业调来调去至北京的胞弟,一个短信,借调李非到教育局,后又办手续,按李非自择在进修学校,西城与众人,莫不惊诧。


白玉兰
一晃有多少年啊?李非不饮酒,少朋友来往,电话号也已关掉,慢慢地来,取之不尽的报纸、书本和来人。股长从外面过来说,今天周末,你还不下班。李非忘了时间,记本天的日记,说,哦,走走。有些阶段你不走,你工作也是错了,因为那个副股长,还是借调李非“普及九年教育”为名而到局里的,那个潘安长相,孔明身高的副股长私下里到处说:“他另立股室了,不在我们的招生办了,他拉住局长的大衣裳襟了。”不过李非真的不竞聘什么办公室和招生办什么主任职位。头一天的晚上,股长说你已经内定,给你的副主任,他去办公室正职。李非看着夜色的城市灯光,手里一本李佩甫老师的《城的灯》,直说谢谢。谢谢你和局长。
但是,第二天,宛若无夜市霓虹的清清早晨,西湖公园的水杯波澜不惊,只是微纹洋洋,也不再高高下下的乱。有什么呢?无所谓,你二十七岁当校长,多少的夏酷冬烈呢?怎么他会当校长?仿佛违背了天志。在考评他的时候,以女人为首为伍的,尤其是那个没有娶她妹妹的,还是夏芳的亲戚,在书桌前,办公室内,只是简单地撩拨,引起共趣,没有顾及案头的《鲁迅文集》。所以今天的招聘会取消了,李非也有新任命,跟着局长在心理辅导中心的一层创文办工作了。那时节,胞弟已安排他到进修学校了,正式的调动手续和工资已定,只还是在教育局帮助工作。这地方也真适合读书、打拳、写字,有两个房间,整一层楼,除了大型活动,几乎无人。李非看着窗外的白玉兰树,心想是谁当年栽种的?不是一棵,是三棵,不是鲁迅先生的有一棵枣树,还有一棵枣树的典故。是越过了三层楼高的白玉兰,应该是乔木了,不是花树,哪里幼小时期的槐树与结婚的梧桐花呢?
白玉兰,李非真的过去查一查,三棵是一九八四年该地域的第一任领导所种植,那是一种什么情怀的青春和壮年?几十年过后,可惜他不在了,少有人知道他的栽种与培育,他的人生道路汇集了共和国几代人的艰辛,与日复一日岁又一年的默默浇灌。不知道为什么,李非在写字的时候,想到这些,看着春天的凋零,竟落下泪,因为那白玉兰的大片大片的花瓣,在昨夜的一场春雨之中,乱了一地的悲切。那就喝酒吧,有必要戒吗。


惶然录
醉后的清晨,夏芳推醀李非:斐斐,斐斐。芳菲之泪落在床榻。他们早已经分居,夏芳有了其他的男人,那是二零零六年的五月,他在上海的街头,他说:“那不倒的旗帜,我很难向上攀登,我一个人向上,用我的手、月光和汗水,甚至可以用说,不是山不够高,那是另外的山峰。难道是优雅的裸体?他还要说,我不会成为事物,我只是一个虚幻,靠这种距离,将世上所有的梦幻聚在我的身上”。
佩索阿写道:“在山谷,篝火闪着光,舞蹈震撼了大地。”我怎么敢再写下去,买第一房子的时候,四叔说你需要多少,李非说我看中延安路旁边的四通小区,四万就行,我回头还会还给你。四叔对会计说,把银行号码记清。李非收到的时候是七万元,没说借,是给七万。李非也只用了五万,那剩下的,装修吧。
李非到教育局的几年之后,在幽暗的办公室里看书,收到妻子的来电,接通后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李非不怒,只问你是谁?对方答曰,我是你爹。李非几乎骂说你是谁?然后听清是四叔。那女人竟然跑到了上海他四叔的那里,回来说去了外滩和不知道的地方,四娘当天晚上陪着睡觉,不敢让夏芳一个人。但是谁知道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吗?一直到死都不知道什么事情。
没有多久的那个清晨,那个最后的清晨,夏芳推醒他:“斐斐,斐斐,四叔不在了,四叔不在了。”芳菲之泪落在床榻,那是什么样的回味应答呢?李非奔丧去上海,在钉棺材的时候,那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给胞弟说:给,锤子。胞弟按照他的要求,飞机跑来,那又是什么样的五角场,何等级别的外滩呢?
那一本《恍然录》,只有上海南京路的那家书店,有那五千册的印痕。李非也只有那个清晨的九点,面对他的葡萄牙,如果可以,他会拥抱着四叔说,我不希望你会做不雅之事,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不能让我坍塌。“他已经撬开大帝之门,其实他已经死了。”不能说谁消失在地平线,上那浦江的彼岸的水啊。
好吧,和桑特与尼采一般,位卑之趣,蜗居之室,竟一人承担了全人类的精神责任,始终贯彻了独立的果敢和勇毅,即那夏天的堤波江,水还可以芳菲吗?她为什么会死呢?当四叔的盖棺之锤,李非一下下钉死的泪水,怎么知道的夏季冬天,那绯红的纯洁呢?四叔,你还好吗?你没有做错什么吧?
远在万里之遥的葡萄牙,在百年之前的佩索阿,在南京路上的书店,是一九九八年四月的韩少功介绍于李非,他清晰地记着费尔南多 佩索阿的《惶然录》,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但是有谁还记得外滩的踩踏事件呢?难道是另外的上海?还有他的恩人四叔吗?还是可以抱紧他,他的恩施与愧疚?但浪平又浪涌,李非在《去教堂》的那篇短文的尾部题注:今天是开心的日子,写作在手心的阳光下飘荡,他总那么爱《惶然录》,像史铁生老师的《病隙笔记》,那美丽地攀谈,生活在冥界的思想者。


右眼跳
多少年后,给夏芳买车,大众发车之际,已经拿住车照,她还要去练车,约好四点出门,是个秋天。李非说你去吧,夏芳收拾好,黑色的短裙和小靴子。到了天晚,已经苍黑,夏芳还没有回来。李非打电话,第一个没有接,又打过去,李非听到男人穿鞋走动的声音,李非说你快回来吧,夏芳说准备回去东街吃饭呢,李非说你别去,你回来吧。
只她基本刚才的要求按时回来,李非说我既往不咎,不该有的电话,不该去的地方,你不要去,然而后来又考虑,她有事,那男人正和他接吻呢,耳朵小的好看的女人,怎么会抵抗花言巧语呢?那男的说你的车真的半路上没油,我拖车帮你。夏芳给李非说这些的时候,她说没有其他,宁死不认。非宁死,鸵鸟而已,谁骗谁呢,我电话都听不出来?
那一个她也不承认,只说我去和姐商量了一块泉店,商量着能不能办一个幼儿园,后来这个事她说没有。还是有两天,要到她的姐姐那里,李非已经睡觉了,你就去吧。但她去了哪里?更早一些,在烟城幼儿园,李非在窗口看到她向东,而不是单位的方向。晚上城西一块饮酒,李非打电话,打到那个院长,院长说,我们下午休息并没上班,然后她被辞退。还是当年的紫色黄色之前的粉红头饰的?有时候李非给城西说,曹雪芹老师说的好,女人到四十岁,就是妖婆,曹老师红楼的美好女人,美好女孩悉为十五岁。
找另一个幼儿园工作,夏芳提前一天说,周六日两天要去郑州培训。李非醉着,说你去吧。晨六点醉醒,去她的房间,方觉是前天的谎言,越想越不对,印象不对,她妈的,我教育局的,怎么会有六点抹黑去参加培训呢?你发个照片过来。发了,还是和同事一块儿。这次没有两天,早早回来了,李非到她的床上,她听到李非明天招呼会打电话给院里落实。只好补充说,那我实话实说吧,是家里面的大姐孩子结婚,李非转身说好:“啊,西游记了”。
这样闹腾的几年里,夏芳最后的一别,是五一路南边,水泥厂倒闭了,原土地开放为住宅小区,一侧的那条铁路边上。夏芳车没开,也没有人送,骑着小电车到那里,一辆卡车过来碰了一下,没事,却又倒撵了一下。那旁边的,有梧桐的树都看到了,那是个傍晚,没有摄像城里的卡车不多,没有找到那个司机。她寡女,看着曾经相爱的人儿,几多思绪。但是李非无泪,殡仪馆火葬场而已。后来李非和一个女人睡了,那女人怀孕,李非方知不是自己看病多次,是那粉红头饰的芳菲无生育能力。
没看什么样的花呢?是鲁迅先生说,你会死,但真话不能说啊。彼此看看结束吧,李非俯卧一榻,在夏日的上午,默在笔记中写道:“竹席月影美酒在,乡关笛声是她人;没到织女天行晚,已是牛郎笑黄昏。”伤哉。

(未完待续)
☆ 作者简介:曹旭,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教师进修学校干部,笔名陈草旭变,近年来有数百篇散文、小说见散文在线、红袖添香、古榕树下、凯迪社区等文学网站,合著有人物传记《那年的烛光》。
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编辑:易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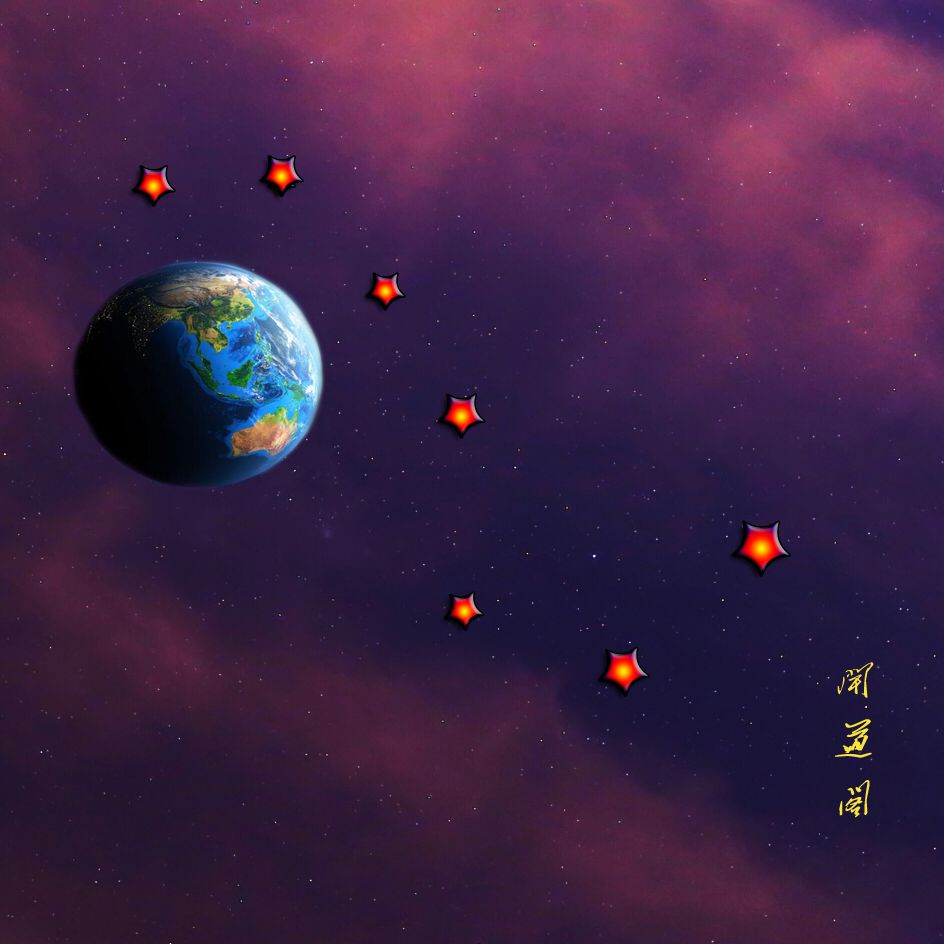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