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在艺术学校上学时,学的是舞蹈。我长的高挑个儿,皮肤白皙,全身曲线动人,都说我毕业后会成为美人鱼。谁知毕业了,没有任何艺术团体招聘学生,我只好给一家酒吧当“领舞”。偶尔有大型歌唱会演出,我才去站在男女歌星胸前背后伴伴舞,得到一些外快。
何处是归宿?我很焦急。

后来,在饭桌上认识了一名日本老商人,他对我很殷勤,送我手表、翠镯、白玉坠,无非想要跟我近乎近乎。我跟这个日本老头儿不近也不远。但他每次到这个城市接洽商务,都找到我。他说,他不但喜欢我,还说每次由我陪他谈判,生意都做得很圆满很顺利。因此,他常常几十万几十万日元的送给我。
起初,我不敢要,他说:“这是提成,‘小小的’,不像样子。”
我心里想,像样子,是什么样?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吧!
这年元旦前,我陪他又谈成一笔生意。说是陪,其实很简单,既不需要我懂得生意经,也不用我张嘴说话,只是在他请客时向客人敬上一小杯“路易十三”,就行了。谁知这位中国老板高兴极了,喝了一杯,又要一杯。最后客人让随从打皮包里掏出一瓶精品名酒,向老日本一杯一杯敬起酒来,没完没了。老日本几杯下肚,先是脸红,又是摇头晃脑,慢慢舌头也哑了。老日本把锋芒转向我,客气地请我代饮。
这种场合,我是不能让宾主下不来台的,就也喝了几杯。我的脸烧得像晚霞,晕头转向。散席送走客人后,老日本把我架到16楼他的房间里。他给我要来一杯茉莉花茶,那香气真诱人,我大口地饮进肚中。谁知酒未解,人更晕了,竟在沙发上睡着了。

在睡梦中,我觉得身上一凉,睁眼一看,老日本正在脱我的衣服。我火了,给老日本一个耳光。谁知这个老头儿竟跪在我的脚下。他说,跟我去日本吧!他现在没儿没女,孤身一人,日本、韩国、菲律宾,有好几家公司,就是外头没有亲信,家里没有主妇。
当时我眼珠一转,平日听同学说,这样的人是“老绝户”,可以嫁过去。他死了,就可继承他的全部家产。而且我又想马上脱身,就答应他:“你如果办好我去日本的全部手续,我就嫁给你。”
他一口答应。
我也显得很诚实,第一次帮他脱衣服,换睡衣后躺在床上,我就回家了。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再理他。
一天,他兴冲冲地跑来找我,手里拿着护照,签证都办完了。我虽然有点傻眼,但是,寻思了一夜,第二天还是同他办了“涉外婚姻”登记。当晚,他请我姑妈(我没有父母,姑妈抚育我长大)在百乐门大酒店吃晚餐。
60岁的人了,直冲我50多岁的姑妈喊“妈妈”,老头儿真有心计,送给我姑妈一份购房合同和一个带着精致匙链的钥匙。日本老头儿给我姑妈买了一套跃层公寓房,200多平米呀!
在中国,我不让老日本碰我一下。我坚持到他故乡神户的教堂举行婚礼后才能合房。我的老头儿很高兴,直冲我鞠躬。

在樱花烂漫的三岛,我度过了平生最舒服最闲散的日子。因为一年后,作为22岁的妈妈,我给老头生了一个儿子,就像洋娃娃一样的儿子。他的同事和朋友来祝贺,都说我是日本当代最漂亮的女性。因为日本的时尚是,女人长得越像西洋女人越好。我正有这样一个胚子。当我穿着红色西装,灰法兰绒裙子,推着豪华童车(那种法国进口的高轮、手工织呢篷的童车),在我一人(我不愿同老头儿逛街遛公园)推着我的“洋娃娃”漫步在神户海边的石板路上,我很高兴。因为日本女人都向我频频点头,投来羡慕的目光。
我的婚姻很不理想,但我要营造自己的浪漫。
我如愿了。谁知,阪神大地震,砸死了我的洋娃娃,我的生命失去了一半。刚过两年,金融大风暴又让老头儿破了产。他曾想自杀,是我救了他。我去当佣工,当家庭保姆,好让老头儿能吃上一口饭。有时候,他看着我,两眼充溢着泪花……我在想,我生命的另一半,也失去了。
我恐慌的,是谁来养活我的姑妈?
我只好一个人,又回到我的出发点,生我养我的地方。
我的日本老头儿来过几封信,但没有一分钱寄来。我和姑妈相依为命,我们靠给印刷厂用手工订线装书赚几个小钱。不久,姑妈也死了。我卖掉房子,换住一间小黑屋儿。这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林中失群的小鸟,四周的天色又黑暗了下来……
我把仅余的几件家具送给了邻居,开始四处漂泊。我夏天到哈尔滨,冬天到海口、三亚;最后,我到了闽南,在酒店里坐台。

我并非残花败柳,也不像那些蓄着长发的小姐。只要有一点钱,我就会把自己打扮成富贵的少妇,像充满春天浆液的柳枝,迎风招展。
我为了强化自己的形象魅力,我在脑后梳了小盘头,穿上旗袍。我不让人们称我为小姐,自己定位:山口夫人。
不出所料,那些几年前靠走私发家,不会穿西装而硬扎领带的渔民,还真像苍蝇一样盯上了我。我却抱定宗旨,敬酒不吃罚酒更不吃,软硬都不怕,送钱的放下,找便宜的,没门。但总得赚钱呀!我创了一个新招儿:陪宴。得吃得喝,每餐2000元,童叟无欺,言无二价,宰你没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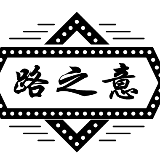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