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4年6月,本文作者的生父、纳粹党卫军军官格哈德·巴斯特因斗殴而留下了永久性疤痕。© 马丁·波拉克
利维坦按:
十分理解作者为什么到50多岁之后才开始面对这段充满耻辱的黑暗往事,毕竟,这段历史涉及到的都是血亲。或许也正因如此,给自己一个良心上的交代也是必然的选择。身为纳粹的后代,作者的反思不可谓不彻底,但这也是他对于历史乃至当下欧洲最为忧虑的一点:即,那些纳粹的意识形态从未远离过欧洲。文中提及的“大取代”阴谋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如果展开论述近十年为何“大取代”阴谋论甚嚣尘上,又必须结合欧洲移民政策等诸多因素来分析,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
我的家人都是纳粹分子。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我的继父、我的叔叔——几乎他们所有人都是二战期间的铁杆纳粹分子。战后呢?没有一个人改变他们的信念,也没有一个人对纳粹罪行表示过任何遗憾。
相反,他们要么否认这些罪行,要么为其辩护,包括对谋杀和大规模屠杀的辩护,最糟糕的是,有时他们还积极参与其中。我们家也不例外——在奥地利和德国,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
战后的官方说法是,奥地利是希特勒扩张主义政策的第一个受害者。四个战胜国——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明确认可了这一解释,一些人认为,这一解释让奥地利和奥地利人民摆脱了参与纳粹暴行的罪责。
但并非所有奥地利人都接受这个说法。奥地利社会的大部分人仍然对国家社会主义抱有强烈的认同感,这是一种激进的大德意志意识形态,它拒绝承认奥地利是一个拥有自己历史和文化的独立国家,并培养了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和反斯拉夫情绪。
我的家人和许多其他人一样,直到去世都坚信希特勒和第三帝国。“我们不是奥地利人,而是德国人,”这是我小时候经常被灌输的信条。“我们将永远为此感到自豪。”
我出生于1944年,也就是战争结束前一年。当我10岁时,我被送到一所寄宿学校,远离我和母亲及继父居住的林茨(Linz),也远离我经常拜访的住在阿姆施泰滕(Amstetten)的纳粹祖父母。为什么我的亲戚要把我送走,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也许他们被学校位于高山之巅、周围环绕着树林这一点吸引,因为那远离了城市的腐化影响,远离了犹太人和反德精神——正如我的祖母所说。此外,学校里我们还必须学习一门手艺——我成了一名木匠。
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所学校的精神非常自由。在那里,没有一个老师是老纳粹分子,这在50年代的奥地利是一个例外。因为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学校里,我与纳粹亲戚的影响隔绝了,很快我开始对他们的信念、他们的大德意志思想、他们的反犹主义以及对奥地利和民主的憎恨产生怀疑。在学校里,我们学到了其他的信念。

1944年7月,格哈德·巴斯特(本文作者马丁·波拉克的父亲,纳粹党卫军军官,左一)与父母在阿姆施泰滕。© 马丁·波拉克
我的母亲大约在1930年与汉斯·波拉克(Hans Pollack)结婚,他比她大20岁。我从未被告知他并非我的亲生父亲,但我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经常被送到阿姆施泰滕和祖父母一起住,他们以“我是真正属于他们的孩子,格哈德(Gerhard)的儿子”的身份热情欢迎我。而我的哥哥和姐姐,他们比我年长,却从未去过阿姆施泰滕,甚至不知道我在那里的祖父母。对于年幼的我来说,这种局面既奇怪又令人困惑,但我只能接受了。
我记得母亲第一次告诉我,我真正的父亲名叫格哈德·巴斯特(Gerhard Bast),他是党卫军的一名军官,也是盖世太保的一位高级成员。当时我14岁,足以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她没有告诉我他在战争期间做过什么——也许她自己也不清楚,至少不知道全部细节。他在1947年去世,那时我才三岁。得知这一切后,我感到震惊迷茫,完全不知所措。我也没有人可以倾诉我的感受,即使是学校里的同学——他们同情我,却并不真正理解我的处境。所以,我不得不独自面对这个可怕的消息。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我总算勉强过上了可以称之为“正常”的生活。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已与家人断绝了所有联系,正在维也纳求学。
某一天,我的叔叔突然联系我,说我的祖母快要去世了。他让我去阿姆施泰滕——那是维也纳以西一小时半火车车程的地方。我匆忙赶去见祖母最后一面。她曾是世上最好的祖母,对我宠爱有加。然而,她也是一个固执而强硬的女人,并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我去得太晚了。叔叔在门口迎接我时,说的第一句话是:“她像一个德国女人一样死去。”
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个家族丝毫没有改变,也永远不会改变。
要解释我的家族为何与纳粹主义有如此强的联系并不容易。无疑,他们的背景和社会化过程起了重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奥匈帝国时代,他们住在所谓的“下施蒂利亚”(Untersteiermark),即如今的斯洛文尼亚地区。像我的曾祖父这样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对哈布斯堡家族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认为哈布斯堡家族是斯拉夫人的朋友,而他们鄙视斯拉夫人。

19世纪后期,德国人与斯拉夫族裔之间的敌意和冲突时常发生。我的祖父和他的两个兄弟被送往格拉茨(Graz)求学。他们在家里已经吸收了激进的德国民族主义,在格拉茨加入了一个名为“日耳曼尼亚”(Germania)的德国学生兄弟会(Deutsche Burschenschaft),这个组织以强烈的反犹主义和反斯拉夫主义而著称。
学生兄弟会是暴力德国民族主义的摇篮,充满了如今被称为“有毒的男子气概”。他们的成员酗酒、斗殴,以及在希特勒1938年吞并奥地利后,对奥地利大学中的犹太教授和社会主义教授进行残忍、甚至致命的攻击。格拉茨被视为抵御斯拉夫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假想入侵的堡垒。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带来的影响,加深了我的家族对德国人将被斯拉夫人“劣等种族”淹没的恐惧。他们认为,这些斯拉夫人正计划剥夺辛勤工作的德国人的权利和地位。如今,欧洲各地的右翼政治家对移民提出的指控与当年的说辞如出一辙。“大取代”(The Great Replacement)这样的阴谋论让我想起了童年时听到的言论。我的家人灌输给我一种观念:我们才是受害者,犹太人和斯拉夫人都在觊觎我们。
如今,这种加害者与受害者角色的颠倒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其追随者不断声称,他们从未计划对乌克兰发起侵略,而是一直在防御那些包围他们的敌人:一个试图摧毁和平的俄罗斯、以实现希特勒原本目标的西方联盟。这就是为什么普京不断抨击虚构的“统治乌克兰的纳粹”。普京的叙述已被欧洲各地的极右翼势力越来越多地采纳,尤其是在我的祖国奥地利的自由党(FPO,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于1956年4月7日在维也纳成立。编者注)。 今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自由党赢得了最多的选票。
战争结束近80年后,为什么国家社会主义的强烈回声仍然如此吸引人?为什么生活在和平时代、享受民主各种好处的人,竟计划颠覆和破坏这一制度,同时试图复兴过去的意识形态和手段?仇恨言论、排外主义、种族主义、“主宰种族”的优越思想,以及对强权人物的崇拜——一个用铁腕统治的“元首”——正在卷土重来,仿佛纳粹主义从未发生过。这种现象不仅困扰着德国和奥地利,还影响了其他国家,包括那些拥有深厚民主传统的国家。
这是某种集体失忆的表现吗?作为纳粹的后代,我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负有责任?我们是否太过自满,认为民主制度不需要我们积极捍卫就能存续?有时我会想,我的家人或许会成为普京及其同类的崇拜者。他们深信,民主是毒药,只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才能拯救我们。
1918年,奥地利失去了作为一个拥有超过5000万人口的庞大帝国的地位,变成了一个人口不足700万的弱小、战败且极不稳定的国家。许多德语使用者发现自己成了新成立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中的少数民族,由他们所憎恶的斯拉夫人掌权。与斯洛文尼亚邻居的冲突、日益增长的排外情绪,以及对日耳曼民族优越性的信念,这些构成了我家族男性成员成长的环境。

1942年,作者的母亲希尔达(Hilda)和父亲格哈德在斯洛文尼亚南部的科切维(Kočevje)。© 马丁·波拉克
继祖父之后,我的父亲也在格拉茨(Graz)学习,并像他一样加入了日耳曼尼亚兄弟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兄弟会变得更加激进。1931年,我父亲20岁时加入了纳粹党,同时加入了党卫队。当时,党卫队还是一个小规模的组织,由随时准备与政治对手(如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或警察)作斗争的暴徒组成。在兄弟会的酗酒与斗殴文化的推动下,我的父亲结识了一批新朋友,其中包括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Ernst Kaltenbrunner),后来成为帝国安全总局(RSHA)负责人、纳粹大屠杀的主要实施者之一。
1938年,德军入侵奥地利并将其并入德国第三帝国,这一事件被称为“德奥合并”(Anschluss)。之后,我的父亲在格拉茨的盖世太保获得了一份工作。他似乎是理想的人选——在希特勒掌权之前,他已是一名坚定的纳粹分子。他因从事反奥地利活动而入狱过,就像我的祖父一样,这对盖世太保、党卫队及其情报机构安全局(SD)的职业发展来说,是极好的推荐信。从格拉茨开始,他被派往德国的不同城市。1941年1月,他被派往林茨,并成为当地盖世太保的代理负责人。

吞并奥地利后,阿道夫·希特勒在前往维也纳的途中受到了部分民众的热烈欢迎。© Heinrich Hoffman / Ullstein / Getty
林茨并非普通的奥地利城市。希特勒年轻时曾在那里生活过几年,对这个地方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林茨上过学,尽管并无显著成就。他的一名同学,后来成为了我的继父汉斯·波拉克。波拉克记得希特勒的一件往事:有一次学校组织郊游,经过一片长满干草的草地时,希特勒点燃了草,然后爬上一棵树,对同学们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但同学们并未被打动,反而认为他疯了。
作为盖世太保的负责人,我的父亲肩负着许多职责,包括执行针对强迫劳工、所谓的帝国敌人以及犹太人的纳粹法律。任何案件似乎都无法逃过他的关注。一位朋友、历史学家曾发现一个关于老人的悲惨故事:这位名叫马克斯·戈尔格(Max Gorge)的老人住在斯泰尔(Steyr)附近村庄,是村里唯一的犹太人,他1868年出生于波西米亚,后移居奥地利,成为一名亚麻织工,退休后住在加夫伦茨(Gaflenz)镇。他很贫穷,几乎难以维持生计。然而,他并未逃过纳粹的注意。在相关档案中,我的朋友找到了一封由我父亲签署的信,要求当局登记并报告所有犹太人,无一例外。戈尔格在1942年初被送往维也纳,随后被送往死亡集中营。但在此之前,他因忘记在证件中加上“以色列”而被判入狱两周。
没有我父亲的介入,戈尔格是否会幸存?我对此表示怀疑,但这并不是重点。我父亲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签署了他的死刑判决。或许有人会问,深入探讨这样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案例是否真的有意义。难道没有无数大规模屠杀的案例,成千上万人在集中营或东欧的屠杀场中被杀害吗?确实,我父亲也亲手参与了大规模屠杀。但我仍然认为像戈尔格这样的个案很重要,因为它为后来的罪行奠定了基础并营造了氛围。
没有人强迫我的父亲加入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他是自愿加入的,完全清楚他将被要求做些什么。他本可以选择另一条路,比如成为一名律师,就像他的父亲和叔叔——他们也参与了犯罪,但程度远不及他。
那么,为什么呢?我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但从未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他不是怪物或虐待狂,而是别人眼中的一个好朋友,登山和狩猎的伙伴,我母亲深爱的丈夫。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1914年,3岁的格哈德·巴斯特拿着他的第一把“真正的”枪,一把小口径步枪。© 马丁·波拉克
当然,他深度参与纳粹政权的暴行部分是由于他的成长环境,但这并不能减轻他的罪责。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学习过法律,懂得区分是非。有道德顾虑的人绝不可能升任林茨盖世太保负责人这样的职位。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43年11月,我父亲的秘密警察生涯突然结束。作为盖世太保负责人,他被邀请在靠近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地方参加一次狩猎活动。在狩猎过程中,他意外射杀了一名赶猎者,一个男孩。或许有人会认为,作为高级盖世太保和党卫队军官,他可能只会受到一顿斥责。但在这些问题上,纳粹非常严格。他被判处四个月监禁。
虽然他不必服刑,但被派往前线,领导一个特遣队(Sonderkommando),负责清理战线后的犹太人、游击队员和其他所谓的帝国敌人。这是一支死亡小队。
那次狩猎事故标志着他人生的重大转折。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所谓的“案头罪犯”。从那以后,他成了直接的施害者。

我花了许多年才开始研究我父亲的生平。 我必须等到母亲去世之后——在她还活着的时候,这个过程会太过痛苦和尴尬。 然而,即便在1978年母亲去世后,我仍推迟了这项研究。 我告诉自己,现在不是时候,我有太多工作要忙(这当然是典型的借口)。 我直到50多岁时才认真开始搜索往事,因为我觉得自己不能再拖延了。
我首先向柏林联邦档案馆申请了他在党卫队的档案。 在研究过程中,我得知父亲于1944年7月在波兰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k)附近与他的特遣队会合。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不愉快的发现。 我之前并不知道他曾在波兰服役,而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有着深厚的感情。 我曾在华沙学习波兰文学,至今仍视波兰为我的第二故乡。我第一次去波兰是在我父亲被派往那里的20年后,但两者的目的却截然不同。
在比亚韦斯托克,特遣队7a(Sonderkommando 7a),也被称为“巴斯特特遣队”(Sonderkommando Bast,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将一群年迈的波兰人作为人质,随后将他们押送到华沙。1944年夏天,他们在华沙城外扎营,当时华沙起义正如火如荼,市民奋起抗争,试图将城市从纳粹占领中解放出来。

被迫为1005特遣队工作的犹太幸存者站在亚诺夫斯卡(Janowska)集中营一台碎骨机前。照片拍摄于集中营解放后。© wikipedia
当我开始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了一些文献,揭示了我父亲的角色。他和他的部下穿着便衣、全副武装,进入城市执行“清理”任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杀死他们遇到的任何人——无论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起义者,还是其他人,不分男女。他毫不留情。
他只是盲目地执行命令吗?这只是部分事实。作为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他几乎是自己的上司。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普通人会如此轻易地变成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所描述的“平凡的杀人者”?他们变得冷酷无情,坚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坚信自己在为正义事业效力。历史记录表明,当国家为针对少数群体的杀戮开绿灯时,人们更可能实施暴力。
而当冲突结束后,他们又会回归正常生活,成为父亲和丈夫。社会似乎并不怎么反感重新接纳他们。这同样适用于下一代。我这一代人中,很多人仍不愿面对纳粹罪行的真相,也不愿承认他们的祖父母和父母曾作为自愿的追随者支持纳粹政权,甚至可能参与了这些罪行。他们要求我们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画上一条粗线,让过去的事情过去。
在我的国家,任何坚持挖掘这段可耻历史的人都不会受到热情接待。社会中仍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我们应该让过去安息。
在许多情况下,即便是最严重的罪犯也能重返医生、律师、工程师或工匠等职业。社会需要他们。在二战这场彻底的道德灾难之后,我们曾确信人类吸取了教训,确信这样的罪行绝不会再次发生,确信罪犯会长期被社会排斥。“Nie wieder”(“绝不再来”)曾是普遍的口号——但正如我们所知,这种决心并未持续太久。
我的父母在林茨相识并开始了一段婚外情。当时我的母亲与汉斯·波拉克还在婚内,而我的父亲格哈德·巴斯特仍是盖世太保的负责人。我在1944年5月出生。1945年初,我母亲与波拉克离婚,与我的亲生父亲结婚。考虑到战争已经失败,我父亲很快会被列入战犯名单,这并非一个明智的决定。
显然,我父亲是我母亲一生的挚爱。他比汉斯·波拉克年轻20岁,这或许是吸引她的一部分原因。我的亲生父亲认识波拉克,但并不熟。据我所知,他们之间没有多少交往。当我18岁时,我母亲问我是否想将姓氏从“波拉克”改为“巴斯特”——因为我出生时她仍与波拉克婚姻存续,因此我的文件上全是波拉克的名字。我考虑了一段时间,但最终拒绝了。或许这是因为我试图与父亲的家族及他在我眼中所代表的邪恶拉开距离。
如今,又一代人无力阻止邪恶在欧洲及其他地方的抬头。
我无法、也不会去评判他人,但我知道,作为一名施害者的儿子,我不能对此视而不见。许多人说,是时候遗忘,让过去过去——为何要一再翻出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但我相信,我们有责任铭记。是的,我们可以向前看,但不能忘记过去。我们必须珍视对受害者的记忆,同时也要保存对施害者及其罪行的记忆。许多受害者似乎已无影无踪——他们无名无姓,在灭绝营的焚尸炉中被化为灰烬,或被扔进某个深坑,永远被遗忘。

2014年,我写了一本书,名为《受污染的风景》(Kontaminierte Landschaften),探讨了这个主题。这些地方是恐怖事件发生的场所,那里发生了大规模屠杀,受害者往往就地掩埋。在研究我父亲的过程中,我经常遇到这些“污染的风景”。在波兰和斯洛伐克,我父亲和他的部下曾驻扎的地方,我发现了许多这样的“污染的风景”,大多数是无名的,受害者被埋在那里。
用“埋葬”这个词并不准确:凶手只是随便盖上一些泥土。有些甚至连泥土都没盖。有些尸体在他们被杀害后不久被挖了出来,但另一些从未被找到——或者说,从未真正被寻找过。他们被遗留在某个隐秘的地方。没有石碑,没有基督教的十字架或犹太人的墓碑,告诉经过的人停下来想一想,这里埋葬着人类生命。
从波兰撤离后,我父亲带着他的部下被派往斯洛伐克,镇压当地反抗法西斯政权的起义。当时斯洛伐克是希特勒德国的盟国。在斯洛伐克,我发现了许多我父亲和他的部下留下的“污染的风景”。他们被派往那里追捕——字面意义上的“追捕”——犹太人和游击队员。我父亲是一个狂热的猎手,对山地生活非常熟悉。
在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件发生在斯洛伐克中部鲁日诺贝罗克镇(Ružomberok)附近山区的事件。在一个叫布利(Bully)的小村庄里,特遣队7a的成员发现了一群犹太人,他们藏在一个贫穷农妇的小屋里。我父亲下令将他们全部枪决——包括那个为他们提供庇护的妇人。后来,当地人挖出了他们的尸体,并详细记录了遗骸和衣物。
当这本书以捷克语出版时,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布拉格一位女士的信。她告诉我,这些无名死者中有一对带着两个孩子的年轻夫妇是她的亲人——她的叔叔耶诺·科恩(Jenö Kohn)——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一位药剂师,以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她还寄来了一张她叔叔的照片,是一位英俊的年轻人。她写道,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她仍然很高兴终于知道了他们的下落。
这正是揭开过去真相的意义所在——试图为至少一部分无名受害者找回他们的面孔和名字,甚至可能还原部分他们的历史。施害者竭尽全力让他们永远消失,从记忆中抹去,就好像他们从未存在过一样。
1945年3月,特遣队7a被解散。我父亲去了林茨,我母亲当时仍与我的继父住在那里。不久后,我母亲与继父离婚,嫁给了我的父亲。但那并不是开始新生活的理想时机。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我父亲忠心效命的第三帝国已然崩塌,苏联红军迅速推进。像许多他的同僚一样,我父亲上了战犯名单,开始潜逃。
最初,对坚定的纳粹分子的搜捕似乎被认真对待,但很快热情就减退了——在奥地利尤甚于德国。所谓的“非纳粹化”在大多数奥地利人中并不受欢迎,他们要么是纳粹政权的追随者,要么至少是冷眼旁观者。尽管奥地利的大多数犹太人在集中营中丧生,反犹情绪依然根深蒂固。而今天,我们看到这种情绪正在迅速抬头——或许这是我们国家当代最大的耻辱。
我父亲潜逃了两年,先是在奥地利,后来去了南蒂罗尔(现意大利的一部分),在那里他得到了一个富裕农民的庇护并找到了工作。他伪装成一名伐木工,但显然没人相信。他脸上的疤痕出卖了他。但没人介意。南蒂罗尔当时是某种意义上的“无人之地”。
1947年3月,我父亲计划返回。我母亲和我将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与他会合,然后陪他继续逃亡到巴拉圭——一个像臭名昭著的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那样的老纳粹的避风港。我母亲只打算带上我,她计划把她的另外两个孩子——我的同母异父的姐姐和哥哥——留给他们的父亲照顾。我父亲已经拿到了红十字会签发的必要证件,当时红十字会正在积极帮助纳粹分子离开欧洲前往拉丁美洲,发放了成千上万的出境签证。
我父亲计划穿越意大利和奥地利边界的布伦纳山口。他雇了一名当地年轻人引路,夜间的边界戒备森严。然而,这位年轻的南蒂罗尔向导确信我父亲的背包里装着传说中的纳粹黄金。他开枪射杀了我父亲,然后将他的尸体藏在一个掩体中。背包里并没有黄金,只是一些衣物和其他没什么价值的物品。几周后,尸体才被发现。
我父亲死后,我母亲深受打击。我当时太小,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我们那时住在乡下的一个村庄里,因为1944年底林茨的房子(波拉克的房子)被炸毁了。在那时候,没人告诉我任何事——既没提到我的亲生父亲,他计划带我和母亲去巴拉圭的事情,也没提到他的死。父亲去世后不久,我母亲又嫁给了波拉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波拉克又娶了她。她有三个孩子,没有工作,而波拉克深爱她。没有他,她会无依无靠。在我的家庭里,我们很少谈论过去——而我也没有提出问题。并不是被禁止提问,我只是没有问。就是这样。
去年,我收到了奥地利警方关于1947年3月布伦纳山口谋杀案的档案。我父亲被射中三枪,两枪打在脸上,一枪打在胸口。这些细节是我真的不想知道的。
他的生活是对持续暴力与非人性的写照,而他的生命却以犯罪的方式被终结。今天,我们再次面对暴力和赤裸裸的武力崛起。民主欧洲似乎准备不足。人们似乎又一次选择闭上眼睛和耳朵。愿我家族的故事能够成为一个警示。
关于作者:

马丁·波拉克现居维也纳,1944年出生于奥地利巴特哈尔(Bad Hall),在维也纳和华沙从事斯拉夫和东欧历史研究。学生时代,他开始翻译和记者工作。
文/Martin Pollack
译/tim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guardian.com/world/article/2024/jul/23/my-family-and-other-nazis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tim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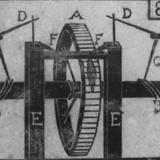


























热门跟贴